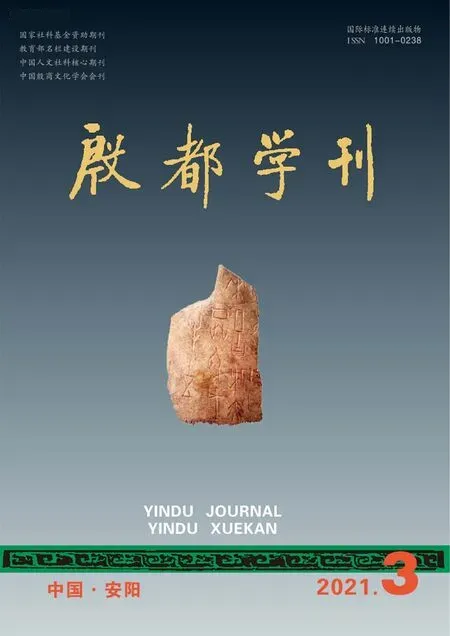《史記·五帝本紀》“柳谷”“昧谷”異文辨
游 帥
(北京語言大學 北京文獻語言與文化傳承研究基地,北京 100083)
一、“柳谷”“昧谷”異文之爭
《史記·五帝本紀》“居西土,曰昧谷”,裴骃集解:“徐廣曰:‘一作柳谷。’骃按:孔安國曰‘日入于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此居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也。’”
《五帝本紀》里的這句話原是承自《尚書》“宅西,曰昧谷”。孫欽善先生《中國古文獻學史》謂:“伏勝《尚書大傳》及《周禮·縫人》鄭玄注引《尚書》皆作“柳谷”(1)疑此處為印刷訛誤,應作“昧谷”。,可知司馬遷所據(jù)為《古文尚書》,而作“柳谷”者,當為后人據(jù)《今文尚書》所改。”(2)孫欽善:《中國古文獻學史》,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第250頁。
孫星衍《尚書今古文疏》:“[注]史遷‘昧’或作‘柳’,夏侯等書同。《大傳》‘谷’作‘穀’。[疏]史公作柳者,集解引徐廣云:‘一作柳谷’。書疏二引夏侯等書,昧谷為柳谷,是言經(jīng)之昧谷,夏侯等為柳谷也。”(3)[清]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20頁。又孫詒讓《周禮正義》卷十五:“據(jù)《堯典》疏及《大傳》則作柳穀者蓋今文《尚書》,鄭注《尚書》從古文作昧谷。故《三國志·吳志·虞翻傳》裴松之注引翻奏鄭解《尚書》違失事云古柳、卯同字,而以為昧。即指此也。”(4)[清]孫詒讓:《周禮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601頁。檢《三國志·吳志·虞翻傳》裴松之注引虞翻奏鄭解《尚書》違失事云:“古大篆卯字讀當為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為昧。”羅積勇等《中國古籍校勘史》解讀之謂“古柳、卯同字,自然同音,卯與昧音近,故柳與昧音近。”(5)羅積勇等:《中國古籍校勘史》,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57頁。
而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則認為壁中古文作“戼谷”,鄭讀作“昧谷”,今文《尚書》作“柳穀”。偽孔本作“昧谷”乃是用鄭玄說。“以愚審之,戼、丣二字易溷,壁中必是戼字。鄭于雙聲求之讀當為昧。”“司馬用今文《尚書》作《史記》,作柳者是司馬真本,作昧者淺人以所習古文《尚書》改之也。”(6)古國順:《史記述尚書研究》,臺北: 文史哲出版社 , 1985年,第61頁。
除此之外,諸家各種歧議亦紛出。不過,“昧谷”“柳谷”“柳穀”等異文在各文本分布的情況大致是明確的。即今文《尚書》作“柳穀”,偽孔本作“昧谷”,《史記·五帝本紀》今本亦作“昧谷”。
二、“柳谷”“昧谷”異文原因新探
昧古音在明母物部,卯在明母幽部。關于幽(覺)微(物)特殊通轉,清代學者段玉裁、王念孫、宋保及清末民初學者章太炎都曾對這個問題有過討論。當代學者如孫玉文、龍宇純、何琳儀、孟蓬生、鄭張尚芳、金理新等人亦有補充說明。近年來由于出土資料的日益豐富,張富海、史杰鵬、李家浩等也有專文對此進行探討。目前看來基本可以證明上古漢語中幽覺與微物文(脂質真)之間存在一定數(shù)量的音轉現(xiàn)象。(7)詳參孟蓬生《漢語前上古音論綱》一文,載《學燈》第一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44頁。但即便如此,鄭玄當時是否是基于這種認識“而以為昧”的,恐怕仍屬未必,更何況我們在上古漢語文獻中確實也未能見到昧、卯二者直接相通之例。



同樣,在漢語親屬語言的借詞中,地支“酉”阿浩姆語作rāo,怒語hrau4,仲家語thou3,李方桂先生指出,“漢代的學者用‘老’l?u解釋這個地支字(《史記·律書》《白虎通·五行》),也用‘留’lu解釋(《漢書·律歷志》)。這說明帶流音l-的漢字在聲音上很相近,因而作為訓釋字。”(12)李方桂:《臺語中的一些古漢語借詞》,載《境外漢語音韻學論文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7頁。
我們知道今文《尚書》乃受伏生所傳,口授記音。且甫一傳世,即已至今文字階段,遞相傳抄,相對而言不易生訛。而鄭玄所本之壁中書,我們推斷其“柳”字或正記作“酉(梄)”。那么,倘在此基礎上,我們再從字形考察“柳”“昧”之異,就豁然開朗了。
故疑所謂“古柳、卯同字,而以為昧”,實因“酉(梄)”“昧”字形接近,鄭玄辨識歧誤,非以雙聲求之而讀為“昧”。今文《尚書》與古文《尚書》存在的“柳谷”“昧谷”之別,當是在《尚書》傳抄過程中對字形的辨識存在差異所致。古文《尚書》乃據(jù)壁中書整理,字形辨識上便是一道障礙。故虞翻所奏鄭解《尚書》違失事,除將“柳”誤以為“昧”之例外,還有諸如“古月似同,從誤作同”等例,可見一斑。
三、“柳谷”“昧谷”何者為是
關于“柳谷”“昧谷”二者究竟何者為是的問題,過往注家多從字形字義角度入手,而對其確切地理位置絕少檢討。唯章太炎《太史公古文尚書說》得之:“今本《史記》作‘昧谷’,此從鄭改也。案:虞翻《駁鄭注尚書違失四事》云:‘古大篆卯字讀當為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為昧’。是鄭氏以前未有讀柳為昧者,蓋壁中真本作丣谷,今文作柳穀,孔安國讀古文作柳谷。柳谷自是西方地名,《漢晉春秋》及《搜神記》稱張掖氐池縣之柳谷有蒼石成文是也。此與東方湯谷皆實有其地。改為昧谷,與旸谷相儷,辭雖可觀,地則汗漫難征矣。案:《五帝德》述顓頊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濟于流沙,東至于蟠木,與《堯典》四宅相應。然張掖在漢初未入版圖,故今文諸家文作柳谷而不能實指其地,但稱柳之言聚而已。及太史公作史,則已知柳谷所在也。”(13)章太炎:《章太炎全集·菿漢微言、菿漢昌言、菿漢雅言札記、劉子政左氏說、太史公古文尚書說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45-246頁。
檢《漢晉春秋》載:“氐池縣大柳谷口,夜激波踴溢,其聲如雷,曉而有蒼石立水中,長一丈六尺。”《搜神記》則記作:“及魏之初興也,張掖之柳谷,有開石焉,始見于建安,形成于黃初,文備于太和,周圍七尋,中高一仞,蒼質素章,龍馬、麟鹿、鳳皇、仙人之象,粲然咸著。”不過《漢晉春秋》畢竟已晚至東晉,且原文乃作“大柳谷口”,用以佐證《史記》中“柳谷”之地名說服力還是有所折扣的。但太炎先生的思路給了我們很好的啟發(fā)。檢索秦漢典籍,“柳谷”之地名又見于《漢書·西域傳》:“狐胡國,王治車師柳谷,去長安八千二百里。戶五十五,口二百六十四,勝兵四十五人。”也就是在當時西域的車師一帶有“柳谷”一地。而車師的地理位置大體處在龜茲以東至焉耆、吐魯番盆地一帶。《五帝德》述顓頊西濟于流沙,亦與此“柳谷”頗相吻合。《山海經(jīng)·海內(nèi)西經(jīng)》:“流沙出鐘山,西行又南行昆侖之虛,西南入海,黑水之山。”敦煌出土的唐代《西州圖經(jīng)》殘卷有載:“大海道:右道出柳中縣界,東南向沙州一千三百六十里,常流沙,人行迷誤,沙石,往來困弊。”唐時柳中縣在今鄯善縣魯克沁鄉(xiāng),猶有故城遺跡,這與漢代車師前國的轄區(qū)形成重合。(14)據(jù)《吐魯番市志》,西漢時車師前國疆域包括今鄯善縣西部魯克沁、吐魯番市東部三堡鄉(xiāng)、恰特卡勒鄉(xiāng)、亞爾鄉(xiāng)、艾丁湖鄉(xiāng)和鄯善、吐魯番、托克遜3縣市沿艾丁湖周圍地區(qū)。(《吐魯番市志》編纂委員會編:《吐魯番市志》,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7頁。)
《尚書》“宅西,曰昧谷”句前又有“宅嵎夷,曰旸谷”,《說文·山部》:“崵山在遼西,一曰嵎銕,崵谷也。”旸谷、柳谷恐怕均實有其地。各家或稱柳之言聚,或謂昧之言冥,大約是過分側重字義的角度了。
司馬遷在《史記》“本紀”“世家”中大量采用《尚書》的記載。皮錫瑞認為“《史記》引《書》多同今文,不當據(jù)為古文”(15)皮錫瑞:《經(jīng)學通論·尚書》,見潘斌整理《皮錫瑞儒學論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81頁。。故綜合以上觀之,《史記·五帝本紀》“居西土,曰昧谷”以作“柳谷”為宜,作“昧谷”者,蓋系后人據(jù)鄭玄對《尚書》的誤識所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