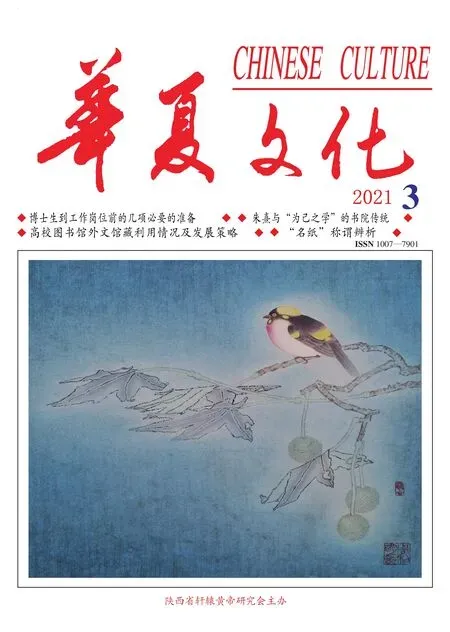貴己與貴兼:楊、墨思想比較研究
李宗敏

學術界一般認同孟子的觀點,將楊朱學派的“貴己”思想與墨家“貴兼”思想對立起來。欒調甫認為:“‘墨子貴兼,楊生貴己。’此言兩家宗本之別。”(欒調甫著:《墨子研究論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65頁)顧實講:“惟是墨家之利他主義,乃是最高之利他主義,而非下等之利他主義……楊朱乃最高之利己主義,而非下等之利己主義也。”(顧實著:《楊朱哲學》,長沙:岳麓書社,2010年,第72頁)
一、墨家的“貴兼”思想內涵
“兼”有“兼有,兼容,整體,整合,全部,全都,盡,遍,俱。”(孫中原編:《墨子大辭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第152頁)等含義。可以看出“貴兼”強調對集體的重視與認同。
維護集體利益始終是墨家思想的出發點與落腳點。墨家講“仁人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兼愛下》),墨家是立足于“公”而非“私”的。墨家指出“凡天下禍篡怨恨所以起者,以不相愛也,是以仁者非之”(《墨子·兼愛中》),“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仁者譽之”(《墨子·兼愛中》)。 “仁,愛己者非為用己也,不若愛馬著,若明”(《墨子·經說上》)可以看出,集體是墨家思想的出發點與落腳點,將動機與結果都歸于是否有利于集體的利益上。
墨家提倡個人為了集體的奉獻犧牲精神。它講“殺一人以存天下,非殺一人以利天下也。殺己以存天下,是殺己以利天下”(《墨子·大取》),墨家主張個人為了大局的犧牲奉獻精神,同時強調不能以犧牲別人來換取天下,這說明,不去傷害別人是倡導集體利益的基礎與前提。雖然主張可以犧牲個人換取集體的利益,但是墨家認為沒有人可以要求別人犧牲自己,墨家的犧牲奉獻是個人的主動犧牲,并非他人的強制,這體現出墨家對個體生命的尊重。
墨家的集體主義精神以愛護自己為前提。愛護自己是維護集體利益的出發點,“倫列之愛己,愛人也”(《墨子·大取》),愛自己就是愛人。墨家倡導維護集體利益是為了更好地維護個體利益。墨家的集體精神以尊重個人為前提,每個人對集體的奉獻是以愛護自己為開始的,墨家主張個體對集體的犧牲奉獻,是因為集體利益高于個人利益,而非對個體生命的不尊重,體現出集體與個體的統一。
綜上,墨家是站在集體立場上關注個體的。墨家既認為愛自己是愛集體的前提,又主張人們應為了集體主動去犧牲自己。當人們為了集體犧牲掉自己時,又是如何愛自己的?后來的法家則完全將個體納入集體之中,忽略了個體的價值。
二、楊朱學派“貴己”思想內涵
楊朱學派的“貴己”思想,往往被認為是自私自利的。蔣伯潛指出:“楊朱蓋亦避世之士,寧曳尾涂中,不肯為人犧牲者矣。”(蔣伯潛著:《諸子通考》,長沙:岳麓書社,2010年,第155頁)
楊朱“貴己”思想是對個體生命的重視。《呂氏春秋·貴生》講“圣人深慮天下,莫貴于生”,楊朱認為生命是最寶貴的,圣人思考治理天下,以保障人的生命安全為最高目標。《呂氏春秋·重己》講“論其貴賤,爵為天子,不足以比焉。論其輕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論其安危,一曙失之,終身不復得。”楊朱學派主張,生命比權力、錢財都珍貴,生命不會失而復得,凸顯出生命的不可再生性。
楊朱學派主張“先己后國”,反對為了國家利益去犧牲自己。《呂氏春秋·貴生》講“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之道也”,楊朱學派認為治理國家是圣人閑暇之余的事,而不是圣人全生養性的方法。楊朱學派主張先全生,后治國。所謂全生是指“六欲皆得其宜也”(《呂氏春秋·貴生》),又講“天生人而使有貪欲,欲有情,情有節。圣人修節以止欲,故不過行其情也。故耳之欲五聲,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貴賤愚智賢不肖欲之若一,雖神農黃帝,其與桀紂同。圣人之所以異者,得其情也”(《呂氏春秋·情欲》),楊朱學派認為圣人與普通人一樣都有欲望,但是圣人之所以是圣人就在于他們能夠克制自己的欲望,將自己的欲望調節到合適的程度,從而達到全生的境界。
楊朱學派認為只有達到全生境界的人才可以做國家的統治者。它講“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可以托天下。越人三世殺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其生也”(《呂氏春秋·貴生》),這里楊朱學派認為只有不因為得到天下而傷害其生命的人才可以為君王。楊朱學派認為王子搜可以做君主,就是認為王子搜不為外物(君位)所累,并不是說楊朱學派不主張人們去為國家、集體做事,而是認為做任何事首先做到的是愛護自己,珍惜自己的生命,只有珍惜自己的生命,才能夠在國家治理中珍惜、尊重他人的生命。
楊朱學派主張統治者對自己生命的重視,實則為整個國家、社會樹立一個典范,反對統治者奢侈享受,認為這不利于統治者的養生之道。 “凡食之道,無饑無飽,是之謂五藏之葆”(《呂氏春秋·盡數》),楊朱學派認為當統治者不奢侈,人民也就不會有生存困難,也就會重視自己的生命。
楊朱學派講“凡事之本,必先治身”、“昔者先圣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呂氏春秋·先己》),可見,楊朱學派不只是單純地“為我”,而是在實現“成己”的基礎上,達到實現“成人”的目的。楊朱學派主張統治者發揮“以上率下”的表率作用,因此,楊朱學派的“為我”并不是自私自利的表現,而是為了在“成己”的基礎上“成人”。
三、 “貴己”、“貴兼”不同的價值選擇
墨家“貴兼”思想與楊朱“貴己”思想看似不同,實則在本質上都是為了愛自己,都是在回答“如何愛自己,如何更好地實現自我的發展”的問題。不同之處在于兩者對這一問題的回答不同。
墨家、楊朱思想都以“愛自己”為前提,體現出兩個學派對個體生命的珍視與尊重,但是墨家主張個人可以為了集體利益犧牲自己,而楊朱學派則認為治理國家、服務國家的前提是不能損害自己的生命。二者都主張人們應該修身,但是墨家的修身更多地是為了維護集體利益,楊朱學派則是主張成全生之道。楊朱學派實際上是對墨子“兼愛”思想的補充與發展。
墨家的“貴兼”思想基于個人對集體的妥協,而楊朱學派的“貴己”則是生命至上。二者的不同實則是對生命的不同態度,墨家更多強調地是生命的價值,而楊朱學派更多側重地是生命的存活。
另外,楊朱主張在維護自己生命安全的基礎上,將自己置于集體之中,實則是指出了一個人融入集體前的必要條件,而墨家學派則是指出了融入集體后實現自身價值的問題,從這點來看,二者是相互補充的關系。
墨家與楊朱學派雖然都講治理國家,但是,墨家主張的治理國家是圣人的職責,而楊朱學派講的治理國家則是圣人實現全生之后閑暇之余做的事。墨家與楊朱學派在個體與集體關系問題上的思想沖突以及孟子對二者的批判,說明了這一時期個人、家庭、國家的關系問題已經開始成為當時社會、諸侯國以及諸子學派所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這其實涉及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國家如何治理的問題,特別是如何處理個體與集體的關系問題。
四、“貴己”、“貴兼”思想的局限性
楊朱學派的“貴己”思想對中國古代思想的發展具有重要影響,但是它并不符合逐漸由封邦建國政制向中央集權政制轉型的社會趨勢,并不利于諸侯國對加強中央集權的政治需求。而在個體與集體關系問題的認識上,墨家主張的個體服從集體的觀點更多地被后來興起的法家學派所接納。如商鞅主張“失法離令,若死,我死……行間之治,連以五,辨之以章,束之以令”(《商君書·畫策》),商鞅吸收了墨家關于個體與集體關系的思想,將個體置于集體之中,將集體與個人生命捆綁在一起,以爵位引導人們,為了國家利益犧牲自己。由于秦國商鞅變法完全地將個體置于集體之中,為了國家利益忽視個體的生命價值,使秦國成為當時的強國,但是同樣地,由于秦國不愛惜民力,不重視百姓個體的權利,不施行仁義,秦二世而亡。
楊、墨兩個學派在個人與集體關系的認識上都有著各自的局限性,從他們的局限性可以看出孟子對二者批判的合理性。“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孟子·盡心上》),孟子認為楊、墨二人思想是喪失了人的基本倫理道德,“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孟子·滕文公下》),孟子認為楊、墨二人的思想對社會產生了負面影響。“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孟子·盡心上》)這里,孟子講子莫主張中道,雖然離中庸之道很近了,但也屬于執著于一點,缺少靈活性。這也說明孟子批評楊、墨二家主要在于二者思想主張都過于極端,都過于執著于一點,缺少靈活性。
值得說明的是,孟子基于儒家中庸之道去評價二者思想。就集體與個人的關系而言,孟子對二人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楊、墨兩個學派對這一問題認識的僵化。對于集體與個人的關系孟子并不認為有具體答案,而應該置于具體環境中去考察個人與集體誰為先的問題。《孟子·盡心上》記載:“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訴然,樂而忘天下。’”孟子認為瞽瞍殺人,一方面應該去抓瞽瞍,一方面又認為舜應該放棄天子之位與瞽瞍一起逃跑,這里也體現出孟子思想中國、家、個人的關系,依國法抓瞽瞍,是不以私廢公,是國家利益至上;認為舜會為父放棄天子之位,是將家庭利益置于個人利益之上,也就是說孟子認為國家利益高于家庭利益高于個人利益。從這里也可看出孟子思想的靈活性就在于他試圖做到對個體、家庭、國家利益的兼顧,但存在的問題在于它并不利于整個國家的治理。
綜上,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的關系問題是這一時期的重要問題,也是先秦諸子回答個人、集體關系問題的初步嘗試。無論是個體利益還是集體利益,都是國家發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重視集體可以提高國家、民族的凝聚力,可是忽略了個體,集體凝聚力也不會長久。呂不韋面對即將統一的秦國提到“勝非其難也,持之其難者也”(《呂氏春秋·慎大》),這就是說對于秦國而言勝利(統一六國)不是最難的,維持勝利成果才是最難的。歷史說明,重視集體使秦國勝利,而忽略個體使秦二世而亡。要使勝利長期被保持,需要在重視集體的同時也要重視個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