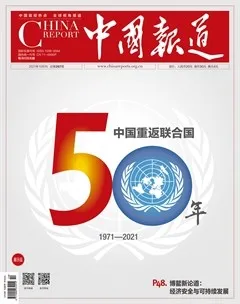“一帶一路”倡議促進國際和平合作
陳珂
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的50年間,我國從世界上最大的受援國之一,變為全球發展的貢獻者。2013年,習近平主席訪問中亞和東南亞時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旨在加強沿線國家之間的互聯互通,推動各國間的務實合作和人文交流,促進各國的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也是在這一年,聯合國成立了專門工作組,正式開始制定可持續發展目標,旨在為2015年后的各國發展和全球發展合作規劃藍圖,幫助各國共同走上可持續發展之路。
8年時間里,“一帶一路”建設跨越國家和地域界限、覆蓋經濟發展水平不一的地區、囊括多種多樣的文明,打造出了全球最大的合作平臺,目前已經組成了包括140個國家和32個國際組織在內的“一帶一路”大家庭;17項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包含169個具體目標,推動各國以綜合方式徹底解決社會、經濟和環境三個維度的發展問題,當前也正成為越來越多國家轉向可持續發展道路的行動指南。
中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耿爽曾表示,“一帶一路”倡議和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看似是兩個不同的進程,實則有很多共通之處,兩者都以推動互利共贏、實現共同發展為宗旨,都以加強協調、深化合作為手段,有關的執行工作也完全可以相輔相成、形成合力。
世紀疫情疊加百年變局,全球可持續發展當前正面臨嚴峻挑戰。“一帶一路”建設將積極適應新形勢、迎接新挑戰,更好同相關國家對接,更多造福相關國家人民,助力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
與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相輔相成
“一帶一路”建設和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議程均屬倡議,盡管發起的主體不同,但在諸多方面存在交集。北京師范大學“一帶一路”研究院院長胡必亮將此總結為目標、內容和實施主體等方面的密切關聯性。
“我們最終的目標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建設給國家和地區間共同應對貿易保護主義、反全球化、極端民族主義等全球性問題提供了合作平臺,幫助實現人類發展的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胡必亮表示,這與聯合國一貫遵循的宗旨保持高度一致。
從內容上看,“一帶一路”建設涉及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五通”,與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8涉及就業和貿易、目標9涉及基礎設施建設等內容直接相關,強調優先解決人民最關心的扶貧、衛生、教育、就業等基礎性問題。
胡必亮對《中國報道》記者表示,從實施主體看,目前共有17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同中國簽署了“一帶一路”合作文件,2015年同聯合國簽署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會員國有193個。“如果查詢就會發現,簽署兩個文件的國家高度吻合。目標、內容緊密相關,實施主體借助‘一帶一路平臺所進行的國際合作,在很大程度上也促進了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議程的實施。”
和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議程關注民生等基礎性問題相一致,“一帶一路”建設帶來的機遇正在惠及沿線國家人民,同時,相關建設計劃也更好地同當地的可持續發展路徑相對接。
在古絲綢之路上的重要一站塔吉克斯坦,貫穿全境的塔烏公路建成通車后,沿線農民的土豆再也不會像往常那樣因大雪封山爛在地里。2006年至2010年,作為“一帶一路”建設的一部分,中國參與了塔烏公路建設,這條公路改寫了塔吉克斯坦南北公路冬季不能通行的歷史,極大促進了沿線貧困地區的經濟發展。“一帶一路”建設的旗艦項目中巴經濟走廊,將巴基斯坦的國內經濟發展戰略與“一帶一路”倡議和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進行了有效對接。這一項目總投資額約460億美元,涵蓋基礎設施、能源電力、港口建設等多個涉及巴基斯坦國計民生發展的重點領域。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薛力看來,“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和實施,代表著中國人幾千年來天下治理理念的轉變。“傳統中國奉行‘禮不往教‘修文德以來之,‘一帶一路實際上是利用自己的比較優勢幫助別的國家發展,這種理念在中國歷史上是沒有過的。”
9月8日,在位于中國科學院北京新技術基地的可持續發展大數據國際研究中心,部分科研人員在“SDG 決策支持與綜合展示廳”集成地球大數據云基礎設施、學科驅動平臺和決策支持系統大廳留影。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王義桅表示,這種比較優勢源自我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改革開放中所取得的成就和形成的經驗——對廣大發展中國家無疑有巨大的說服力,間接推動了“一帶一路”建設的順利推進,也推動了全球可持續發展議程向前一步。
更好對接、擴大范圍
8年來,中國與沿線國家各領域交流合作進展迅速,“一帶一路”建設成果豐碩。胡必亮將成功的原因歸結為三個方面:“一帶一路”倡議反映出當代世界各國人民追求發展的共同訴求、遵循了時代發展的正確方向以及中國積極務實的推進。
王義桅也表示,發展中國家之所以沒有發展起來,很大程度上在于過多地受到了西方國家的影響。“可以看到,發達國家的模式在發展中國家進行復制時基本上都失敗了。中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具有最全的產業鏈,基礎設施的建造能力最強、成本最低、效率最高,比較契合發展中國家的國情。”他認為,中國所走的改革開放道路,將有為政府與有為市場相結合,尤其是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使得“一帶一路”著眼于長遠,避免了私人資本短期投資、多黨輪流執政等造成的不穩定因素,更具生命力。
數據顯示,2013年至2019年,中國與沿線國家的貨物貿易累計總額超過7.8萬億美元,對沿線國家直接投資超過1100億美元;截至2019年底,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設的一批境外經貿合作區累計投資350億美元,上繳東道國稅費超過30億美元,為當地創造就業崗位32萬個。
目前,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超過一半在東南亞國家。“這些國家積極性高,經濟發展比較活躍,特別是東盟去年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今年上半年雙方的貿易額超過了4000億美元,預計今年全年這一趨勢仍不會改變。”胡必亮表示,“一帶一路”建設接下來應當發力的是中蒙俄、中亞和中東歐地區,“這些地區受制于政治、經濟等因素,但有條件做得更好。”
9月27日,國家國際發展合作署署長羅照輝在2021年可持續發展論壇上表示,推動共建“一帶一路”是中國開展國際發展合作的重要內容,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是中國開展國際發展合作的重要方向。中國的國際發展合作將繼續向“一帶一路”共建國傾斜,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更強動力、更大空間、更優路徑,使之成為全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推進器”。
第三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暨虹橋國際經濟論壇開幕式于2020 年11 月4 日在上海舉行。
事實上,不只是發展中國家。自2015年6月中法兩國政府發表《中法關于第三方市場合作的聯合聲明》起,我國目前已經與法國、日本、意大利、英國等14個發達國家簽署第三方市場合作文件。
第三方市場合作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經濟體引導各自企業共同開發第三方國家市場的合作模式。“對于發達國家,中國更像是起到了轉化器作用——把發達國家的標準轉化為能夠在發展中國家因地制宜施行的方案。這是為什么發達國家也參與進來的原因。”王義桅表示。
在高質量共建中抓住新機遇
作為一個系統而龐大的工程,“一帶一路”建設也面臨諸多挑戰。
除了我國自身存在的不足,“一帶一路”倡議在最早提出時就伴隨著外部非議,有西方國家將其視為新時代的“馬歇爾計劃”“中國版WTO”等,采取多種措施抹黑、對沖、打擊“一帶一路”建設在相關國家和地區的落地實施。
對此,胡必亮認為不必悲觀,“一帶一路”建設帶來的利好有目共睹,“如果對沖、打擊是為了讓世界變得更好,我們樂見其成,繼續把這件事情做好是最重要的。”王義桅也表示,“一帶一路”倡議主要聚焦發展,強調合作、互聯互通,同聯合國有關事業相一致,這也是為什么聯合國大會、聯合國安理會認可并將其納入決議內容的原因。
針對新冠肺炎疫情后出現的質疑“一帶一路”建設與全球可持續發展關系的雜音,羅照輝表示,疫情以來,中國對“一帶一路”和全球可持續發展的推進沒有放緩,共建“一帶一路”與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也沒有脫節。比如,在設施聯通方面,中老鐵路、匈塞鐵路、以色列輕軌等40多個標志性項目取得突破性進展;在貿易暢通方面,去年我國對沿線國家非金融類直接投資同比增長18.3%,新簽承包工程合同額1414億美元,完成營業額911億美元……
此外,羅照輝表示,我國對外援助將為共建“一帶一路”實現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展現新的作用。他指出,我國開展對外援助71年來共向160多個發展中國家提供過援助,“尤其是去年以來,面對疫情開展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最集中、最廣泛的援助——向世界各國提供2900多億只口罩、35億多件防護服、45億多份檢測試劑,向100多個國家提供超過12億劑疫苗,同28個國家共同發起‘一帶一路疫苗合作伙伴關系倡議。”
“現階段,疫情對‘一帶一路建設的影響正逐步削弱。但面對嚴峻復雜的外部環境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沖擊,全球發展將轉向數字化、綠色、健康,全球供應鏈追求自主、可控、安全。”王義桅向《中國報道》記者強調說,“一帶一路”建設必須適應這些轉變,推動綠色、健康、數字化成為合作新的增長點。
以綠色絲綢之路為例,9月21日,習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宣布,中國將大力支持發展中國家綠色能源低碳發展,不再新建境外煤電項目。“我國的能源轉化、低碳能源等技術較為先進,為了契合發展中國家國情,提出了全球能源互聯網計劃,即智能電網、特高壓電網、清潔能源三位一體。這將對綠色絲綢之路建設起到積極推動作用,推動實現綠色絲綢之路和全球能源、環境等的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