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心魔面對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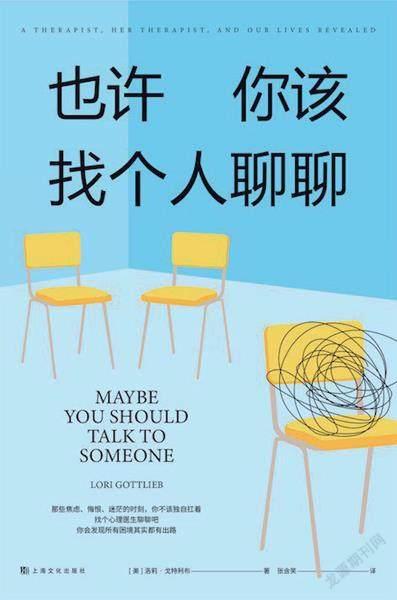
也許你該找個人聊聊》
[ 美] 洛莉·戈特利布張含笑 譯
果麥文化/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21 年7 月
瑞士著名心理學家卡爾·榮格說過:“人們會想盡辦法,各種荒謬的辦法,來避免面對自己的靈魂。”
但他還說過:“只有直面靈魂的人,才會覺醒。”
到處是蠢貨
當年逾不惑的約翰坐在我對面,跟我說起他生活中遇到的所有“蠢貨”時,我就像念咒語一樣,在心里不斷地重復著這句話:為什么!
他想知道,為什么世界上會有這么多蠢貨?他們生來就是這么蠢嗎,還是后天變蠢的呢?他尋思著,或許是我們現在吃的食物里所含的人造添加劑在作怪。
約翰自述感到“壓力過大”,入睡困難,無法與妻子和諧相處;周遭的人令他心煩,他想知道如何“應付這些蠢貨”。
我已經快數不清他都提過哪些“蠢貨”了:問太多問題的口腔衛生師—“他的每個問題你都得回答”;一天到晚發問的同事—“他從不作任何陳述,因為根本提不出什么見解”;那個把車開在他前面,一遇到黃燈就立刻剎車的司機—“一點緊迫感都沒有!”還有那個沒能幫他修好筆記本電腦的蘋果天才吧的技術專家—“真是個磚家!”
“約翰……”我剛要開口,但他已經開始講述另一個有關他妻子的冗長故事了。盡管他來這里是為了尋求我的幫助,但此刻,我卻完全插不上嘴。哦對了,我是誰呢?我是約翰新一任的心理治療師。他在上一任治療師那里只做了三次治療,他對那個治療師的評價是“很友善,但愚蠢”。
“然后呢,瑪戈她就生氣了—你能相信嗎?”約翰繼續說道,“但她不會告訴我她生氣了,她只會用行為來表現出她生氣了,然后指望我去問她是怎么了。但我知道就算我問了,她頭一兩次肯定會說‘沒怎么,直到我問第四第五遍的時候,她才會說,‘怎么了你自己知道,然后我就會說,‘我不知道呀,否則我就不問了呀。”
就在這時,約翰嘴角上揚,展現出一個燦爛的微笑。我嘗試從這個微笑入手,借機打破他的獨角戲,與他進行對話,和他建立交流。
但他打斷了我。“我還剩20 分鐘時間。”說完,他繼續講起了他的故事。
每個人都有可愛之處
在我接受心理治療師的專業培訓時,曾聽督導說過,“每個人都有可愛之處”。我后來驚訝地發現,她說得沒錯。如果你能深入了解某個人,就不可能不對他產生好感。我們應該把全世界的宿敵們都請到同一個房間里,讓他們分享各自的過往和成長經歷,說說內心的恐懼和掙扎,也許他們立刻就能和諧共處了。
作為一名心理治療師,我真切地從每個來訪者身上都找到了令人喜歡的地方,就連一位曾企圖實施謀殺的男士也不例外—深藏在他盛怒之下的,其實是一片柔情。
當我目送約翰大笑著走過走廊時,我仍堅信自己一定會慢慢發覺他的可愛之處。在他惱人的外表之下,一定會冒出一些可愛的,甚至是美好的特質。但那已經是上周的事了。今天他表現得完全像是個混球,一個牙齒炫白的混球。
“要心懷慈悲,要心懷慈悲,要心懷慈悲……”我繼續默念我的咒語,嘗試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到約翰身上。他正在講述劇組里某個工作人員所犯的一個錯誤(在約翰的講述中,那個人的名字就叫“蠢貨”)。
就在這時,我突然意識到,約翰的咆哮聽上去竟出奇的熟悉。這熟悉感并不來自他描述的情景,而是來自這些情景所觸發的情緒:理所當然地將自己的不滿遷怒于外界,在名為《我無比重要的人生》的現實情景劇中,拒絕承擔自己的戲份。
我了解那種感覺:沉浸在自以為是的憤慨中,堅信自己絕對正確,還覺得受盡了冤枉和委屈。作為心理治療師,我十分了解痛苦,我知道痛苦總是和喪失緊密相連。但我還知道一些不太容易理解的事情,那就是變化也常常伴隨著失去。無所失則不得改變,正因如此,人們常常說著要去改變,卻依然駐足原地。要幫助約翰,我就得知道變化會令他失去什么。
自身即地獄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心魔,或大或小,或新或舊,或安靜或吵鬧,不管以什么形態出現,這些不速之客總會找上我們。既然連治療師都有心魔,也就證明:心理問題并不是少數人才有的問題。認識了這個事實,我們就可以嘗試和自己的心魔建立一種新的關系,不再非要和內心那個引發困擾的聲音爭辯出個青紅皂白,也不用再依賴酒精、暴飲暴食或是上網來麻痹我們的感受—雖然我的同事們也都把上網看作是“最佳短效非處方類止痛劑”。
心理治療中一個很重要的步驟,就是幫助人們對自己當前的困境負責,因為只有當人們意識到自己有能力,且必須靠自己的能力去建構生活,他們才能放手去改變。然而,人們常常將自己的問題歸咎于環境或條件等外在因素。既然問題是由別人或客觀因素造成的,是外界的錯,那又有什么必要去改變自己呢?畢竟就算自己決心去改變,外界也還是老樣子。
這樣的狡辯聽上去很有道理,但事實并不是這樣的。薩特說過:“他人即地獄。”確實,這個世界上到處都是難對付的人(或者用約翰的話來說,都是“蠢貨”)。我敢打賭,就算要你立刻說出5 個你覺得真心難相處的人也不難。這些人里有的你能避則避,有的或許礙于血緣而避之不及。但我們常常不能意識到:有時真正難相處的,是我們自己。沒錯,有時自身即地獄。
有時我們就是自己的絆腳石。如果我們能把“自己”從前行的路上挪開,奇跡便會發生。心理治療師會為來訪者豎立一面鏡子,但同時,來訪者也是醫生的鏡子。心理治療不是單向的,而是一個雙向的過程。每一天,來訪者帶來不同的問題,我們也會在自己身上反思這些問題。
如果我們的反思能幫助來訪者更透徹地看清自己,那我們也可以透過他們來更清楚地認識自己。這樣的雙向過程,發生在我們為來訪者提供心理治療的時候,也發生在我們自己接受心理治療的時候。我們是鏡子,反射著對面正在反射我們的鏡子,互相照見自己未曾發現過的自己。
(本文獲出版社授權,標題為編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