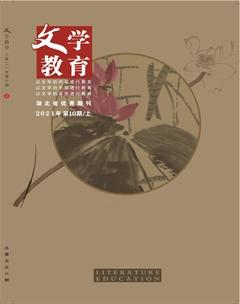時光之下的喚醒與沉沒



于懷岸,出生于上世紀七十年代。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文學創作,被譽為“文學湘軍五少將”之一。在《人民文學》《中國作家》《青年作家》《民族文學》《花城》《上海文學》《江南》等眾多文學期刊發表長、中短篇小說近百部(篇)。曾獲湖南青年文學獎、深圳青年文學獎、《上海文學》中篇小說獎、《民族文學》年度獎等獎項。已出版長篇小說《巫師簡史》等。小說集《一粒子彈有多重》《一座山有多高》《想去南方》《骨肉》《火車,火車》《一眼望不到頭》等。
當前我們所生活的世界,是多重空間的混雜。由于互聯網的介入,人們在主流空間之外還能夠實現對其他空間的全新配置,現實與虛擬的反復跳躍之下,人類與環境的關系更為復雜,一方面,虛擬空間打破了環境的實在之感,但另一方面,人們又能夠在這種交叉空間中獲得真實的感官回饋,并且帶來重組時間的體驗以及邊界跨越。
于懷岸在其小說中就塑造了這樣一種真實與虛擬的混雜,在他的小說中,真實與虛擬的二元對立被否定了,轉而實現的是一種混合的循環體系,人類成為書寫的主題,在一個物質與信息共通的虛實結合之下,持續不斷地建構并且重建自己的邊界。
在于懷岸的小說中,故事大多發生在小鎮甚至是鄉村中,人物在隱秘的時間循環中勾勒出了獨特的命運象征,死亡敘事與時間循環在個人視覺上形成了某種恒定的思想特征,在人生的不同階段,于懷岸書寫了不同人物對于死亡的思索以及困惑,在這樣的困境之下有效地聚合了情感本質,也激蕩出獨特的美學色彩。
一.循環敘事下的焦慮籠罩
在小說的敘述形式中,重復性敘事始終是小說敘事形式以及表現手段中常見的一種。作家們借助這種對于語言的玩味以及自我放逐式的闡釋來完成對于小說意義的固定。在這種重復之下,小說原本的情節講述具有了某種離心的力量,使得讀者能夠在這種重復性的講述中重新創造作為他人的經驗,這種想象性的力量才能使個體變為更加有生機的存在。
而在于懷岸的小說中,我們也常常能夠窺探到這種想象性重復的存在,在小說的寫作中,他顯然意識到了自我的根基無限沉降,因而轉用重復的敘事手段,令自身獨一無二的闡釋去參與到更偉大的整體、在自我之外的某處深不可測之中找尋到新我的途徑。
在于懷岸的小說中,他不斷地在客觀性進程的重復中來書寫自我的終極目的,他所尋求的意義是在偽裝之中接近欲望的主題,并且在這些意義之中來體驗過往世界中的喧嘩與流動。他的小說大多發生在鄉鎮甚至農村之中,這樣一種帶有原始野性的空間,具備了精神性的藝術力量,小說也能夠在生活的表象之下挖掘出真理本質。
實際上,人們的認知不應該囿限于小我固化、強化的自循環,認知也能夠以自我延伸的方式發生,即在遙遠和陌生的事物中去發現自我的新配置。只有將自我之根盡力拉伸直至拉到將斷未斷之時,才能一睹奇異妙美的景致。
從小說《你為什么結婚》[1]來看,小說將余朋宴這一女性角色在持續不斷的推拉乃至生活重復之中實現了模糊的流動感。余朋宴所展露的是一種對于生活機械性的反抗。在她的生活中,她經歷了種種自我的糾葛。她的婚姻也如是,在小說中,作者講述了幾次循環,她和丈夫周廣斌的每一次推拉,實際上都暗含著謊言和騙局,但當真相抵達到了某一個程度時,這一部分真相就轉而形成了某種完全的事實,更抵消了其作為騙局的本質。因此,沒有一個循環是孤立的,小說就在這種循環與人物交融中十分明顯地轉換出了任務的彼此平衡乃至到的思考,發揮出美學價值中彌散的張力。
她的婚姻乃至生活方式是一次又一次的重復和自我解脫,她試圖從經驗角色的負擔中擺脫出來,但卻不可避免地在反叛的轉型之中被制服,她所經歷的是一個女性在當代社會中的掙扎和解體,小說也沿用了某種循環的講述,來將這種隱藏的痛苦加以懷想。
余朋宴是一個認識到了生活之美,同時也有著一定的自我意識的覺醒,但在生活的摧殘以及自我的搖擺之下,她仍然陷入了自我的頹唐。面對著周廣斌近乎誘奸的入侵,她在強裝鎮定之下,誤入了婚姻,又進入了現實的反叛之中。在她的婚姻生活里,她原本不想嫁給周廣斌,但在彼此的推拉以及周遭生活的擠壓之下,她進入到了這樣一段從一開始就是錯誤的婚姻中。小說中將她的慘淡婚姻進行了非常直觀的刻畫,她與周廣斌,兜兜轉轉,從一開始的周廣斌下套和余朋宴結婚,到余朋宴不肯放手。當小說的最后,兩人終于分開,而余朋宴再婚看似找到了一個好的對象,但面對那個癡呆的兒子小正,即便余朋宴從未流露過,但仍然在最后“雙眼霧蒙蒙的、空洞、呆滯”。她的再婚對象趙文遠撫過她的臉頰,語氣輕柔:“等我們有了孩子,就叫小正吧。”
很顯然,小說在此完成了一種深度的循環,隱藏在了可感的場所之中,實現了對于自我境遇的逆轉和循環反叛。事實上,小說所呈現的是一種對于物質事件的情緒轉換,克服了凝視的障礙,并且將事件變為了可感的情緒,發揮出重要的儀式功能。循環性敘事打破了原本封閉單一的小說敘事講述,在無限循環的悖論情境中,小說能夠不斷地吸納到純粹的情感,并且提供多層級的離散式閱讀體驗。
在于懷岸的小說中,讓我們在生活中發現一些被遮蔽的東西,這是我們無法用經驗來感受到的。作者試圖在主體的消解中講述邏輯纏繞,并且對自我的界域和時域的局限性做出了良好的揭露:無論個體的境遇如何,自我的功能需要總是會與相應的配置形成較大的際差,也就形成了致命的沖突,顛覆了意識性的儲備。
二.死亡書寫建構沖突衰敗
在于懷岸的小說中,死亡一直是極為經典的命題建構,無論是虛構死亡還是真實的死亡敘事,他在自己的小說中都呈現出一種向死而生的別樣故事內核,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于懷岸所書寫的死亡并不是生命意象的終極毀滅,而是在虛構的探索之下深入到人性之中,完成某種對于哲學深度的推進。
在這樣的文學圖景中,小說所呈現的向死而生,都形成了某種特殊的虛構死亡的敘事方式,這種死亡敘事所開啟的并不是對于死亡的恐怖和萬物寂滅的逼仄,而是在靈魂的盡頭之處,書寫堅韌生命的美感。
事實上,我們可以將于懷岸的死亡書寫看作是一種對于日常生活的藝術化呈現,在死亡的視角之下,小說通過種種嫻熟的筆墨來對故事進行打磨和重建,能夠有效地在間離的效果之下呈現出復雜的人生況味,無論是他對于死亡美學的追溯,抑或是在死亡陰影之下所建構的人性沖突,都呈現出多重復調的敘事效果。在小說《合木》[2]中,從始至終,“我”的故事都與死亡有關,作為一個“合木師傅”,也就是給人做棺材的人,“我”經歷了一場又一場的死亡,也從這些蕓蕓眾生的死亡絕境之下,敘述了當人抵達虛無之后,人類在靈魂深處的想象與規則。事實上,“我”的角色是一個在死亡與生命之間不斷徘徊的人,作為離死亡最接近的人,他受人尊敬,卻也被人拒絕靠近。在此,死亡是一個至高無上卻也恐怖如斯的秘密,在這樣持續性的狀態中,人物被割裂成為了悲涼且備受摧殘的生命主體,只能不斷地在生命的限度中聯結日常生活的哲學。
或許是第一人稱的敘事視角加持,《合木》顯現出一種順暢卻碎片化的敘事模式,以合木為線索,小說收束成為了一種關于陰陽兩界的代際延續,虛實結合之下,小說以死亡作為勾連點,完成了結構上的內外建構。
而在小說《一切美好的事物皆應永存不朽》[3]中,小說以一場兇殺案開頭,顯然是極其現實主義的筆調,但到小說的結尾,故事卻呈現出一種全然不同的浪漫主義乃至現實魔幻的書寫,呈現出某種攝人心魄的美感。面對女孩的死亡,女孩的尸體,老彭在一片靜謐之中窺探著這樣的美感,他不想檢查少女的傷口,更不想破壞這種美感,事實上,他被這一具裸體所打動了,少女的死亡陡然成為了某種自由與永恒的象征。在最后,老彭向上面傳遞了拉繩索的信號,他幻想著少女身上的血肉在冰層之中永不腐爛,更幻想著她軀體融入到每一粒沙子之中,消亡成為永恒的美。
在此,小說實現了美學形式上的邁進,小說超越了現實的人性,轉而直接指向對于人性的探索。在小說中,顯然,老彭并不是一個日常中對美的追求者,但在死亡的絕境面前,他仍然爆發出了對于虛幻美感的追求和神圣敬畏。少女的尸體在此成為了柔軟姿態下的生命力抗爭,即便是死亡,也呈現出了一種絕美的生命力和自由的光明精神。
那具絕美的裸尸最終會歸于塵土,這樣的情節很容易令人想到《紅樓夢》中黛玉葬花的一段,“質本潔來還潔去”的燦爛意志所穿越的是死亡世界的虛擬,也完成了對現實主義的超越和生存意志想象。
很顯然,死亡是每個人都不可逃避的,在奔向生命終點的路途中,人們所選擇的道路是全然不同的,但小說仍然呈現出了一種全新的思考以及深度的洞悉。當人在無牽無掛的絕望中奔向死亡,小說自然也就呈現出了人類豐富的本質,也闡述了更為燦爛的生之意志。于懷岸在他的作品中建構了廣闊的死亡詩學思索,在死亡這一非常態的情境之下,于懷岸完成了對于美學乃至哲理的探索,突破了舊有的思維方式,在無經驗的狀況中實現了對于生存意志的推進。
當表達或壓制死亡沖動耗盡了你的生命。主體在自我創建的空虛感中維護自己普羅米修斯式的意志。這種空虛感將意志本身的行動化作烏有。在征服周邊世界時,意志廢黜了對它自己行為的所有約束;而在同樣的行動中,也破壞了自己英雄般的規劃。當一切都得到允許,沒有什么還會有價值。
從這種結構來談,小說所呈現的是一種絕對的殘忍,同時也是一種最為集中的美學意象,黑暗的死亡意象顯現出情感脈搏的膨脹。無論是《合木》中蕓蕓眾生世事滄桑,在立體人性中展露出柔弱生命的悲喜與共,還是《一切美好的事物皆應永存不朽》中面對美好胴體的由衷虔誠,絕境之中人性真正的美好與純善,建構起了對于脈脈溫情的把控與悲憫。
三.生命困境中的自我排斥
值得思考的是,在死亡敘事以及時間循環之外,于懷岸在他的作品中也提出了對于生命困境的闡釋,在個體的虛妄之下,他試圖書寫一種關于人的偉大自由幻想,包含了對于自我所囤積的悲喜劇觀念,也由此宣告了人們所排斥的自我。
事實上,他所書寫的現代困境也不斷地通過人物的自我排斥乃至空虛的沖動來加以顯現。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種困境關乎于選擇,小說也就通過諸多生存命運下的隱喻來指控人們在困境之下的自我排斥以及不自由的困苦。
因此在于懷岸的小說中,虛構與真實、文本與現實提供了一種越界般的敘述手法,打破了原本傳統的敘述方式,在類似莊周夢蝶的審美感應之中,剔除了多余的人性翻滾,緊接著就在想象之下實現了對自我人生困境的建構和拓展。
從小說《余生漫長》[4]來談,小說所講述的是一個叫做李有然的男人,無父無母、無兒無女、孑然一身,他的生活始終在不斷地找尋,他多次入獄,而出獄之后,他又為了找到自己的兒子,終其一生都在路上,相伴而生的,是他一次又一次地被生活所打敗,找不到兒子,也失去了自己的妻子,面對妻子之后的歸來,他又無法讓自己全然放棄。
正是在這樣一種裹挾著痛苦的找尋之中,小說實現了一種關于生命困境的斷裂式排斥,人物的命運仿佛被割裂開,在世界的遭際之中不斷翻滾打旋,墜落到底。自由精神在任何時候都完全相信自身參與的實踐:它們知道,至少在那時,若無這些信念就無法生存;但它們也知道,如果他人若抱有同樣的信念就無法生存。
小說在對他的闡釋之中加入了諸多魔幻的色彩,李有然的人生也可以看作是一幕現實魔幻的悲喜劇,在個人的虛構故事上,小說通過對于邏輯矛盾的掙脫,來消除自身在生命困境中的掙扎和痛苦,也書寫了真實的自我障礙。不僅如此,小說還利用一種近乎語焉不詳的姿態來闡述了生命困境的普遍性。事實上,當作家們精確、認真、恰當地表達自己的思想,其文字就顯得愈加晦澀難懂,因為他們希冀于得到全然精確的反饋,但值得思考的是,而無論措辭多么嚴謹純粹,結果都會造成一種真空。
與之相反的是,隨波逐流而來的淺俗道理被認為是接地氣的標志,當人們在作品之中窺探到自己想要的表達時,小說中人物的內容與記憶、心理和生活行為獲得了內在的統一,這種精確是一種聚焦而非定焦,能夠有效地凝視到全局之中。表達允許聽者去想象任何適合自己的東西,以及他已經想到的東西;而嚴格的說法需要明確的理解和概念上的努力,人們故意排斥這種理解和努力。只有他們不需要理解的東西,才認為是可以理解的。
這也可以解釋在小說《余生漫長》之中所語焉不詳的狀態,作者從始至終都沒有對李有然的多次入獄經歷進行多么細致的描繪,這種“粗枝大葉”的講述也同樣顯示在了對于他整個人生的描述之中,無論是兒子的去向,還是李有然自身的心理狀況等,小說都以一種自我排斥的姿態進行了模糊的闡釋,近乎幻覺的始終找尋之下,小說呈現出一種自由的信念感,也反映出了綿延的自我突圍。在這些隱喻的投射通道之中,小說承載起了解放的自由的意義象征,人類永遠擺脫不了“回溯”的誘惑,回溯在追尋到了過去時間的同時,也證明了自我的存在。
或許在于懷岸的思考之中,李有然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種對于自我人生的突圍,在小說的最后,李有然找尋一生的兒子仍然沒能找到,但那頭牛卻形成了隱秘的循環敘事,而當他死后,下葬之前,他找了一輩子的親生兒子卻來到了靈堂前,甚至,這個兒子在尋找自己的母親,自此,小說也就形成了某種回環的宿命論點,突圍了專屬的倫理范疇,形成了自我表達之后的異常逃逸。當父子二人的彼此找尋乃至生命找尋承載了不可預知的隱喻。由此,理想的達成因此也超越了理想。小說中的他們始終不服從于宿命,而是服從于斗爭的自己,也始終堅持多重的邊際之中找尋被排斥的自我。
四.形式到哲學轉變的自由格局思考
在前文中我提到了于懷岸對于死亡命題的追求和講述,而從另一種層面來說,于懷岸對于人性的書寫也同樣尖銳,在他的小說中,我們能夠窺探到人物的鮮活屬性:他們的意志是有所欲求的,舊的欲求一旦滿足,便會追求新的,永無休止。實際上,人的快樂和順遂,僅存于從欲求到滿足、再到產生新欲求的過程中,而這一過程持續時間很短。得不到滿足便會痛苦,尋不著新的欲求便會倦怠,便會無聊。
在他的思考之中,世界更加徹底地成為了哲學的冒險思考,人們能夠與純粹的感覺相分離,形成思想和記憶、思想和認知的現實平衡。當一個人能夠看穿世界的某一單薄屬性之時,他也就具有了對生活的反叛。在于懷岸的小說中,所闡述的就是這樣一種迷失與找尋,乃至人物在自由意志之下的真理引入。
黑格爾在《美學》里有一個著名論斷:(文學)人物是創造自我的自由藝術家。這個論斷里有兩個要點:第一,人物的“自我”是創造(請注意,不是塑造,更不是再現)出來的。第二,這個人物擁有能夠逃脫創造者之控制的自由。[5]
很顯然,在于懷岸的小說中,我們常常能窺探到這種離散感和自由感,于懷岸近乎放任地任憑他筆下的人物不斷地自我突圍,同時,在這樣一種自我創作中擺脫固有的經驗敘事,完成了對于文學人物的標志疊加。在這幾部作品中,人們不斷地談論著絕望、孤獨、乃至特殊且悲慘的生命個體,無論是如同《你為什么結婚》中只是經歷微小生活挫折的余朋宴,還是在《余生漫長》中漫長一生都在尋找和對抗的李有然,都表現出了一種對于生命本身的抗爭和愉悅。
人們通常認為,沒有比按照我們自己選擇的方式過日子更重要的事情了。這不是因為我們比先輩更珍視自由,而是因為我們已經認定,良好的生活就是被我們自己選擇的生活。然而,“生活可以選擇”這一理想,與我的如何生活這一事實并不協調。我們并非自己生活的原創者,甚至連烙印般事件的合作者都談不上。
正如小說《合木》中的“我”,從始至終,“我”的選擇都并非是自己想要的,但卻在一次又一次合木中走向了生命的盡頭,盡管這種生活并非由自我選中,但卻在他的生命中解構出先行的烏托邦。而《一切美好的事物皆應永存不朽》亦然,在老彭的選擇之下,他所堅持的是一種美學的驅動,也就此實現了創造性的意志找尋。
在生活中幾乎所有重要的事情都不是我們自己選擇的結果。出生的時空、父母、母語,這些都是憑借機遇而非選擇。正是事物的隨機性塑造了我們生活中最決定命運的關系。因此個人的自主性是我們想象出來的東西,不是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被投擲到一段時空之內,其中的一切都是已被規定好的。新技術每天都在改變我們的生活,但我們很少能知道未來將給我們帶來什么。對選擇的崇拜反映出我們不得不在生活中窮于應付的窘境。我們只能如此,這是我們不自由的標志。選擇已經成為了一種迷戀,但這種迷戀恰恰意味著它不是被選中的。
也正是因為這種無法選擇,于懷岸在小說中真實細膩的細節是為了襯托出整體生存下的荒誕。不難看出,在于懷岸的作品中,他堅持認為沒有一種永久的、同樣的物質能充斥世界,正相反,我們今天所堅持喚醒的世界實際上是力量和關系相互對抗的源泉。每個個體都有讓它存在下去的意志。現實由成千上萬相互纏繞成網、彼此疊加的個體意志組成。其中的一些精巧生動,另一些則怠惰認命。在這樣的世界里,許多至今尚不可思議的事情成為了可能,而各種個體間的界限則是虛妄的。
無論是對于鄉村敘事的關注,抑或是于懷岸在死亡敘事中所表現出的持久性和迷戀感,都闡述了其對于死亡敘事的理解和想象,小說也常常借助不同人物之口,不斷地闡明了作者對于死亡的思索與體悟。再次,死亡并不像某些小說一樣發展成為亡靈敘事或是死亡主體的注解,而是成為了一種持續性的自我見證,令人得以在死亡的陰影中思索生活的真實狀況,凸顯更為真實唯美的人性魅力。
注 釋
[1]于懷岸:《你為什么結婚》,《青年作家》2018年第9期。
[2]于懷岸:《合木》,《江南》2018年第4期。
[3]于懷岸:《一切美好的事物皆應永存不朽》,《長城》2020年第2期。
[4]于懷岸:《余生漫長》,《青年作家》2020年第8期。
[5]著者:[德]黑格爾:《美學》(第3卷)(下)著譯者:朱光潛.1981年7月。
馮祉艾,出生于1995年。湖南長沙人,畢業于湖南師范大學。作品散見于《文藝評論》《東吳學術》《百家評論》《中國當代作家評論》《名作欣賞》《中國文藝評論》《中國作家》《青年作家》《野草》《青年文學》《文藝報》等報刊。現供職于湖南省文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