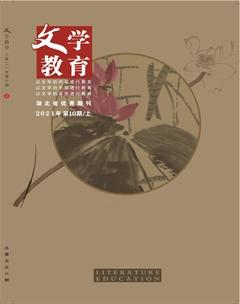卡夫卡《判決》的深層隱喻
韋祚浩
內(nèi)容摘要:短篇小說(shuō)《判決》敘事帶有卡夫卡自傳性色彩。小說(shuō)以格奧爾格和父親之間矛盾為情節(jié)展開(kāi),也象征著作者和父親之間的沖突。從弗洛伊德文藝觀來(lái)看,文學(xué)藝術(shù)是作家的“白日夢(mèng)”,為作家本能、無(wú)意識(shí)中的壓抑提供一種宣泄渠道,是潛意識(shí)的外化。小說(shuō)主人公格奧爾格的經(jīng)歷與卡夫卡的處境較為相似,他們對(duì)“父親”反抗的根源基本相同。
關(guān)鍵詞:卡夫卡 《判決》 精神分析批評(píng) 白日夢(mèng)
短篇小說(shuō)《判決》是卡夫卡創(chuàng)作走向新階段的成果之一。小說(shuō)細(xì)致描述主人公格奧爾格潛意識(shí)活動(dòng),其本我意識(shí)在生活中受到壓抑,在與父親的矛盾沖突中無(wú)意間表現(xiàn)出其“弒父”心理。《判決》的故事情節(jié)與卡夫卡生活經(jīng)歷有密切聯(lián)系,從精神分析學(xué)角度看,故事情節(jié)包含作者的內(nèi)心的外化,格奧爾格和卡夫卡經(jīng)歷較為相似,在“父權(quán)”壓抑中成長(zhǎng)與反抗。這也是作者“幻想”的動(dòng)力和不滿足原因的根源。弗洛伊德從精神分析角度把文學(xué)藝術(shù)解釋為創(chuàng)作者“白日夢(mèng)”,形成以精神分析學(xué)為研究方法,運(yùn)用于研究文學(xué)、藝術(shù)作品中的人物心理和揭示人類(lèi)心理深層意識(shí)領(lǐng)域的文藝觀,同時(shí)作品不謀而合印證理論的成立。精神分析學(xué)的形成對(duì)現(xiàn)代文學(xué)觀念、文學(xué)批評(píng)實(shí)踐等產(chǎn)生重要影響,也為文學(xué)創(chuàng)作、文學(xué)研究和批評(píng)實(shí)踐提供一種新的視角與研究方法。本文擬從精神分析批評(píng)角度探討《判決》中的深層隱喻問(wèn)題。
一.格奧爾格的潛意識(shí)與“俄狄浦斯情結(jié)”
人的潛意識(shí)是精神分析學(xué)以及心理學(xué)領(lǐng)域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心理學(xué)認(rèn)為潛意識(shí)指“潛隱在意識(shí)層面之下的感情、欲望、恐懼等復(fù)雜經(jīng)驗(yàn),因受意識(shí)的控制與壓抑,致使個(gè)人不自覺(jué)知的意識(shí)”,也稱無(wú)意識(shí),多表現(xiàn)為人的本能、被壓抑欲望,人們?cè)谀骋粫r(shí)刻不經(jīng)意間通過(guò)言語(yǔ)、動(dòng)作、夢(mèng)等方式顯露出來(lái)。“俄狄浦斯情結(jié)”是弗洛伊德引用索福克勒斯的悲劇《俄狄浦斯王》中俄狄浦斯無(wú)意殺父娶母故事,來(lái)闡釋人最深層的心理意識(shí),由于“弒父娶母”行為有違背倫理而不為社會(huì)所允許,只在人的潛意識(shí)里活動(dòng)。弗洛伊德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弒父者》文中指出,“弒父是人類(lèi)的,也是個(gè)人的基本的原始的罪惡傾向”,是一種罪疚的情感體驗(yàn)。在心里上把父親看做競(jìng)爭(zhēng)對(duì)象而產(chǎn)生的負(fù)面仇視,但對(duì)父親懷有關(guān)愛(ài)、敬畏,整體上對(duì)父親是一種既有愛(ài)也有恨的心理矛盾狀態(tài)。
格奧爾格有類(lèi)似“俄狄浦斯情結(jié)”,即“弒父”潛意識(shí)心理。格奧爾格與父親之間矛盾積累已久,且長(zhǎng)時(shí)間對(duì)父親有畏懼心理,最后因訂婚事件激發(fā),被父親判決死亡。母親在世前,父親在商業(yè)經(jīng)營(yíng)上獨(dú)掌權(quán),鑒于畏懼心理,顯然格奧爾格對(duì)父親的各項(xiàng)安排是百依順從。母親去世后,父親逐漸退出了商行,不再妨礙格奧爾格“真正按自己的主意行事”,經(jīng)過(guò)兩年精心經(jīng)營(yíng),商業(yè)成就遠(yuǎn)遠(yuǎn)超過(guò)父親以前的經(jīng)營(yíng)。盡管有矚目成就,但仍未能改善父子之間對(duì)立關(guān)系,反而進(jìn)一步惡化,其原因是格奧爾格訂婚和“不得體的事情”。父親對(duì)格奧爾格說(shuō)道:“自從你親愛(ài)的母親去世后,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好幾起不得體的事情。也許談這些事情的時(shí)候到了,也許比我們想象的要來(lái)得早一些……”父親顯然是在暗示對(duì)格奧爾格婚事安排和商業(yè)的不滿,他被父親掌控的陰影并沒(méi)有散去,這也是他產(chǎn)生不滿的原因之一。
格奧爾格“弒父”行為主要表現(xiàn)在他的無(wú)意識(shí)之中,言語(yǔ)、心理活動(dòng)和簡(jiǎn)單日常動(dòng)作上。如格奧爾格把父親抱在懷里和簡(jiǎn)單地為父親蓋被子動(dòng)作。在一個(gè)上午“暖和”的天氣,格奧爾格把病弱父親抱到床上,并為他蓋上被子。這實(shí)質(zhì)是象征格奧爾格“弒父”動(dòng)作。最后父親看出其意圖,于是把被子掀開(kāi),用手指向天花板,喊道:“你要把我蓋上,這我知道,我的好小子,不過(guò)我可還沒(méi)有被完全蓋上……你出賣(mài)了你的朋友,你把你父親按倒在床上,不叫他動(dòng)彈。可是他到底能動(dòng)還是不能動(dòng)呢?”另外,格奧爾格為父親蓋被子動(dòng)作和父親反復(fù)問(wèn)是否已蓋好,這些實(shí)際是雙關(guān)語(yǔ)句,即“隱瞞”父親,是對(duì)父親反抗的行動(dòng)。
心理上“弒父”幻想。當(dāng)格奧爾格抱起父親時(shí),父親在他懷里玩弄表鏈,從格奧爾格視角來(lái)看,“當(dāng)酷似巨人的父親畏縮在自己的懷里并玩弄自己的表鏈時(shí),即是一種無(wú)可言術(shù)的驚怖”,顯然格奧爾格心理活動(dòng)和現(xiàn)實(shí)實(shí)際表里不一。“現(xiàn)在他的身子將往前彎曲了,要是他倒下來(lái)摔壞了怎么辦”。父親動(dòng)作本意是想讓格奧爾格過(guò)去扶起他,但格奧爾格卻不為所動(dòng),父親有可能摔倒的畫(huà)面在格奧爾格潛意識(shí)中瞬間閃過(guò),卻對(duì)父親不理會(huì),他的潛意識(shí)中允許父親摔倒在地。此時(shí)父親看出格奧爾格的想法,知道格奧爾格有能力向他走來(lái),只因?yàn)樗辉敢饪拷耪驹谀遣粍?dòng)。當(dāng)父親再次憤怒責(zé)備,格奧爾格卻在想“他如果把這些談話公之于世,就會(huì)使父親不再受人尊敬”。接著父親告訴格奧爾格,在彼得堡朋友對(duì)其情況一清二楚,遠(yuǎn)在彼得堡的“他什么都知道,比你清楚一千倍!”格奧爾格聽(tīng)到父親說(shuō)的這些,原本只是想說(shuō)嘲笑父親的話,卻把回答的“一萬(wàn)倍”的語(yǔ)氣說(shuō)得非常嚴(yán)肅認(rèn)真。父親也看出格奧爾格會(huì)說(shuō)出這句話。接著,父親說(shuō)自己一直在給他的朋友寫(xiě)信,知道商店被搶劫一空,一幅落魄、潦倒樣子站在凌亂的商店里。父親覺(jué)得格奧爾格有意等母親去世,不讓母親經(jīng)歷他的大喜日子,而自己則退出商業(yè)后被安排在一間“陰暗”房間里,最后認(rèn)為格奧爾格是一個(gè)沒(méi)有人性的人,判決格奧爾格去投河淹死。格奧爾格被父親趕出房間后在汽車(chē)噪聲的掩蓋之下跳入了河中。
盡管格奧爾格潛意識(shí)中有“弒父”意念,同時(shí)他深知這是一種極為罪惡想法,但在父親威嚴(yán)面前,其“弒父”目的顯然不能實(shí)現(xiàn),他也難以成功做到反抗父親。面對(duì)父親指責(zé),有意識(shí)的盡可能地離父親遠(yuǎn)一點(diǎn),在父親的一步步指責(zé)的壓力下,格奧爾格無(wú)意識(shí)地對(duì)父親指責(zé),但格奧爾格“立刻認(rèn)識(shí)到他闖下了禍,并咬住舌頭……他兩眼發(fā)直,由于咬疼了舌頭而彎下身來(lái)。”格奧爾格在這種自我意識(shí)中表達(dá)對(duì)父親的關(guān)愛(ài)與無(wú)意識(shí)的表達(dá)出對(duì)父親的“弒父”的心理,形成其心中的罪惡之感。
二.對(duì)“權(quán)威”反抗的根源
格奧爾格對(duì)父親有畏懼心理以及潛意識(shí)中“弒父”心理與行為,這種錯(cuò)誤的心理使得他身心背負(fù)一種罪惡感、愧疚感。“父親”為何能宣判格奧爾格死亡呢?“父親”形象其實(shí)在卡夫卡作品中有著象征意義,即“權(quán)威”。文中“父親用一只手輕巧撐在天花板上”動(dòng)作折射出對(duì)格奧爾格審判“父權(quán)”形象,且“疊合著猶太文化中上帝形象的影子”。格奧爾格“弒父”行為是他對(duì)“權(quán)威”的反抗,而反抗失敗必然要面臨來(lái)自“父親”審判,也就是“上帝”的判決。再看看格奧爾格負(fù)罪心理和面對(duì)“弒父”原罪的恐懼心理,加上生活在父親獨(dú)權(quán)掌控的家庭里,當(dāng)聽(tīng)到父親的審判“我現(xiàn)在判你去投河淹死”時(shí),格奧爾格的接受了審判的懲罰,他沒(méi)有足夠的反抗力量,只得在父親形象下做一個(gè)服從“權(quán)威”的角色。
弗洛伊德在《作家與白日夢(mèng)》一文中論述人“幻想”的特征:一個(gè)幸福的人從來(lái)會(huì)不去幻想,只有那些愿望難以滿足的人才去幻想。卡夫卡“幻想”源于其童年時(shí)期,父親赫爾曼在管教上專橫跋扈,缺乏溫和。當(dāng)時(shí)正處于“排猶傳統(tǒng)和排猶情緒”社會(huì)環(huán)境中,父親承擔(dān)家庭的經(jīng)濟(jì)壓力,忙于商店的經(jīng)營(yíng),給卡夫卡關(guān)愛(ài)顯然不夠,對(duì)其態(tài)度也不合理,因而家庭環(huán)境對(duì)其身心產(chǎn)生影響。1913年8月21日,卡夫卡在日記中寫(xiě)下給父親草擬的信,“現(xiàn)在,我生活在家庭里,生活在最好的、最可愛(ài)的人當(dāng)中,但陌生得比一個(gè)陌生人還要陌生。近幾年里,我每天和母親說(shuō)話平均不到20個(gè)字,與父親,在某些時(shí)候頂多只是互換幾句問(wèn)候的話。”日記與《判決》相隔近一年時(shí)間,但是這樣的生活環(huán)境并不是短時(shí)間內(nèi)出現(xiàn)。“為了忘掉我的父親又一次稱我是個(gè)壞孩子這件事,我給自己寫(xiě)下這些。無(wú)論是為了壓抑我,還是假裝地為拯救我……我也許不應(yīng)該將這些寫(xiě)下來(lái)的,因?yàn)槲仪∏“炎约簩?xiě)進(jìn)了對(duì)父親的仇恨中了。”這是卡夫卡1911年10月31日寫(xiě)的日記,內(nèi)容恰好說(shuō)明父親的行為給卡夫卡留下負(fù)面陰影。1919年11月卡夫卡在《致父親》中寫(xiě)道:“你最近曾問(wèn)過(guò)我,為什么我聲稱我在你面前感到畏懼”;“那個(gè)巨大的人,我的父親審判我的法庭,會(huì)幾乎毫無(wú)理由的向我走來(lái),在夜間把我從床上報(bào)到陽(yáng)臺(tái)上去,而我在眼里就是這樣無(wú)足輕重”;“你在我心中產(chǎn)生了一種神秘的現(xiàn)象,這是有暴君共有的現(xiàn)象:他們的權(quán)力不是建立在思想上,而是建立在他們的人身上。”顯然卡夫卡與父親之間有著“代溝”或者互不理解對(duì)方,而且“父親”形象在卡夫卡內(nèi)心過(guò)于高大,甚至帶有粗暴方式。當(dāng)父親責(zé)備卡夫卡時(shí),母親會(huì)在父親面前悄悄保護(hù)他,并私下給卡夫卡某些承諾,以此打消他的反抗心理,遺憾的是母親的保護(hù)行為相反會(huì)給卡夫卡成長(zhǎng)心理帶來(lái)負(fù)面影響。這種保護(hù)和對(duì)父親的畏懼讓卡夫卡產(chǎn)生有罪心理,使得他在父親面前“變成了怕見(jiàn)天日的東西,成了騙子、知罪著,由于自身的毫無(wú)價(jià)值,這個(gè)人連到他認(rèn)為是他的權(quán)利范圍的地方去,也要偷偷摸摸。當(dāng)然我漸漸習(xí)慣于在這些偷偷摸摸進(jìn)行的途中,也順便尋找些即使在我看來(lái)也是我無(wú)權(quán)得到的東西。”
《致父親》信是卡夫卡對(duì)父親的反抗,也是希望能與父親消除隔閡,擺脫父親對(duì)自己的安排,他有自己的生活追求,他深?lèi)?ài)文學(xué)的生活方式。除了《判決》外,《變形記》《審判》等作品中都有“父親”權(quán)威形象描寫(xiě),“都反映出父親的絕對(duì)權(quán)威投射在卡夫卡心靈上的陰影,同時(shí)也表現(xiàn)出卡夫卡通過(guò)藝術(shù)的審美作用來(lái)擺脫權(quán)威的荒誕性的強(qiáng)烈要求”,卡夫卡以文學(xué)藝術(shù)的“超越”來(lái)擺脫被“判決”愿望。
三.《判決》與卡夫卡的“白日夢(mèng)”
按照弗洛伊德觀點(diǎn),“一篇具有創(chuàng)見(jiàn)性的作品像一場(chǎng)白日夢(mèng)一樣,是童年時(shí)代曾經(jīng)做過(guò)的游戲的繼續(xù),也是這類(lèi)游戲的替代物”,可以說(shuō)白日夢(mèng)為作家壓抑心理提供一種宣泄渠道,是人潛意識(shí)外化的一種方式。白日夢(mèng)也就是人的一種幻想,是具有源源不斷的驅(qū)動(dòng)力量,而“幻想的動(dòng)力是尚未滿足的愿望,每一次幻想都是一個(gè)愿望的滿足,都是對(duì)人令人不滿足的現(xiàn)實(shí)的補(bǔ)償。”作家的某些愿望難以企及時(shí),通過(guò)文學(xué)藝術(shù)這一“創(chuàng)見(jiàn)性”的升華補(bǔ)償,從而平復(fù)心中的失落和不滿足愿望。在弗洛伊德看來(lái),文學(xué)藝術(shù)作品實(shí)質(zhì)是一種“幻想”,作者則是一個(gè)“白日夢(mèng)”者,通過(guò)自己理想的愿望以及創(chuàng)作靈感對(duì)“白日夢(mèng)”進(jìn)行創(chuàng)造性改造,在這一過(guò)程中作者會(huì)有意或無(wú)意把自己的潛意識(shí)、愿望融合在作品中的某個(gè)人物或故事情節(jié)中,而作品與作者也就形成密切聯(lián)系。
卡夫卡的經(jīng)歷和心理活動(dòng)與《判決》中格奧爾格較為相像,小說(shuō)的故事情節(jié)和人物心理描寫(xiě)方面投射著卡夫卡的“白日夢(mèng)”愿望,是他的潛意識(shí)的外化和幻想的升華。從格奧爾格與父親的關(guān)系以及他的成長(zhǎng)環(huán)境來(lái)看,他的人格極為脆弱,且不健全。父親告老退居后,格奧爾格成為了家庭的主力,承擔(dān)著家庭的生計(jì),并“以全副精力從事他的商業(yè)以及所有別的事情”。在工作上格奧爾格雖然得到獨(dú)立了,但仍未完全擺脫父親的束縛和影響,而且他長(zhǎng)久以來(lái)在生活上對(duì)事情總是仔細(xì)地觀察,避免被來(lái)自各方面的打擊而出現(xiàn)驚慌失措。盡管有這一想法卻是時(shí)而忘記,又時(shí)而記起。當(dāng)父親道出在彼得堡的朋友現(xiàn)狀的瞬間,格奧爾格的內(nèi)心本能防御被攻破。盡管被“父親”判決跳河,在跳前低聲喊道:“親愛(ài)的父母親,我可一直是愛(ài)著你們的。”從主人公的心理語(yǔ)言和動(dòng)作上看,格奧爾格對(duì)父親雖有畏懼和服從的心理,但對(duì)家人也是懷有關(guān)愛(ài)和付出,他就這樣生活在一個(gè)被動(dòng)的世界與自我幻想的交替之中。
卡夫卡在日記中提到過(guò)那晚寫(xiě)《判決》時(shí)的心理狀態(tài),“當(dāng)故事情節(jié)在我面前展開(kāi)的時(shí)候,當(dāng)我在一處水域中前進(jìn)著的時(shí)候,我正在處于極度的努力和歡樂(lè)之中。在這個(gè)夜里,我好多次地忍受背部的沉重。”卡夫卡在短暫的一夜完成了寫(xiě)作,從他的日記來(lái)看,當(dāng)晚卡夫卡正沉浸于故事情節(jié),進(jìn)入了人物角色的情感當(dāng)中。1913年2月,卡夫卡在日記中再次提到《判決》的寫(xiě)作并簡(jiǎn)略梳理情節(jié)內(nèi)容。身居彼得堡的朋友只是他們父子之間的共同聯(lián)系和共同性,格奧爾格以為自己的成就已經(jīng)贏得了父親。退出商業(yè)的父親也希望能加強(qiáng)自己的地位,并他把自己放在與格奧爾格對(duì)立的位置,以此來(lái)達(dá)到目的。最后逐漸演化為父子矛盾,愈演愈烈。
卡夫卡的作品是精神分析批評(píng)實(shí)踐運(yùn)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之作,而且卡夫卡與弗洛伊德幾乎是同一時(shí)期的奧地利人,至于弗洛伊德是否認(rèn)識(shí)卡夫卡無(wú)從得知,但他的“精神分析學(xué)”研究成果明顯早于卡夫卡的創(chuàng)作。在《判決》完成寫(xiě)作后的上午,卡夫卡在日記中提到了寫(xiě)作感想和弗洛伊德,“許多寫(xiě)作的時(shí)候一起出現(xiàn)的情感,比如歡樂(lè),我已為馬克斯的《阿爾卡迪亞》有了一些美好的設(shè)想,當(dāng)然也想到了弗洛伊德……”顯然卡夫卡對(duì)弗洛伊德是有一定的了解。此外,在日記中卡夫卡多次寫(xiě)到自己的“夢(mèng)境”,從弗洛伊德夢(mèng)的解釋來(lái)看,夢(mèng)即指潛意識(shí)中的欲望,也是“幻想”的滿足過(guò)程。而夢(mèng)中父親“冷酷無(wú)情”,不幫助卡夫卡,映射著卡夫卡眼中的父親,也是潛意識(shí)中對(duì)父親的不滿與反抗。盡管《判決》是一個(gè)怪誕結(jié)局,但這個(gè)“白日夢(mèng)”是卡夫卡在幻想的動(dòng)力下,是他實(shí)現(xiàn)“自我滿足與充當(dāng)旁觀者的角色”的一種藝術(shù)升華。
精神分析批評(píng)并沒(méi)有忽略社會(huì)性的因素,在人文學(xué)科領(lǐng)域仍然廣泛運(yùn)用,從這一角度來(lái)分析文本更能對(duì)作家的創(chuàng)作心理過(guò)程有深刻認(rèn)識(shí),理解文本的深層隱喻。《判決》作為卡夫卡的“白日夢(mèng)”,格奧爾格的潛意識(shí)活動(dòng)和“弒父”心理映射著卡夫卡內(nèi)心幻想,他們?cè)跐撘庾R(shí)中反抗“父權(quán)”根源主要是家庭的因素和被“父權(quán)”壓抑之下而產(chǎn)生,形成了“俄狄浦斯情結(jié)”的心理,文本映射的“白日夢(mèng)”正是作者“幻想”的滿足。
參考文獻(xiàn)
1.張春興:《現(xiàn)代心理學(xu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車(chē)文博主編:《弗洛伊德文集》第四卷,長(zhǎng)春:長(zhǎng)春出版社。
3.卡夫卡著,葉延芳主編:《卡夫卡全集》,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
4.卡夫卡著,張榮昌譯:《致父親:天才卡夫卡成長(zhǎng)的怕與愛(ài)》,廣西: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2004年5月。
5.李曉娟:《卡夫卡筆下的父親形象》,《大眾文藝》2009年03期。
6.楊恒達(dá)著:《卡夫卡》,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
7.卡夫卡著,葉延芳.黎奇譯:《致父親》,北京:華文出版社,2017年6月。
(作者單位:三峽大學(xué)文學(xué)與傳媒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