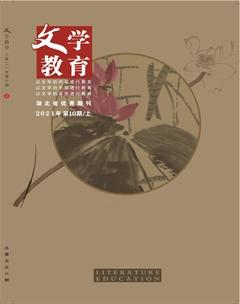《詩經(jīng)·木瓜》主旨論析
楊敏
內(nèi)容摘要:《詩經(jīng)·木瓜》的主旨歷來爭辯不一,如有“美齊恒公” “諷衛(wèi)人以報齊”“贈答結(jié)好”“薄施厚報”等;而考論“木瓜”等名物,可知其乃一類可食用的瓜果,且此類瓜果與玉皆含有兩性生殖、男女情愛的文化意蘊,結(jié)合周代禮俗,又可知“投瓜報玉”的行為符合周代男女互贈禮俗的特點,是古代男女愛情生活中常見的文化現(xiàn)象,故可明此詩乃男女相互贈答之愛情詩。
關(guān)鍵詞:《詩經(jīng)·木瓜》 愛情詩 生殖崇拜 婚戀禮俗
《木瓜》共三章,雖耳熟能詳,但為了解詩方便,亦茲錄全詩: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1]100!
詩歌聚焦一對青年男女互贈信物的場景,展示了一幅古代青年選擇對象傳遞情意的極富情趣的景象:詩歌沒有對女子的面部作細致的刻畫,卻透過她的動作依稀看到了一個大膽、熱情、美麗的女子情竇初開時的悸動,面對欣賞愛慕之人,大膽示愛的勇氣與嬌矜。眼前仿佛出現(xiàn)了這樣一副畫面:女子見到帥氣的小伙,向他投去充滿愛意的一個木瓜,隨即又羞澀地低下了頭,靜靜地等待著男子的應(yīng)答。看到美麗的女子緋紅的臉頰,男子似乎被愛神之箭射中,激動與興奮不能自禁,他也忙不迭地解下佩飾,雙手獻上瓊玉回贈姑娘,表明自己愿與女子永結(jié)為好的心意。
一.《木瓜》主旨概說
《木瓜》的詩旨可主要分為三類:一類“美刺說”。“美”——“美齊恒公”[3]16,“刺”——刺衛(wèi)人以報齊、刺送禮行賄。或以為美或以為刺,都是從政治層面考量附會史事解說詩歌主旨,故此種說法雖影響深遠,卻與不能成為主流。如“衛(wèi)人以報齊國”一說,程俊英就對“齊恒公救衛(wèi),衛(wèi)人思報而作此詩”的史事存疑,認為“全系穿鑿”[1]100,更勿論“諷刺衛(wèi)人以報齊”之說。《詩序補義》中,清人姜炳璋也從語意出發(fā)明確此詩“有感徳之深情,無風(fēng)刺之微意”[3]85。至于“諷送禮行賄”一說,孔穎達以為贈人果實必須包裝起來,人們在人際交往中互贈禮物,但禮物越來越厚重,就有“厚賄”之嫌。此說仍免不了與詩文本相背離,附會牽強,不過有益教化。另一類是“結(jié)好說”。對投桃報李的對象存在分歧。有以為男女贈答結(jié)好,有以為朋友互贈結(jié)好。《詩序》“美齊恒公”因循甚久,到南宋時,朱熹疑此詩為“男女相贈答之辭”[1]48,而這種脫離《序》附會史事,妄生美刺的釋《詩》方法,實開“贈答結(jié)好”的先河。朱熹可說是首倡“就詩論詩”,注意把握詩歌的文學(xué)特點,這也啟發(fā)后之學(xué)者顛覆舊說,開拓新的解經(jīng)路徑,于后世影響深遠。程俊英、聞一多、余冠英亦從此說。“朋友互贈結(jié)好”說的產(chǎn)生實是在朱熹“男女贈答之辭”的基礎(chǔ)上衍化而來,卻無其它鮮證。最后一類是薄施厚報說。此說主要還是受“斷章賦詩”的影響,有鮮明的時代性。宋代楊簡《慈湖詩傳》從此說,以為乃“薄來厚往之意”[1]67。
總的來說,自先秦兩漢至朱熹前,《木瓜》詩旨以《詩序》“美齊恒公”為主流,受“斷章賦詩”的影響,間時有詩家闡發(fā)新論:或諷衛(wèi)人以報齊,或刺送禮行賄,或為薄施厚報之詩,直到朱子“疑亦男女相贈答之辭”[4]48雖然只是寥寥數(shù)字,但其影響卻甚為深遠。后之學(xué)者多沿襲此說,且衍生以為“朋友相贈答”。雖說詩無達詁,但考辯“木瓜”“木桃”“木李”等名物,從生殖崇拜角度分析名物以及贈玉文化的象征意義,再結(jié)合周代禮俗分析“投瓜報玉”行為與古式社會男女婚戀禮俗的關(guān)聯(lián),可略索得《木瓜》乃男女贈答之愛情詩較貼合詩歌主旨。
二.“木瓜”“木桃”“木李”名物辨
《木瓜》詩旨聚訟紛紜,對“木瓜”“木桃”“木李”等名物也爭論不一。或可說是因為名物不清影響詩歌題旨分析。鄔文清以為木瓜、木桃、木李是象征愛情的木刻雕飾、王力先生、余冠英等則倡“木桃,就是桃”“木李,就是李子”,而趙民樂所持“木桃就是樝子、榠樝即是木李”[6]之論頗值得我們注意。翻閱典籍,考索“木瓜”“木桃”“木李”等名物的形狀、果實大小口感、生長境地分布等情況,并結(jié)合《詩經(jīng)》重章復(fù)沓、同類異辭的文法句式邏輯,“木桃就是樝子”“榠樝即是木李”這種對《木瓜》中名物的注解較貼合詩歌文本的解讀。
木瓜今舊名未變,與郭璞《爾雅》所說形態(tài)相合,故木瓜爭議不大,從舊說。但仍要注意區(qū)分《木瓜》中所說“木瓜”不是今日所言番木瓜。《<詩經(jīng)·木瓜>解碼》一文就將二者相混淆。此文佐證部分舉《海南植物志》為證,謂木瓜是“番木瓜屬”,生長在“熱帶美洲,現(xiàn)在廣泛植于熱帶地區(qū)”[7],“《木瓜》出自‘衛(wèi)風(fēng)而‘衛(wèi)風(fēng)之‘衛(wèi)在今河南淇縣,不屬我國南部,也不是熱帶地區(qū),產(chǎn)不出木瓜[7],”其以此為一證,論說《詩經(jīng)》中的“木瓜”是木刻的佩飾“假果”“玩具”。孰不知,此文所說木瓜乃今人平日所食用的一種熱帶水果——番木瓜。番木瓜與《詩經(jīng)·木瓜》中的木瓜實不可混為一談。“今日各地所言之木瓜,原產(chǎn)于美洲熱帶,17世紀(jì)末才引入中國,正確名稱應(yīng)為番木瓜”[8]388。《詩經(jīng)·木瓜》中的木瓜與《本草綱目》《果譜》中所指之物同。《本草綱目》中載,木瓜是春末時節(jié)開花,色深紅[9]與花色為乳白色和黃白色之番木瓜又不同,且木瓜生境分布在我國西南、中部絕大數(shù)地區(qū)。《果譜》“葉光而厚,春末花開,紅色微白,實如小瓜,或似梨稍長,色黃如著粉,津潤不木者為木瓜”[10]。屬于薔薇科木瓜屬,灌木或小喬木,又叫鐵腳梨樹,可以食用或作藥用,“津潤不木”可知口感尚佳,亦有謂其果味酸。
木桃與木李屬同類,都是木瓜的一種,只不過在口感、大小等方面有所差異。《毛詩稽古編》云:“木瓜之圓而小,味酸澀者為木桃,其大而黃,蒂間無重蒂者為木李”[11]391。木桃、木瓜多別名,又或因流傳久遠,故人們多混淆或不識了。“木桃又名楂子,《雷公炮炙論》謂之‘和圓子。木李又名榠楂,陶隱居云‘山陰多木瓜,人以為良果,又有榠楂大而黃,又有楂子小而澀。《禮記》云:‘楂、梨鉆之。古亦以此為果。鄭玄不識以為梨之不臧者,是已木桃下于木瓜、木李,又下于木桃二者之外又有榅桲,生于北地蓋榠楂之類,與林檎相似而異物,三者皆與木瓜同類;但木瓜得木之正氣,故貴之”[11]391。可知,木桃、木李皆屬木瓜類,相似度極高,三者之難辨也,但亦有著優(yōu)劣等級之細微差異。
綜上可知“木桃就是樝子”“榠樝即是木李”,此種對《木瓜》中名物的注解才是較符合科學(xué)的正確的解讀,也符合《詩經(jīng)》重章復(fù)沓、同義異辭文法句式邏輯之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木瓜,美而且大者也。木桃,次之。木李,又次之”[12]606。“瓊琚,玉也。瓊瑤,石之似玉者也”[12]606。“瓊玖,石之次于瓊瑤者也”[12]606。
三.瓜果名物和玉含有兩性生殖、男女情愛之文化意蘊
古式社會的先民們,禮物贈予的終極指向不是具體的物質(zhì)性回禮,而是通過禮物交換這種方式建立或延續(xù)雙方之間的紐帶關(guān)系。為此,在禮物交換中,交換雙方看重的并非物品本身所具有的價值,而是物品本身所融合著贈禮者的友好情感,抑或是自身文化對物品含義的定義[13]。此處《木瓜》中的“木瓜”等瓜果,“瓊琚”等,就有著先民對它們所賦予的特殊意義。
先論瓜果。從已知的文獻記載來看,木瓜實亦是一類多籽(子)的瓜果。考索《詩經(jīng)》全書可以發(fā)現(xiàn)在古式社會初民的原始思維中,有將多子的瓜瓠與女性繁衍相聯(lián)系,寄寓多子多孫的愿望。《詩經(jīng)·大雅·綿》有云:“綿綿瓜瓞”[1]413。瓜,指大瓜;瓞,瓜也;《毛傳》:“綿綿,不絕貌”[14]703,意即連續(xù)不斷,此處用瓜的綿綿不絕比喻兒孫滿堂,世代興盛。承襲這一文化象征,古代七夕祭祀儀式和風(fēng)俗中,婦女們不以魚肉犧牲作為祭品,而代之以瓜果麥豆等農(nóng)作物。七夕時“婦女陳瓜果于庭中以乞巧”[15]434;“以瓜果祭于月下,用花針七口穿五色花線插瓜上,謂之乞巧”[15]434。婦女緣何為此?是有意向“主瓜果”的生殖神祈盼多子多孫,瓜瓞綿綿。后世“送瓜祈子”的習(xí)俗也與此有關(guān)。有些地方有送瓜的習(xí)俗,特別是結(jié)婚多年而未孕的婦人,則親友們必然會有送瓜的行為。在一些民族的刺繡和剪紙上,也會常見一些構(gòu)圖將瓜與孩童相伴組合出現(xiàn)在一幅作品中。如一個娃娃站在一個裂開的瓜瓤上,瓜的兩旁枝蔓纏繞,這實際上也展現(xiàn)了祈愿兒孫滿堂、世代延續(xù)的民俗心理。
再說玉。《詩經(jīng)》中玉具有多種象征意蘊,如以玉比人,象征君子美好道德品格;也有將玉作為男女報答定情的信物,象征男女堅貞不渝的愛情。而將玉作為男女報答的信物則與男性生殖器的崇拜有關(guān)。在《詩經(jīng)》的“玉文化”研究發(fā)現(xiàn)古式先民把山峰、石柱等高聳直立之物與陽具作比,男贈女以玉的風(fēng)俗習(xí)慣就是生殖器崇拜之下的一種表現(xiàn)形式。《詩經(jīng)·斯干》即是玉與男性生殖器崇拜相聯(lián)系的鮮證。從“載衣之裳,載弄之璋[1]300”的注疏來看,玉璋即是男性的標(biāo)志。
故而可見此之瓜果、玉是蘊含著表示兩性生殖、男女情愛的特殊之象征意義。
四.“投瓜報玉”——先秦婚戀禮俗中的贈遺之風(fēng)
《禮記·曲禮》云:“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16]。”《詩經(jīng)》中“投瓜報玉”的行為與先民之禮俗有著緊密的關(guān)聯(lián)。聞一多認為原始社會要獲得食物,常根據(jù)“兩性體質(zhì)所宜,分工合作”錯誤!未找到引用源。143男人負責(zé)狩獵,女人負責(zé)采集,故蔬菜瓜果一般為女子所擁有。結(jié)合人類文化學(xué)和民族學(xué)的知識,可知男女分工的不同產(chǎn)生了最初的交換行為,并演變?yōu)樵嫉娘L(fēng)俗習(xí)慣。古時男女分工一般是男在外狩獵,女子則負責(zé)從事采集瓜果的工作。而隨著社會的進步,男性狩獵工具由最初的石斧、石刀逐漸演變?yōu)槭謭?zhí)的玉器。以至到后來,男女見面交換禮物時就將手中的工具作為交換,久而久之逐漸形成男贈女以玉佩,女贈男以瓜果的風(fēng)俗習(xí)慣。并且這種風(fēng)俗逐漸融入滲透到日常生活中,經(jīng)過統(tǒng)治者的改造與利用演變?yōu)橘椧姸Y。《禮記·表記》:“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16]873。人們交互往來必須要有“禮”。鄭玄云:“禮,謂摯也”[17]386。“摯”是指見面時送人的禮物。發(fā)展到后來的婚禮贄見禮,女子拜見公婆,必須用棗栗、段修以見。可見后世互贈的禮俗也保留了最初的一些風(fēng)俗習(xí)慣。
《木瓜》中的“投瓜報玉”的行為正符合此種禮俗特點,并漸漸發(fā)展為一種贈遺之風(fēng),《詩經(jīng)》中就有大量贈瓜果花草以起興達情,男子報玉結(jié)情的詩句,例如:女子贈瓜果花草“靜女其孌,貽我彤管”[1]64“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1]140“視爾如荍,貽我握椒”[1]204等等。男贈女玉有“彼留之子,貽我佩玖”[1]114“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1]127!從中也不難窺見古時先民愛情生活中的贈遺之風(fēng)。
《木瓜》詩旨變動不居,因時、因事、因人而變,“詩無達詁”[19]157亦為確論。但從文本內(nèi)部出發(fā),從文化視角著手,再結(jié)合先民禮俗以禮說詩,無疑為最能貼近詩歌主旨的途徑之一。
盡管歷來對此詩的主旨理解多附會史實,或以為美,或以為刺,或感人之恩,厚以為報,但從詩歌中反復(fù)提到的“木瓜”“木桃”“木李”等名物的辨正中,卻可明確其不但為一種可食用的瓜果,而且潛含兩性生殖、男女情愛的文化意蘊,結(jié)合周代先民禮俗,明確“投瓜報玉”的行為實與周代男女互贈禮俗特點相符合,故不難窺見此詩主題,即是男女贈答之愛情詩。
參考文獻
[1]程俊英.詩經(jīng)譯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7(2004.12重印).
[2][周]卜商.詩序[M].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總第69冊).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6.
[3][清]姜炳璋.詩序補義[M].影印文淵閣四庫(總第89冊).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6.
[4]朱熹.詩經(jīng)集傳[M].岳麓書社,1994.
[5][宋]楊簡.慈湖詩傳[M].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總第73冊).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6.
[6]趙民樂.木瓜·木桃·木李——談《詩經(jīng)·風(fēng)衛(wèi)·木瓜》中三個名物[J].教學(xué)與進修,1981(01):74-76.
[7]鄔文清.《詩經(jīng)·邶風(fēng)·木瓜》解碼[J].齊齊哈爾大學(xué)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2000(06):50-52.
[8]潘富俊.草木緣情——中國古典文學(xué)中的植物世界[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16.
[9][明]李時珍.本草綱目第三卷[M].吉林大學(xué)出版社,2009.
[10][清]汪灝.御定佩文齊廣群芳譜 果譜[M].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總第845冊).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6.
[11][清]陳啟源.毛詩稽古編[M].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總第85冊).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6.
[12][宋]蔡卞.毛詩名物解[M].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總第70冊).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6.
[13]馬賽爾·莫斯.禮物——古式社會中交換的形式與理由[M]商務(wù)印書館,2019.
[14][漢]毛亨,鄭玄,[唐]孔穎達.毛詩注疏[M].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總第69冊).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6.
[15][清]李光地.御定月令輯要[M].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總第467冊).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6.
[16]楊天宇.禮記譯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11(2018.11重印).
[17]聞一多.古典新義.詩經(jīng)通義[A]聞一多全集第二卷[M].上海:三聯(lián)書店,1982.
[18][東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注疏[M].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總第116冊).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6.
[19][漢]董仲舒.春秋繁露[M].鄭州:河南大學(xué)出版社,2009.
(作者單位:重慶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