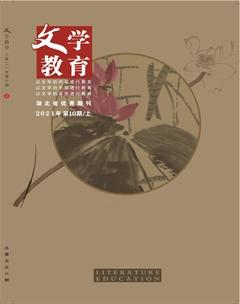電影《喜福會》中的疾病表征與主題表達
內容摘要:電影《喜福會》講述了四對母女的故事。每個故事都是以母親一代的悲劇開始,以女兒一代的喜劇結束,其中總有一個明顯的疾病表征。疾病暗指了歷史戰爭、婚姻制度、封建禮教、傳統道德等給中國女性帶來的精神之殤,同時也展現了她們在重重壓迫下不斷反抗的勇氣和智慧。
關鍵詞:《喜福會》 母女 疾病 主題
《喜福會》是美國華裔女作家譚恩美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也是她的成名作。1989年,該書一出版即大獲成功,被列入《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長達9個月之久。1990年,該書又先后獲得了洛杉磯圖書獎、全美圖書獎等多項文學大獎,在全世界引發強烈反響。1993年,美籍華裔導演王穎將這部小說改拍成了同名電影,并于同年獲得柏林電影節“銀熊獎”。2020年12月,電影《喜福會》成功入選美國《國家電影名冊》(National Film Registry),作為“對國家電影產業的文化、歷史和美學產生重大影響力”的25部影片之一,被永久保存在美國國會圖書館,成為國寶級文化作品。
《喜福會》講述了四個在中國出生長大的母親背負著各自的痛苦創傷,飄洋過海來到美國,與自己在美國出生長大的女兒打破重重隔閡、共同尋找幸福的感人故事。影片的開頭是一個其樂融融的家庭聚會,四個在美國生活的華人家庭齊聚一堂,為了一個共同的主題:送君尋親。原來君的母親素云已經離世,但君在中國還有兩個從未謀面的姐姐。在母親好友的幫助下,君得知了姐姐們的消息,于是決定遠渡重洋回中國尋親,這個聚會就是為她送行的。在聚會上,大家感慨萬千,分別陷入了對往事的回憶之中,而四對母女之間的陳年恩怨也徐徐鋪展開來。在這四組如同拉家常一般的講述中,疾病是一個常見卻又常被忽視的現象。然而,“疾病自從在文學作品中出現的那一刻起,就已經脫離其自身而成為一個社會文化的問題。”[1]在影視作品中亦是如此。電影《喜福會》中的疾病表征不僅在推進情節發展、構建人物形象、營造悲劇氣氛、增強故事張力等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同時豐富了影片的主題,具有深刻的社會文化內涵。
一.痢疾·棄子·戰爭之殤
吳素云是君的母親,她的故事發生于抗戰時期的舊中國。素云在戰亂中遺棄了自己尚在襁褓里的雙胞胎女兒,后來幾經輾轉來到美國,成立了新的家庭并生下了小女兒君。她一心想要女兒出類拔萃,希望頗有音樂天賦的君能成為“華人界的鋼琴奇才”。但是母親過高的期待卻成為了女兒的巨大壓力和無形枷鎖,在一場失敗的鋼琴表演之后,母女關系徹底僵化。面對強勢逼迫自己練琴的母親,君哭喊道“我希望我死了,就像你在中國害死的孩子一樣……”君曾聽說過母親丟棄了兩個女兒,并對此耿耿于懷,認為母親自私狠心、不可原諒。聽了君的哭訴,素云震驚了,但她沒有任何解釋,用沉默應對女兒的憤怒。“棄子事件”成為母女之間的一堵墻,直到素云去世后,君仍然認為自己并不了解母親。
后來在父親的講述中,君才明白了母親的棄子之痛。影片展現了素云在日本侵華戰爭攻打桂林時的逃難經歷。在滾滾逃難人流中,素云步履蹣跚地推著獨輪車里的雙胞胎女兒,打算到重慶去尋找丈夫。途中她患上了嚴重的痢疾,破舊的獨輪車也壞了。目睹著橫尸遍野的場景,素云在絕望中把雙胞胎放在路邊,并將隨身攜帶的所有金銀細軟留給這對女兒,希望好心人能收養她們。“安頓”好孩子之后,奄奄一息的素云獨自離開,想找個僻靜的地方等死,因為她認為孩子身邊有一個身染重病的母親是不吉利的,會減少她們被收養的機會。后來,素云陰差陽錯地獲救了,兩個女兒卻從此杳無音訊。移居美國后,她仍然不放棄尋找女兒的希望,但始終無果。這種骨肉分離成為素云一生的心病,她對此一直念念不忘,最終帶著遺憾離世。
自此,君才明白了母親當時的“棄子”之舉是懷著怎樣無奈的絕望和苦痛,事后又忍受了怎樣刻骨的思念和煎熬。她多年來對母親的誤會終于化解,也理解了母親對自己沉重的期望背后其實飽含了對三個女兒的愛。最后,君去上海見到了同母異父的雙胞胎姐姐,彌補了母親生命中最大的遺憾。
素云的故事從離散開場到團圓結束,其中,“痢疾”是一個重要的疾病表征。痢疾是一種由細菌引起的急性腸道傳染病,以痢下赤白膿血、發熱、腹痛、腹瀉、里急后重為癥狀。我國清代孔毓禮在專著《痢疾論》中寫道“瘟疫而外,惟痢疾最險惡,能死人于數日之間”。[2]電影中吳素云患痢疾于戰亂之時。雖然影片中沒有正面描寫血腥的戰爭場面,但是疾病之“險惡”映襯了戰爭之“險惡”,二者都是在猝不及防時對生命進行摧毀與踐踏。在朝不保夕的逃亡途中,身患惡疾的素云為了“救子”而“棄子”,凸顯了母性的光芒與力量。“痢疾”在《喜福會》中不僅僅是一種身體疾病,也暗指戰爭之殤,揭示了日本侵華戰爭給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同時它也助力塑造了一位在戰爭與疾病的雙重迫害下勇敢無私的中國母親形象。
二.抑郁·殺子·婚姻之痛
《喜福會》中顧映映和麗娜母女的故事體現了不同文化背景下女性在錯誤婚姻中的掙扎與反抗。年輕時的顧映映是一位大家閨秀,情竇初開的她愛上了一個風流倜儻的男人。二人赴宴共舞,情意纏綿,喜結連理。然而這場貌似美滿的婚姻卻成為映映愛情的終結和噩夢的開始。婚后丈夫原形畢露,從孩子滿月酒宴上公開與歌女調情,到夜不歸宿;從公然將歌女帶回家,到惡毒地辱罵妻子,這個魔鬼般的男人一步步地把映映推向絕望的深淵。原本明艷如花的她越來越抑郁,越來越枯萎。影片中雖然沒有明確提及“抑郁癥”這三個字,但鏡頭里多次呈現出映映的抑郁表征。
電影中連續展現了映映坐在飯桌前等待丈夫回家用餐的三個情景。從衣著華美、妝容精致,到身穿睡衣、披頭散發,再到長發凌亂、眼眶紅腫,映映外貌上的變化表現了她從滿懷希望到心灰意冷再到悲傷絕望的心理變化。這是抑郁癥“情緒低落”的早期征兆。[3]之后,映映等到的是丈夫和歌女相擁而來,以及丈夫的推打謾罵。不堪其辱的映映摔碎盤子想要自殺,卻遭到丈夫變本加厲的斥責,她只得跪在地上收拾碎片,無聲哭泣。如果說映映的自殺念頭是抑郁癥的隱形表現,那么她的“殺子”行為則是這一疾病的最后“確診”和慘痛結果。面對殘暴無情的丈夫,映映終日沉浸在悲傷、絕望、仇恨的心情中。一天,她在給兩三個月大的兒子洗澡的時候,想起了丈夫的種種惡行,產生了報復他,奪走他最寶貴的東西的念頭……恍惚間她將孩子沉入盆底。等她回過神來的時候,孩子已經溺水而死。抱著兒子小小的身體,映映發出凄厲的尖叫。
顧映映的抑郁癥凸顯了舊中國封建社會中夫權男權對女性的摧殘與壓迫。“殺子”是抑郁癥發展到最嚴重程度的表現,同時也是女性反抗力量的表達。在中國,子嗣傳承,極其重要。丈夫雖然對映映冷酷殘忍,卻視兒子為驕傲。兒子響亮有力的哭聲,在他看來是自己男性力量的繼承。作為暴力的男權體制的受害者,殺死兒子,奪走丈夫最在意的東西,幾乎是顧映映在有限的范圍內,能做到的最大力度的報復和反抗了。然而,作為母親,殺死自己的親生骨肉,也成了映映生命中難以承受之痛。雖然后來映映移民美國、再婚并生了女兒麗娜,但她卻始終不能忘記被自己溺死的孩子。她常常陷入痛苦的回憶中難以自拔。電影鏡頭里晚年的顧映映穿著白色睡衣,短發凌亂、目光呆滯,滿臉淚痕,抑郁的神態比之前更加令人哀嘆。
沉湎于往日傷痛的映映習慣于隱藏傷口,和女兒之間交流甚少。她認為麗娜是一個“沒有靈魂的人”;而在麗娜眼中,母親是一個充滿不安和恐懼的怪人,總是精神恍惚、不知所措。這種疏離的母女關系一直持續到麗娜婚后。麗娜的丈夫哈羅德堅持賬務均攤,每一筆日常開銷都算得一清二楚。麗娜內心非常抗拒這種不近人情的做法,但是始終沒有勇氣表達自己的真實想法。麗娜的遷就順從使虛偽吝嗇的哈羅德更加斤斤計較。映映目睹了女兒的婚姻狀況,敏銳地覺察到了隱藏在生活平靜表面下的危機。她從麗娜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那個在不平等的婚姻里屈從和忍耐的自己。最終映映主動打破沉默,用自己的故事喚醒女兒,鼓勵她離開那幢“傾斜的房子”,重新追求幸福。在母親的引領下,麗娜結束了這段畸形的婚姻,找到了一個珍視自己的男友,開始了新的感情生活。
映映的故事起初是悲慘壓抑的,所幸的是她經歷的磨難最終變成了寶貴的經驗和智慧。映映以母愛為治愈力量,在幫助麗娜走出不幸婚姻的同時,也把自己從抑郁的泥沼中解救了出來。看著女兒重獲幸福,映映的臉上出現了久違的笑容。這笑容標志著她對過去的釋懷,以及跟自己的和解。困擾她半生的抑郁終于在笑容中日漸消弭。
三.侍疾·救母·親情之重
安梅是素云和映映的好朋友,影片通過安梅的回憶,講述了安梅母親的悲慘故事。安梅的父親早逝,漂亮的母親一直恪守婦道。不料她被已有三房姨太太的富商吳青看上,吳青的二太太把她騙上門打麻將,隨后她被吳青強暴懷孕。安梅的母親因為打破了為亡夫終身守寡的中國封建傳統而遭到娘家人的唾棄、謾罵。外婆和舅舅舅媽以敗壞門風的罪名把懷有身孕的母親逐出家門,并以會“帶壞”女兒為由剝奪了她撫養安梅的權利。走投無路之下母親投靠吳青,做了地位低下的四太太。數月后,她生下了吳青唯一的兒子。可是孩子剛出生就被陰險狡詐的二太太搶走撫養,成了二太太的兒子。原來當初二太太幫吳青設下圈套霸占安梅母親,就是為了使其懷孕然后奪子,以鞏固自己在吳家的地位。
先后失去女兒和兒子的母親在吳青家過著凄苦孤寂的生活。母親的悲劇表現了封建禮教對女性的壓迫和侵奪。在等級森嚴、男尊女卑的封建社會,摧殘女性的不僅僅是以吳青為代表的男性權勢者,還有受封建意識毒害的女性自身,如外婆、舅媽、二太太等。其中外婆對母親的傷害最令人唏噓。身為母親,外婆在女兒遭受強暴、痛苦無助的時候非但沒有保護她、安慰她,反而將她永遠趕出家門。外婆的絕情之舉反映了其自然母性的泯滅,揭示了內化于心的封建思想對親情的破壞。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女人必須從一而終;一座座貞節牌坊立在民間,也立在人們的心里。安梅的母親遭陷害被玷污,成了“不守婦道”的女人,使家族蒙羞,此時外婆從母親的身份中抽離出來,做了封建道德禮教的捍衛者,做了將女兒推向悲慘生活的幫兇。
母親被趕走之后,年幼的安梅生活在舅舅家,外婆和舅舅舅媽不允許母親探望她,她的童年在等待母親的煎熬中度過。后來外婆重病不治,母親匆匆趕回家,割下自己胳膊上的肉熬湯給她喝。這是當地的風俗,據說只有至親骨肉,割肉救母,母親的病才能好。鏡頭里昏暗的燈光、鋒利的尖刀、流淌的鮮血構成了影片中最令人觸目驚心的一幕。這一情節不僅包含著豐富的民間文化信息,展現了中國傳統的孝文化,同時具有很強的隱喻意義。外婆的“病”隱喻了“吃人”的封建禮教;母親的“藥”暗指弱勢者單方面的義務。不久外婆病逝,母親通過自我犧牲也沒能挽回失去的親情。
母親處理完外婆的喪事離開舅舅家的時候,安梅決定跟母親走,她渴望回到母親身邊。在吳青家里,安梅了解了母親作為小妾的卑賤處境。而母親在享受了與女兒團圓的短暫喜悅之后,又要忍受吳青對女兒的輕視以及二太太對她的刻意拉攏。為了保全安梅在吳家的地位,母親選擇在小年夜服毒自殺。吳青信鬼神,怕母親的鬼魂回來找他,就把母親奉為大太太,還承諾善待安梅,扶養她長大。母親以自我犧牲的方式換來安梅的生活保障,卻讓她承受了永失至親之痛。
安梅后來輾轉到了美國,生了自己的女兒露絲。露絲自信獨立,獲得了出身高貴的大學同學特德的青睞。特德不顧家人反對與露絲結婚。嫁入豪門后,露絲處處以丈夫為中心,放棄讀研深造的機會,全心全意操持家務,自身的光芒逐漸消失。厭倦了妻子的沉默謙卑,特德提出離婚。安梅看到女兒消沉的樣子,向她講述了自己母親的故事,教育她不能像上一輩那樣一味地自我犧牲,要認識到自己的價值。露絲被母親的話觸動,與丈夫坦誠交流、表現真我,重新贏得了他的尊重和欣賞。最終兩人解開心結,和好如初。
《喜福會》中安梅的故事實際上是四代人的故事。安梅的母親“割肉救母”卻無力回天,“自殺助女”卻加重了女兒的痛苦。影片通過安梅母親的悲劇傳遞了這樣一個觀念——親情的維系需要雙方自然樸素的愛,單方面的付出和犧牲會使感情的天平失衡傾斜直至倒塌。后來安梅與露絲合力挽救婚姻危機是對上兩代扭曲失重的母女關系的改寫和撥正。
四.裝瘋·尋母·自由之路
林多是四位中國母親中最無所畏懼、敢于反抗的一個,她的故事在影片回憶部分暗沉的基調上增添了一抹亮色。林多出生在北方農村的一戶窮苦人家,母親希望她通過婚姻改變命運,過上比自己好的日子。母親在林多四歲時就通過媒人為她定下娃娃親,把她許配給地主黃家做童養媳。電影用幾個鏡頭表現了母親對林多的疼愛——吃飯時把自己的菜夾到林多碗里,溫柔地幫她擦去臉上的泥垢,給她梳頭時告訴她她的耳朵長得有福氣,以后一定會過得好。林多明白母親的愛和期待,并暗下決心要實現母親的愿望。
林多15歲那年家鄉鬧水災,全家被迫南遷,只有林多被留下來,嫁入黃家,自此和母親天各一方。新婚之夜林多才發現丈夫是一個比她還年幼的傻小子,根本不通男女之事。他命令林多睡在地板上,拿出蜥蜴嚇唬她,門外的媒婆聽見林多的尖叫滿意地笑……這些讓人啼笑皆非的畫面充分展現了封建時期包辦婚姻的荒謬。由于小丈夫的吹噓和謊言,一心想抱孫子的黃太太把不能懷孕的過錯全部歸咎在林多身上,動輒對她打罵泄憤。她被灌下中藥、禁足室內,在傳宗接代“任務”的壓迫下艱難度日。
一天,林多在無意間得知家中女仆懷上了小鞋匠的孩子,而鞋匠卻拒不承認之后,想到了一個“調包計”。她弄亂頭發,劃破衣服,厲聲尖叫,成功地吸引了婆家人的注意。在眾人的圍觀下,“瘋瘋癲癲”的林多開始了籌謀已久的“表演”。她用一個噩夢,三個“不祥預兆”和女仆腹中的孩子,讓婆家人相信了她和小丈夫的婚姻是受到老祖宗詛咒的,將會給黃家帶來滅頂之災,而女仆才是小丈夫的“真命天女”,會為黃家綿延子嗣。就這樣,黃太太得到了孫子,女仆得到了婚姻,而林多得到了一張去上海的火車票。雖然影片沒有更多的交代,但是聯想到之前的舉家南遷,我們有理由相信林多奔赴上海是為了追尋母親的蹤跡,追尋她一直念念不忘的溫情。
這場“裝瘋”的鬧劇是影片中最有喜劇色彩的一幕。作為童養媳的林多在婆婆家一直處于“失語”的狀態,婆婆的強勢蠻橫自不用說,就連小丈夫也煞有介事地“告誡”她:“我是丈夫,是當家的,一切由我說了算”。因此,她只能任由丈夫“栽贓”和婆婆斥責,卻無法訴說自己不孕的真相。然而,地位低下的林多通過“裝瘋”獲得了話語權,她看似荒誕不經的“瘋言瘋語”是對封建婚姻制度和傳宗接代思想的反抗和戲弄。“女性瘋狂既是父權壓迫的結果,也是女性在父權社會里的一種生存策略和反抗方式。”[4]林多瘋癲的表象下是強烈的自我意識和清醒果斷的頭腦;相反,婆家人霸道強勢背后是迷信無知和自私軟弱。影片通過“瘋癲”這一疾病表征控訴了舊的社會體制和社會陋習對女性的壓迫,嘲諷了權勢者的愚昧和虛偽,贊揚了被壓迫女性的勇氣和智慧。
逃離了婚姻的林多時刻銘記母親的心愿,跋山涉水到了美國,再婚并生下女兒薇莉。林多實現了母親的期望,并且走了一條比母親預設的人生之路更好的路——自由之路。薇莉繼承了林多不甘屈服的個性,要強的母女二人之間的“爭斗”一直持續著。薇莉的第一次婚姻遵從母親的意愿,嫁給了一個中國男人,很快以離婚告終。后來薇莉結識了美國男子里奇,兩人相知相愛,卻難以得到母親的認可。面對女兒的難過甚至憤怒,林多表面上無動于衷,但回想起自己的情感歷程,最終決定尊重女兒的自由選擇。在薇莉的第二次婚禮之前,林多送上了贊美與祝福,母女緊緊相擁,開懷大笑。這大笑與林多“裝瘋”時特寫鏡頭中的暗笑形成了對照;暗笑是看到自由曙光時的竊喜,大笑則是自由路上的狂歡。
電影《喜福會》講述了四對母女的故事,每一個母親的故事中都包含了一個明顯的疾病表征。在這里,疾病不僅是身體機能的紊亂與破壞,更多的是社會文化癥候的某種鏡像反映。在舊中國社會體制下,女性作為弱勢群體話語權喪失,人身自由喪失,被置于消極被動接受命運安排的位置,隱忍地承受著社會風習所帶來的精神之殤。四位母親故事中的疾病隱喻性地表達了歷史戰爭、婚姻制度、封建禮教、傳統道德等對女性的壓迫和對親情的破壞。然而,影片里的中國母親經歷不幸卻敢于抗爭,在傷痛中樂觀前行,她們身體里所蘊涵的智慧、堅毅、執著的特質也傳給了下一代。雖然她們和女兒們常常由于文化差異而產生誤解和矛盾,她們都能在女兒身陷困境時用愛和理解打破堅冰,在幫助女兒走出困境的同時為自己“治病療傷”。最終冰釋前嫌的兩代人都經歷了真正意義上的精神成長。影片以疾病為始,以治愈為終,展現了中華民族那段多災多難的歷史,先輩們那些似曾相識的往事,以及一代代女性坎坷起伏的人生命運。然而,無論經歷多少坎坷,她們身上的優秀品質作為民族的印記依然清晰可見,不曾泯滅。她們作為中國母親的縮影,向世界闡釋了中國女性之美。
參考文獻
[1][美]亨利歐·內斯特·西格里斯特. 秦傳安譯.疾病的文化史[M].北京:中國編譯出版社,2009:1.
[2]薛博瑜主編.中醫古籍珍本集成(內科卷·痢疾論)[M].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4:28.
[3][美]阿倫·貝克,布拉德·奧爾福德.楊芳譯.抑郁癥[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14.
[4]蔣天平.神圣的疾病——美國小說中的瘋狂形象研究[M].成都:巴蜀書社,2010:5.
(作者介紹:朱文佳,河南大學外語學院在讀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