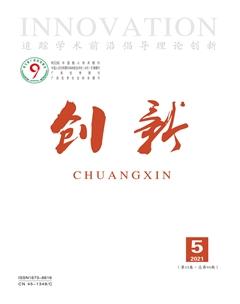嵌入全球價值鏈對中國制造業升級影響的多重維度分析
肖劍橋 宋憲萍

[摘 要] 已有文獻主要從產品內國際分工維度、全球價值鏈治理維度和中間品貿易維度研究嵌入全球價值鏈對中國制造業升級的影響。產品內國際分工的實質是“中心—外圍”的結構化,推動了分工地位的攀升,同時導致了分工環節的固化,需由低端要素驅動轉變為發展生產性服務業;全球價值鏈治理是市場與非市場關系的綜合運用,既推動了鏈條環節的升級,也導致了“低端鎖定”,需由被動嵌入轉變為主動重構;中間品貿易的最終目的是獲取企業增加值的核心競爭優勢,制造業企業吸收技術溢出易產生路徑依賴,需由引進學習轉變為自主創新。今后可從動態演化和層級累積的維度,深入剖析嵌入全球價值鏈的升級斷層機理,闡明其存在升級斷層、難以自動升級的內在機制,形成對我國制造業階梯式升級的路徑探源。
[關鍵詞] 全球價值鏈;國際分工;中間品貿易;制造業;升級
[中圖分類號] F114.1? ? [文獻標識碼] A? ? [文章編號] 1673-8616(2021)05-0080-13
全球價值鏈背景下的垂直專業化分工已成為世界經濟貿易和投資的核心機制。當今時代,生產在全球范圍內的分散是空前的。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公布的數據表明,在2016年,全球貿易總額的85%是在全球價值鏈內進行的。全球價值鏈背景下的生產重組,將國際貿易動力從國家層面的運轉,轉變為在企業之間運轉,每個企業以連續的方式增加價值,以中間產品的形式進行貿易,這些中間產品可作為其他地方的最終產品的投入[1-2]。
自2018年起,美國特朗普政府挑起中美貿易爭端,頻繁對中國輸美商品加征關稅,企圖用極限施壓的手段抑制中國經濟的發展。美國揮舞“貿易大棒”的深層原因并不是中美貿易逆差、中國技術趕超和國內的社會矛盾,而是意圖遏制在全球價值鏈背景下中美間動態利益的進一步失衡和維護自身在新國際分工格局中的主導地位[3]。中國制造業在過去的20余年內,以勞動力、土地和資源環境等要素成本優勢,承接了大量發達國家主導企業分割、淘汰、轉移出的低附加值環節,完成了工藝升級和產品升級的環節,正在形成由本土市場需求培育的本土企業高端要素的創新能力[4],向功能升級和鏈條升級邁進。美國政府在此關鍵升級節點發難,不僅是對中國經濟應對外部沖擊能力的一次大考,也進一步印證了中國經濟由追求發展速度向追求發展質量、由低端要素驅動發展向技術創新驅動發展轉變的必要性、緊迫性,亟須以新發展理念為核心,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指導,實現功能升級和鏈條升級。特別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下,產品內國際分工這一生產組織形式受到嚴重沖擊,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面臨巨大挑戰,中國正在加速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黨的十九大明確指出:“加快建設制造強國,加快發展先進制造業……支持傳統產業優化升級,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促進我國產業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級先進制造業集群。”[5]嵌入全球價值鏈的中國制造業升級不僅事關國之大計,而且也是學術界研究的熱門話題。已有文獻主要從產品內國際分工、全球價值鏈治理和中間品貿易三個維度對該問題展開了深入研究,各維度下均涵蓋理論基礎、影響及升級路徑等完整的研究范式。
一、產品內國際分工的分析維度
(一)理論基礎:產品內分工“中心—外圍”的結構化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伴隨著第三次科技革命引起的技術進步,產品生產的垂直一體化被逐漸分割,生產中的各道工序和各個環節被分散到不同的國家,形成了新的國際分工形式,即產品內國際分工[6]。產品內國際分工是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主導的價值鏈向發展中國家代工企業的延伸。Frobel等人認為,過去由少數發達國家從事工業生產活動,其他國家從事農業生產活動,并為前者提供生產所需原材料的舊國際分工模式正在瓦解。跨國公司將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由本國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使得發展中國家的生產部門越來越多地與世界經濟體系相關聯,嵌入由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生產網絡當中[7]。產品內國際分工的表現為“訂單制造”,實現形式是外包。Luthje將“訂單制造”歸納為主導企業把生產中各個環節的部分或全部工序以合同的形式外包給其他企業,包括國內外包和國際外包。承包企業沒有自主品牌,所提供的服務或生產的產品皆標以發包企業的品牌。訂單制造模式催生了專門為發包企業服務的訂單制造業,成為各個行業的基礎組件[8]。上述觀點都采取靜態分析的方法,也有學者從動態視角分析,認為產品內國際分工是隨資源稟賦不斷演化的分工形式。Hutchinson認為Frobel的分工理論沒有考慮到新興工業經濟體資源稟賦的動態發展,他以亞洲四小龍的崛起為例,證明一國或地區在以承接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為基礎實現經濟騰飛后,投入大量資本發展高等教育,為本國或地區累積了雄厚的人力資本,將人口紅利的數量優勢轉為質量優勢。在這種情況下,發達國家主導企業因勢利導,將承接產業轉移國家或地區的人力資本增長納入決策范疇,重構生產環節的國際分工,它的實質是承包企業在跨國公司全球生產網絡中地位的上升[9]。
(二)影響:分工地位的攀升與固化
中國制造業嵌入全球價值鏈的實質是參與產品內國際分工,這一分工形式對資本技術的稟賦要求較低,只需在某一生產環節具有比較優勢、具備生產條件即可參與到國際分工體系當中。在這種條件下,中國制造業企業以豐富的勞動力稟賦和低工資、低稅率的區位條件,承接了大量國際外包業務[10]。產品內國際分工的格局為中國制造業帶來了參與分工的生產機會,利用現有的生產技術和管理模式獲得后發優勢,通過產業關聯機制和“雁陣”轉移機制,提高了中國制造業的分工地位,產品內國際分工帶來的生產分割能夠有效促進中國工業價值鏈地位的提升,有利于收入的增長[11-12]。
雖然上述觀點都認為嵌入全球價值鏈能夠促進中國制造業在產品內國際分工中地位的提升,但是參與到這種分工模式中的中國制造業企業大多是開放模塊型和封閉集成型,它們的分工固定、缺乏創新[13],處于整條價值鏈的“微笑曲線”低端位置[14]。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企業仍然會受到發達國家主導企業和其他國家代工企業的雙重圍堵,即處于分工中心地位的企業為了維護自己的主導地位,會采取“技術鎖定”戰略抑制外圍企業進行攀升,并不斷培育新的代工企業加劇低端生產環節的競爭,引起價格的下降,使中國制造業企業陷入“悲慘增長”的境地[15]。因此,在分工維度下,中國制造業所處的國際分工地位不高,扮演的是“加工車間”的角色,一些所謂的高新技術企業實際上依賴核心零部件的進口,從事的是低技術生產環節,沒有能力承接真正高技術含量的國際外包業務,落入了“比較優勢”的分工陷阱之中,被發達國家主導企業鎖定在了分工的外圍[16]。正如張二震和戴翔所言,國際貿易中的動態利益雖然向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傾斜,但是這種發展中國家的崛起只是縮小了與發達經濟體之間的距離,是一種“有限趕超”,并未在本質上改變發達經濟體在全球經濟中占據絕對主導和優勢地位的現狀[17]。
(三)升級路徑:由低端要素驅動到發展生產性服務業
產品內國際分工與過去的產品間分工的根本區別在于,產品內分工是以各國生產要素的比較優勢為基礎,產品由各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生產要素組成。綜合上述文獻觀點,當前阻礙中國制造業在國際分工格局中地位提升的重要原因在于,中國制造業是以低端要素嵌入全球價值鏈,而之所以發達國家的企業可以主導國際分工,是因為發達國家掌握了參與生產的高端要素。因此,提升中國制造業在新國際分工中的地位,必須培育參與全球化生產的高端要素。
在大數據時代,物聯網、云計算、人工智能等高新技術使傳統制造業突破了其產業邊界,“中國制造2025”的核心要義在于把技術創新作為制造業發展的第一驅動力,重點是把生產性服務業和傳統制造業有機結合,推動制造業的數字化、網絡化和智能化,生產性服務業是整合全球價值鏈的關鍵,是中國制造業升級的根本措施。因此,發展中國家發展生產性服務業是實現產城互動、協同升級的關鍵,生產性服務的進口和離岸外包對制造業效率有正向影響[18-19];制造業和服務業可以通過“技術溢出效應、產品關聯溢出的直接效應、資源再配置效應和成本效應實現出口產品升級”[20];同時,應推動制造業服務化發展,為制造業分工地位的攀升提供支撐,使二者間形成交互效應[21]。因此,必須把生產性服務業的創新和發展作為制造業企業升級的必由路徑,加快制造業服務化發展[22]。
二、全球價值鏈治理的分析維度
(一)理論基礎:市場與非市場關系的綜合運用
全球價值鏈被視為大型主導企業作為價值鏈驅動者的治理工具,根據主導企業主要參與的生產環節分為生產者驅動型和購買者驅動型[23],在現實的生產中還存在兼顧二者特點的混合型驅動模式[24]。治理指的是任何通過非市場關系的協調經濟活動[25],它的內容主要包括立法治理、司法治理和執法治理,由鏈內的主導企業和鏈外的政府及非政府組織對參與價值鏈的企業行使治理權力[26]。價值鏈治理的類型是一個動態研究和不斷發展的過程:Schmitz和Humphrey將價值鏈的治理類型分為市場型、網絡型、準層級型和層級型[25];Gereffi等人以交易的復雜程度、識別交易的能力和基礎供應的能力為考量因素,將價值鏈的治理類型分為市場型、模塊型、關系型、俘獲型和層級型(如表1所示),這種分類方式當前被學術界廣泛采用[27]。Pietrobelli表示,要素的變動可能引起價值鏈治理類型的改變,因此全球價值鏈的內部治理是一個不斷調整和變化的動態現象,其本質影響著全球價值鏈的共同演進[28]。此外,Ivarsson和Alvstam以瑞典宜家公司與供應商的關系為案例,提出了啟發型治理模式。他們認為這種治理模式雖由主導企業控制,但其戰略是幫助能力較差的供應商實現技術升級,以此實現高效、靈活的低成本產品采購目標。同時,供應商可以采用主導企業的相關技術獲得額外的優勢,從而改善與其他客戶相關的產品、流程和市場地位——因為在這種治理結構中,主導企業不要求供應商鎖定在專屬的價值鏈中[29]。
(二)影響:鏈條環節的升級與鎖定
全球價值鏈中的升級指的是企業為了獲得更高收益進入更高層次的有壁壘市場的過程,包括工藝升級、產品升級、功能升級和鏈條升級[25]。
一方面,嵌入全球價值鏈促進了工藝升級和產品升級的過程,使發展中國家的企業能夠向國際市場出口,否則它們很難進入這些市場。例如,Baldwin認為,全球價值鏈可能為發展中國家的小企業提供一個理想的機會進入全球市場,使它們能夠專注于單一的產品類別,而無須努力建立掌握整個生產系統的能力[30]。李宏和陳圳指出,融入全球生產網絡可以幫助中國科技含量較高的制造業企業增強國際競爭力,實現升級[31]。王振國等人的研究佐證了上述觀點,他們認為中國制造業融入全球價值鏈,不僅提高了中國以一般貿易方式嵌入全球價值鏈的位置,也使得高技術含量的加工貿易部門在價值鏈中向上游邁進,促進了制造業產品在加工貿易中的升級[32]。此外,葛順奇和羅偉指出,制造業企業的要素結構能夠在嵌入全球價值鏈的過程中得到改善[33]。劉磊等人也表示制造業嵌入全球價值鏈還能夠緩解中國當下面臨的產能過剩問題[34]。
另一方面,有部分學者認為,嵌入全球價值鏈阻止了功能升級和鏈條升級,對代工企業具有抑制效應。在某些情況下,與大買家的排他性關系阻礙了其客戶群的多樣化,這進一步提高了“退出選項”的成本,將它們與主導企業捆綁在一起[35]。一些學者的研究表明,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分工并未實現功能升級,即便有企業試圖向價值鏈高端躍遷,也很少能夠順利完成[36];Ravenhill同樣認為僅依靠參與國際分工來發展技術和生產能力這一做法并不能自動實現功能升級的過程,并且要付出高昂的代價[37];Sampath和Vallejo通過對74個發展中國家(地區)不同技術水平的制造業行業進行實證分析得出,并非所有主導企業都對其他企業的學習和技術升級產生積極影響,當一些發展中國家(地區)的企業設法升級時,它們在現有的價值鏈中將面臨被主導企業邊緣化和排斥的危險[38]。這一觀點同樣被國內學者佐證,他們認為中國以“大進大出”的貿易模式嵌入全球價值鏈,不僅不能快速地實現產業升級,反而通過要素、市場和價值鏈的三重鎖定效應,形成低端鎖定的困局[39]。特別是嵌入全球價值鏈對制造業企業的創新活動具有顯著的抑制作用,這種影響對高價值鏈嵌入度的行業是逐年遞增的,且對加工貿易企業的影響尤為顯著[40]。
上述“升級悖論”的產生,主要源于中國制造業在融入全球生產網絡的過程中自動形成了俘獲型網絡治理模式:發達國家掌握著核心技術環節且具有大量的市場終端渠道,迫切需要能力強、成本低的代工企業滿足其市場需求;而發展中國家代工企業具有大量的低端要素稟賦和強大的生產能力,需要技術和管理方面的支持,也迫切需要生產機會賺取利潤。當代工企業實現一定程度上的工藝升級和產品升級后,試圖進入功能升級或鏈條升級的高端階段,就會威脅到發達國家主導企業的核心利益,它們就會采取渾身解數阻礙發展中國家代工企業的升級,形成“低端鎖定”[41]。王益民和宋琰紋發現了全球生產網絡中“戰略隔絕機制”的存在,導致了產業集群的“升級悖論”,即集群內企業沿某一特定產品—技術路徑升級越快,當地根植性與當地產業關聯被弱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42]。任保全等人的進一步研究表明,“低端鎖定”的形成也具有內生性,不僅源于主導企業的擠壓,也源于內需不足和制度障礙等內在約束[43]。沈國兵和于歡認為,正是俘獲型網絡中正向的“技術溢出效應”“規模和激勵效應”和負向的“壓榨效應”“低端鎖定”之間的矛盾,導致中國制造業走向低端嵌入導致的“悲慘增長”[44]。
(三)升級路徑:由被動嵌入到主動重構
新李斯特主義認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展中國家應該建立即使是低效率但卻報酬遞增的、而非只提供廉價勞動的高端產業部門,才能實現真正的致富”[45]。因而,中國必須依靠巨大的國內市場,構建獨立自主的國內價值鏈,加強自主創新,實現價值鏈升級。劉志彪和張杰強調,要突破被“俘獲”和“壓榨”的全球價值鏈關系網絡,必須構建依托國內市場需求的本土價值鏈網絡結構,采取勢力抵消策略、反“梯子策略”,通過“重新整合中國企業的商業網絡及產業循環體系、重新塑造國家價值鏈的治理結構、重新調整區域間的產業關系結構”,以服務于生產廠商和采購、銷售商的雙邊交易平臺以及直接由國內主導企業面對消費者的單邊市場平臺為載體,構建基于國家價值鏈的產業升級機制[46-47]。
在成熟的國內價值鏈的基礎上,中國制造業可以再次把鏈條向周圍區域延伸,通過再造或重構價值鏈的方式,改變現有的貿易格局,主導新的區域性價值鏈。梁運文和張帥曾針對中國制造業國際競爭力斷層問題,提出過依靠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構建區域產業價值鏈,破解競爭力傳導斷裂困境的方案[48]。在新時代,更多的學者把目光聚焦到了“一帶一路”倡議。一些學者認為,由于“一帶一路”倡議采用了根據不同國家的要素稟賦進行差異化的制造業合作理念[49],在合作中中國可以接觸到先前由發達國家主導企業壟斷的價值鏈高端環節,有助于中國擺脫長久以來的被“俘獲”命運[50]。
三、中間品貿易的分析維度
(一)理論基礎:企業增加值的核心競爭優勢
就貿易角度而言,中間產品的貿易銜接全球生產網絡各個環節。中間品成為最終產品前,在全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的企業間流入流出,這些企業因其要素分工和技術水平的差異,具有不同的增值能力。在高增加值企業的中間品流入低增加值企業的過程中,產生了一種技術溢出效應,承接低端要素分工和低技術水平環節的企業若合理利用技術溢出效應,則能夠通過促進企業技術進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方式,培育企業增加值的核心競爭優勢。Amiti和Konings采用印度尼西亞1991—2001年的制造業普查數據,估計了進口中間產品對生產率提升的影響。結果表明,中間品投入可以通過學習效應、種類效應和質量效應提高全要素生產率[51]。Gopinath和Neiman以阿根廷2000—2002年金融危機為案例,研究了危機期間貿易斷崖式下跌的原因,建立了包括迂回生產和進口固定成本的異質企業模型,證明了進口中間品投入減少是危機期間生產力損失的重要因素[52]。姜青克等人對1995—2009年27個國家和地區14個制造業的面板數據展開實證研究,證明了外國研發資本通過進口中間品的技術溢出效應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具有正向推動作用,行業間中間品對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更為顯著[53]。此外,在中間品貿易背景下,貿易自由化即關稅的降低,能夠為企業節約成本,促使企業引進更多種類的中間品、加大研發投入,從而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培育企業增加值的核心競爭優勢。Goldberg等人通過研究1989—1997年印度企業的案例發現,通過降低中間品投入關稅,引進貿易自由化之前得不到的新中間投入品,企業將從國際貿易中獲得靜態收益。這些新的進口中間品投入又使公司能夠通過引進新的品種擴大其國內產品范圍,從而從貿易中產生動態收益[54]。沿著這一思路,耿曄強和鄭超群構建了包括中間品貿易自由化、進口多樣性和企業創新在內的理論模型,闡釋了中間品貿易自由化和進口多樣性對企業創新的促進作用,并以2003—2007年中國工業企業和海關匹配數據進行了實證檢驗[55]。Amiti和Khandelwal的進一步研究發現,降低中間投入品的關稅能夠促進世界高端產品的質量升級,抑制低端產品的質量升級,同時需要營商環境、制度質量等因素的支持[56]。
(二)影響:進口要素的吸收與依賴
中國制造業以承接外包訂單、進口中間產品、從事加工貿易的方式獲得了融入全球生產網絡的機會,并在融入過程中學習來自中間產品制造的技術和發包企業的制度管理經驗,為企業培育核心競爭優勢以提高企業的增值能力。陳勇兵等人以2000—2005年中國部分工業企業的微觀數據為樣本,證明了企業能夠通過進口中間品獲得水平和垂直的技術溢出,增加企業生產的產品種類、提高企業產品質量,從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水平[57]。張少軍和劉志彪利用1998—2009年中國制造業的面板數據,提出中國制造業發展外向型經濟的優勢在于利用進口中間品的技術溢出效應降低研發成本,通過“干中學”效應在全球價值鏈中不斷吸收學習,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內資企業的技術水平,實現工藝升級和產品升級的初級升級模式[58]。田巍和余淼杰則使用2001—2006年中國制造業企業的數據,發現中間品關稅的下降能夠降低企業成本,增加研發投入,從而提高企業的技術水平[59]。
但進口中間品提供的技術溢出是有限的,取決于企業的學習能力;進口中學習易演變為進口中依賴,抑制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同時,通過進口中間品發展加工貿易的發展方式不僅扭曲了貿易結構,并且在數據測度上形成了“高技術幻象”和“技術進步悖論”[60],夸大了中國制造業企業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和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呂越等人的研究表明,中國制造業企業對技術吸收的能力不強,而進口中間品的技術溢出能否轉化為企業的技術水平,取決于企業對技術的吸收能力,目前大多數本土制造業企業未達到合理的技術吸收門檻[61]。紀月清等人檢驗了進口中間品帶來的技術溢出效應對企業出口產品技術創新的影響,發現反映進口中間品與本土中間品之間競爭關系的水平技術溢出,抑制了進料加工貿易型企業的技術創新,并對來料加工裝配貿易型企業的影響不顯著。這是由于加工貿易型企業在長期進口中間品的過程中形成了技術依賴,缺乏自主創新活動,喪失了獲取核心競爭優勢的能力[62]。盛斌和馬濤區分了產品的全部技術含量和國內技術含量,通過計量檢驗對國內技術含量與中國工業在垂直專業化分工中的地位之間的關系進行考察[63],隨后一些學者在此基礎上繼續改進檢驗方法,通過剔除出口商品中所包含的進口中間投入品價值,計算了全部技術復雜度和實際的國內技術復雜度,證明了中國制造業企業的國內出口技術復雜度較低,參與技術密集型行業的加工、組裝等低附加值環節造成了全球價值鏈參與度的虛高,實際上處于全球價值鏈的低端地位[64-65]。
(三)升級路徑:由引進學習到自主創新
中國制造業利用進口中間品發展加工貿易融入全球生產網絡的方式實際上遵循了林毅夫和張鵬飛的后發優勢理論[66]。該理論認為欠發達國家通過從發達國家引進技術,可以獲得比發達國家更快的經濟增長速度,最后使欠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收斂于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但這一模型成立的前提是,欠發達國家可以通過技術引進獲得比發達國家更快的技術創新速度。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增長奇跡,已經成功地實現“有限趕超”[67]。但也應當認識到當前已處于技術進步的瓶頸期,依靠進口中間品帶來的技術溢出效應和學習模式已經不能滿足中國制造業發展的需要,由引進學習向自主創新邁進是企業獲取核心競爭優勢的必要途徑[68],也是中國制造業升級的必由之路。
自主創新要求中國制造業由依靠進口中間品驅動發展向創新驅動發展升級,強調以技術和制度的雙重創新促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一方面,要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動下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把技術創新作為增長的新動力;另一方面,要繼續全面深化改革,破解長期制約科技創新的體制機制問題,充分發揮制度紅利,增強企業的創新競爭力[69]。張亞豪和李曉華歸納了后發國家的制造業企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學習升級方式,認為自主創新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從初期的模仿制造逐漸過渡到引進學習、合作學習,最后經過借鑒、吸收、再創新等學習環節,達到自主創新的程度。只有具有自主創新能力的企業,才能真正掌握核心技術與競爭優勢,這一點在復雜產品系統產業中尤為重要[70]。
四、述評與展望:動態演化與循環累積的分析維度
關于嵌入全球價值鏈對中國制造業升級的影響這一問題,國內外學者進行了積極的廣泛探索,提出了很多有價值的思路和觀點。但是以上三種維度的分析脈絡大多以靜態視角研究中國制造業在全球生產網絡中一個時期內的特點,少有從動態演化和循環累積的分析維度研究中國制造業嵌入全球價值鏈的動態特征。
事實上,部分學者已經注意到,嵌入全球價值鏈對中國制造業的影響是一個動態變化、循環累積的過程,這個過程既可以是正反饋的良性循環,也可以是負反饋的惡性循環[71]。張其仔指出,比較優勢具有不斷演化的特征,“中等收入陷阱”形成的根源在于新的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沒有形成,存在比較優勢斷檔。中國已經依靠比較優勢“分叉”的非線性演化步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必須積極尋找新的比較優勢產業才能防止落入“中等收入陷阱”[72]。俞榮建將代工能力分為專用性驅動和專有性驅動,認為代工能力專用性削弱討價還價權力,在專有性水平低的情況下,助長國際客戶對關系租金的掠奪傾向,推動代工企業“偽升級”演化[73]。部分學者的實證也在一定程度上佐證了動態演化的觀點。王玉燕等人認為制造業垂直專業化水平和升級存在倒“U”形關系,即在嵌入全球價值鏈初期,中國制造業可以通過技術溢出、“干中學”等效應促進升級,但是隨著嵌入的不斷深入,其生產環節被發達國家領導企業的治理模式鎖定在低附加值環節[74]。潘秋晨在中國裝備制造業嵌入全球價值鏈的考察中同樣發現了倒“U”形的規律,且技術水平越高的裝備制造行業越容易對中間品效應形成技術依賴[75]。但是這種倒“U”形關系意味著存在一個“改善區間”,在改善區間內可以促進升級,過度嵌入則會受到發達國家主導企業的打壓[76]。周巖和陳淑梅從貿易、生產和區位三個角度研判了中國制造業嵌入GVC的程度和地位,發現中國制造業參與GVC的程度呈現M形趨勢,且前向參與度增速高于后向參與度增速,正在由被動“俘獲”向主動嵌入升級[77]。以上觀點進一步說明了嵌入全球價值鏈對中國制造業升級并不是靜態影響,而是一個動態演化的過程。因而相應地,中國制造業的升級也是一個不斷累積的過程,既不可能完全脫離技術溢出和“干中學”效應的促進作用,直接達到完全自主創新的高度,也不能繼續走依附于發達國家主導企業、維持當前“中心—外圍”的國際分工格局的老路,而應該形成系統的、完整的階梯式、層級式制造業升級模式,使中國制造業業態逐步演化、逐步走向價值鏈的高端地位。
基于以上分析,未來研究可能取得的邊際貢獻如下。
首先,用演化的視角研究中國制造業嵌入全球價值鏈的升級問題。在當前由低端要素驅動發展模式轉為技術創新驅動發展模式的背景下,中國制造業處于升級的瓶頸期。可以動態演化和循環累積理論為研究視角,結合產品內國際分工、全球價值鏈治理和中間品貿易等分析維度的研究成果,構建層級累積理論下中國制造業嵌入全球價值鏈的升級斷層機理,分析中國制造業存在“升級斷層”、難以“自動升級”的原因。
其次,優化衡量中國制造業升級的方法。孔偉杰認為,目前缺少一種合理測度制造業企業轉型升級的方法或指標體系[78]。當前的主要研究方法包括:以技術水平衡量升級;采用一般產業理論的產業間升級和產品內升級,尋找代理變量測度兩種升級的效果;構建產業升級指標,包括各種經濟和非經濟因素。若以技術作為衡量指標,則應在剔除國外出口技術復雜度的基礎上,進一步研究國內出口技術復雜度的結構演化,高技術產業在出口結構中的比例是否提升;若以產業間升級和產品內升級作為衡量中國制造業升級的指標,則需甄選更為貼切的代理變量,把反映創新驅動發展的指標納入考量之中;若以包括經濟和非經濟因素的綜合指標衡量制造業升級,則既需要體現嵌入全球價值鏈對中國制造業升級的影響,又需突出全球價值鏈背景下制造業升級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同時兼顧對社會、環境等多方面非經濟因素的影響。
最后,在已有研究的升級路徑的基礎上,建立全球價值鏈背景下中國制造業升級體系。可以動態演化和循環累積視角下的升級斷層機理為依托,從微觀、中觀、宏觀三個層級,逐步以技術創新驅動發展為內核、以發展生產性服務業為依托、以構建國內價值鏈為平臺、以主導區域價值鏈為契機,形成全球價值鏈背景下中國制造業升級的階梯式路徑,尋求制造業突破“低端鎖定”困境和被“俘獲”命運,邁向價值鏈高端和打造價值鏈主要地位的升級之道,為實現建設制造業強國的戰略目標和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奠定堅實基礎。
參考文獻:
[1] PONTE S, STURGEON T. Explaining governance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 modular theory-building effort[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2014, 21(1):195-223.
[2] FLENTO D,PONTE S.Least-developed countries in a world of global value chains: Are WTO trade negotiations helping?[J].World development,2017(94):366-374.
[3] 宋憲萍,康萌.美國發起貿易爭端的緣起反思[J].當代經濟研究,2019(9):72-83,113.
[4] 張杰,劉志彪.需求因素與全球價值鏈形成:兼論發展中國家的“結構封鎖型”障礙與突破[J].財貿研究,2007(6):1-10.
[5] 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24.
[6] ARNDT S.Globalization and the open economy[J].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1997(8): 71-79.
[7] FROBEL, HEINRICHS J, KREYE O.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J].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1978, 17(1):123-142.
[8] LUTHJE B. Electronics contract manufacturing: global produc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J]. Industry and innovation, 2002(3):227-247.
[9] HUTCHINSON F. Globalisation and the ‘newer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J]. Labour and management in development journal,2004,4(6):61-63.
[10] 唐海燕,張會清.產品內國際分工與發展中國家的價值鏈提升[J].經濟研究,2009(9):81-93.
[11] 姚博,魏瑋.參與生產分割對中國工業價值鏈及收入的影響研究[J].中國工業經濟,2012(10):65-76.
[12] 余東華,田雙.嵌入全球價值鏈對中國制造業轉型升級的影響機理[J].改革,2019(3):50-60.
[13] 牛衛平.國際外包陷阱產生機理及其跨越研究[J].中國工業經濟,2012(5):109-121.
[14] 劉志彪.重構國家價值鏈:轉變中國制造業發展方式的思考[J].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11(4):1-14.
[15] 卓越,張珉.全球價值鏈中的收益分配與“悲慘增長”:基于中國紡織服裝業的分析[J].中國工業經濟,2008(7):131-140.
[16] 唐海燕,張會清.中國在新型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地位:基于價值鏈視角的分析[J].國際貿易問題,2009(2):18-26.
[17] 張二震,戴翔.關于中美貿易摩擦的理論思考[J].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2):62-70,192.
[18] 張少軍,劉志彪.全球價值鏈與全球城市網絡的交融:發展中國家的視角[J].經濟學家,2017(6):33-41.
[19] 趙霞.生產性服務投入、垂直專業化與裝備制造業生產率[J].產業經濟研究,2017(2):14-26.
[20] 王思語,鄭樂凱.制造業服務化是否促進了出口產品升級:基于出口產品質量和出口技術復雜度雙重視角[J].國際貿易問題,2019(11):45-60.
[21] 羅軍.服務化發展與制造業全球價值鏈地位:影響機制與門檻效應[J].當代財經,2018(11):100-110.
[22] 劉斌,魏倩,呂越,等.制造業服務化與價值鏈升級[J].經濟研究,2016(3):151-162.
[23] GEREFFI G. Global commodity chains:new forms of coordination and control among nations and firms in international industries[J]. Competition & change,1996,1(4):427-439.
[24] 張輝.全球價值鏈動力機制與產業發展策略[J].中國工業經濟,2006(1):40-48.
[25] SCHMITZ H,HUMPHREY J. Governance and upgrading:Linking industrial cluster and global value chain[C].Brighton: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00.
[26] KAPLINSKY R. Globalization and unequalisation: What can be learned from value chain analysi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00, 37(2):117-146.
[27] GEREFFI G, HUMPHREY J, STURGEON T. The governance of global value chains[J].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2005, 12(1):78-104.
[28] PIETROBELLI C.Global value chains meet innovation systems:are there learning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J] World development,2011,39(7):1261-1269.
[29] IVARSSON I,ALVSTAM C.Supplier upgrading in the home-furnishing value chain:an empirical study of IKEAs sourcing in China and South East Asia[J].World development, 2010, 38(11):1575-1587.
[30] BALDWIN R. Global supply chains: Why they emerged, why they matter, and where they are going[R]. London: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2012.
[31] 李宏,陳圳.中國優勢制造業全球價值鏈競爭力分析[J].審計與經濟研究,2018(2):93-105.
[32] 王振國,張亞斌,單敬,等.中國嵌入全球價值鏈位置及變動研究[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9(10):77-95.
[33] 葛順奇,羅偉.跨國公司進入與中國制造業產業結構:基于全球價值鏈視角的研究[J].經濟研究,2015(11):34-48.
[34] 劉磊,步曉寧,張猛.全球價值鏈地位提升與制造業產能過剩治理[J].經濟評論,2018(4):45-58.
[35] HUMPHREY J,SCHMITZ H.How does inser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ffect upgrading in industrial clusters? [J]. Regional studies, 2002, 36(9):1017-1027.
[36] GIBBON P. Global commodity chains and economic upgrading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J]. CDR working paper, 2011(2):1-35.
[37] RAVENHILL J.Global value chains and development[J].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014, 2(21):264-274.
[38] SAMPATH P, VALLEJO B. Trade,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upgrading: what, when and how?[J].The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2018, 30(3):481-504.
[39] 杜宇瑋,周長富.鎖定效應與中國代工產業升級:基于制造業分行業面板數據的經驗研究[J].財貿經濟,2012(12):78-86.
[40] 張杰,鄭文平.全球價值鏈下中國本土企業的創新效應[J].經濟研究,2017(3):151-165.
[41] 劉志彪.國際外包視角下我國產業升級問題的思考[J].中國經濟問題,2009(1):6-15.
[42] 王益民,宋琰紋.全球生產網絡效應、集群封閉性及其“升級悖論”:基于大陸臺商筆記本電腦產業集群的分析[J].中國工業經濟,2007(4):46-53.
[43] 任保全,劉志彪,任優生.全球價值鏈低端鎖定的內生原因及機理:基于企業鏈條抉擇機制的視角[J].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16(5):1-23.
[44] 沈國兵,于歡.中國企業參與垂直分工會促進其技術創新嗎?[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7(12):76-92.
[45] 沈梓鑫,賈根良.增加值貿易與中國面臨的國際分工陷阱[J].政治經濟學評論,2014(4):165-179.
[46] 劉志彪,張杰.全球代工體系下發展中國家俘獲型網絡的形成、突破與對策:基于GVC與NVC的比較視角[J].中國工業經濟,2007(5):39-47.
[47] 張杰,劉志彪.全球化背景下國家價值鏈的構建與中國企業升級[J].經濟管理,2009(2):21-25.
[48] 梁運文,張帥.垂直專業化下中國制造業競爭力層次傳導效應[J].財經研究,2011(12):95-106.
[49] 孟祺.基于“一帶一路”的制造業全球價值鏈構建[J].財經科學,2016(2):72-81.
[50] 王恕立,吳楚豪.“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的國際分工地位:基于價值鏈視角的投入產出分析[J].財經研究,2018,44(8):18-30.
[51] AMITI M, KONINGS J. Trade liberalization, intermediate inputs, and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Indonesia[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7, 97(5):1611-1638.
[52] GOPINATH G, NEIMAN B. Trade adjustment and productivity in large crise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4, 104(3):793-831.
[53] 姜青克,戴一鑫,鄭玉.進口中間品技術溢出與全要素生產率[J].產業經濟研究,2018(4):99-112.
[54] GOLDBERG P K,KHANDELWAL A K, PAVCNIK N,et al.Imported intermediate inputs and domestic product growth: evidence from India[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8,125(4):1727-1767.
[55] 耿曄強,鄭超群.中間品貿易自由化、進口多樣性與企業創新[J].產業經濟研究,2018(2):39-52.
[56] AMITI M,KHANDELWAL A K.Import competition and quality upgrading[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3, 95(2):476-490.
[57] 陳勇兵,仉榮,曹亮.中間品進口會促進企業生產率增長嗎:基于中國企業微觀數據的分析[J].財貿經濟,2012(3):76-86.
[58] 張少軍,劉志彪.國際貿易與內資企業的產業升級:來自全球價值鏈的組織和治理力量[J].財貿經濟,2013(2):68-79.
[59] 田巍,余淼杰.中間品貿易自由化和企業研發:基于中國數據的經驗分析[J].世界經濟,2014(6):90-112.
[60] 宋憲萍,賈蕓菲.全球價值鏈的深度嵌入與技術進步關系的機理與測算[J].經濟縱橫,2019(12):74-85.
[61] 呂越,陳帥,盛斌.嵌入全球價值鏈會導致中國制造的“低端鎖定”嗎?[J].管理世界,2018(8):11-29.
[62] 紀月清,程圓圓,張兵兵.進口中間品、技術溢出與企業出口產品創新[J].產業經濟研究,2018(5):54-65.
[63] 盛斌,馬濤.中國工業部門垂直專業化與國內技術含量的關系研究[J].世界經濟研究,2008(8):61-67,89.
[64] 杜傳忠,張麗.中國工業制成品出口的國內技術復雜度測算及其動態變遷:基于國際垂直專業化分工的視角[J].中國工業經濟,2013(12):52-64.
[65] 于津平,鄧娟.垂直專業化、出口技術含量與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J].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14(2):44-62.
[66] 林毅夫,張鵬飛.后發優勢、技術引進和落后國家的經濟增長[J].經濟學,2005(4):53-74.
[67] 楊汝岱,姚洋.有限趕超與經濟增長[J].經濟研究,2008(8):29-41,64.
[68] 黃德春,劉志彪.環境規制與企業自主創新:基于波特假設的企業競爭優勢構建[J].中國工業經濟,2006(3):100-106.
[69] 黃群慧.“新常態”、工業化后期與工業增長新動力[J].中國工業經濟,2014(10):5-19.
[70] 張亞豪,李曉華.復雜產品系統產業全球價值鏈的升級路徑:以大飛機產業為例[J].改革,2018(5):76-86.
[71] 楊虎濤.不可逆性的演化經濟學含義[J].社會科學戰線,2017(8):33-39,2.
[72] 張其仔.比較優勢的演化與中國產業升級路徑的選擇[J].中國工業經濟,2008(9):58-68.
[73] 俞榮建.基于共同演化范式的代工企業GVC升級機理研究與代工策略啟示:基于二元關系的視角[J].中國工業經濟,2010(2):16-25.
[74] 王玉燕,林漢川,呂臣.全球價值鏈嵌入的技術進步效應:來自中國工業面板數據的經驗研究[J].中國工業經濟,2014(9):65-77.
[75] 潘秋晨.全球價值鏈嵌入對中國裝備制造業轉型升級的影響研究[J].世界經濟研究,2019(9):78-96,135-136.
[76] 呂越,黃艷希,陳勇兵.全球價值鏈嵌入的生產率效應:影響與機制分析[J].世界經濟,2017(7):28-51.
[77] 周巖,陳淑梅.中國融入全球價值鏈的動態變遷及國際比較[J].經濟問題探索,2018(3):108-117.
[78] 孔偉杰.制造業企業轉型升級影響因素研究:基于浙江省制造業企業大樣本問卷調查的實證研究[J].管理世界,2012(9):120-131.
[責任編輯:李 妍]
Multi-dimensional Analyses on Impacts of Embedding into Global Value
Chain on Chinas Manufacturing Upgrading
Xiao Jianqiao? Song Xianping
Abstract: Existing literature mainly studies the impacts of embedding into global value chain on Chinas manufacturing upgrading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within products, global value chain governance, and intermediate goods trade. The essence of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within products is the structure of “center-periphery”, which not only promotes the status of division of labor but also results in the solidification of division of labor. It needs to shift from low-end elements-driven to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services. Global value chain governance is a comprehensive interaction between market and non-market relations, which not only promotes the upgrading of the chain but also results in the solidification of low-end elements. It needs to shift from passive embedding to active restructuring. The ultimate goal of intermediate goods trade is to obtain the cor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the added value of enterprises. It is easy for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hat enjoy technology spillovers to depend on introducing existing technologies, and it is necessary for them to shift from introduction of technology and learning to independent innovation. Future studies can further analyzes the upgrading fault mechanism of embedding into global value cha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ynamic evolution and hierarchy accumulation and elaborate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existing upgrading faults and the difficulty in automatic upgrading so as to find the solutions for Chinas manufacturing upgrading in a gradual manner.
Key words: global value chain;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intermediate goods trad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upgr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