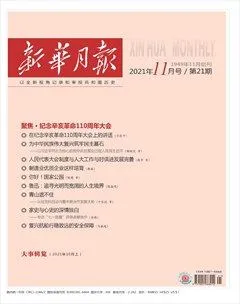“9·11”事件20周年:反恐戰爭并未走出困局
曹然
美國紐約世貿中心雙子塔遺址,如今是一座一英畝見方的水池。池邊的護欄上刻著2983個名字。入夜,柔和的黃色燈光會穿過鏤空的字符。每個字符都雕刻精致,排列也講究:同一架次航班的旅客、同一家公司的員工、同一支隊伍的消防員。至于其他遇難者,設計師拜訪了他們的家屬,考察是否有人曾一起吃飯、一起通勤,盡可能讓每兩個挨在一起的名字都有生前的聯結。
2021年8月30日,美軍從混亂的喀布爾國際機場撤出最后一名士兵,結束了持續20年的反恐戰爭。
20年前的10月7日,在“基地”組織恐怖分子針對美國紐約世貿中心的一起系列恐怖襲擊事件后的將近一個月后,美國及北約聯軍轟炸了包括喀布爾在內的阿富汗多座城市,拉開了這場反恐戰爭。
對于如今的阿富汗亂局,塔利班指責一切混亂都是美軍造成。非塔利班的新政府談判代表及反塔利班的馬蘇德家族,同樣認為美國應當負責。拜登政府駐華大使提名人選、當年曾支持出兵阿富汗的伯恩斯去年也表示,如果歷史能重來,“想必能有比戰爭更好的辦法”。
文明的沖突?
“9·11”事件發生當天,距離第二架客機撞擊雙子塔才過去26分鐘,時任美國總統小布什就在佛羅里達州布克小學宣布:“這是恐怖襲擊。”簡短的記者會后,他乘“空軍一號”輾轉三地,一天內發表三次演說,每次都強調“恐怖襲擊”的定性。

彼時,恐怖主義還是模糊的概念,各國政府普遍缺乏反制預案。組建國土安全部、聯合國安理會1377號決議將國際恐怖主義定性為“最嚴重威脅”,都是“9·11”事件之后的事。
當時,美國國務院出現了兩種觀點。一位時任美國國務院中亞事務顧問的國際關系教授對記者回憶,當時一些人認為這是極端宗教世界與“西方文明世界”的“文明之戰”;另一派則認為這其實是恐怖分子設下的“文明之戰”陷阱,應保持警惕,聚焦于恐怖組織本身,避免文明對立。前一種觀點來自冷戰中興起的“文明的沖突”理論代表人物亨廷頓與伯納德·劉易斯,后一種則源自批判“文明沖突論”忽視伊斯蘭世界內部差異性的知名學者愛德華·薩義德。
1998年,劉易斯在倫敦一份小報上讀到“基地”組織領導人本·拉登對美國宣戰的消息,當即指出,此人操持明顯的“圣戰意識形態”,將對西方世界構成嚴重安全威脅。
在阿富汗,這種“意識形態”無處不在:塔利班等信奉哈乃斐派教法的遜尼派穆斯林滿足于實現一地一國的宗教化,而信奉薩拉菲派教法的“基地”組織和后來的“伊斯蘭國”(IS)都主張將外國領土視為圣戰地。
直到“9·11”事件發生,美國政府才重視起劉易斯的警告。霧谷和五角大樓的絕大多數都支持劉易斯的觀點,時任副總統切尼稱贊“在這個新世紀,他的智慧每天都被決策者、外交官、學者和新聞媒體所追求。”而薩義德及其在華盛頓的支持者則因“批評西方”的立場被指責為“恐怖分子的幫兇”。
時年72歲的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宗教教授大衛·拉波波特由此突然被華盛頓注意。他基于“文明沖突”的邏輯,在“9·11”事件兩年前就提出自己對恐怖主義及反恐的定義和思路,其論文《現代恐怖主義的四次浪潮》被后來者譽為“最著名、最有影響、也最有爭議的恐怖主義研究文獻”。
事實上,這仍是冷戰思維的延續。“與其說拉波波特的浪潮理論影響了美國政府,不如說拉波波特的觀點契合了華盛頓的冷戰思維。”前述教授說。和福山對民主“浪潮”的解釋類似,拉波波特將恐怖主義的歷史簡單分期,用單一因素解讀恐怖主義在人類不同歷史時期的興衰。其中,1979年至今的恐怖主義浪潮被他歸結為“以宗教為目的的政治運動”,換言之,其本質是文明沖突論,即一種文明對其他文明的極端攻擊。
“9·11”事件之后的20年,回到國內并成為阿富汗政府高官的拉德馬得常與美國外交官討論他們眼中的恐怖主義與反恐戰爭。拉德馬得在阿富汗戰爭初期以難民身份逃往伊朗,他認為,除了冷戰思維外,將反恐戰爭擴展為“文明之戰”,也是實用主義的選擇,因為大多數美國官員“根本搞不清楚伊斯蘭文化,甚至不知道塔利班和‘基地組織信奉的是不同教派”,直到“9·11”事件發生10年后,美軍仍沒有摸清“基地”組織的邊界,而是將之定義為“一個由各種關聯網絡組成的恐怖辛迪加”。
猛藥未奏效
拉德馬得2002年回到家鄉喀布爾后,作為新政府內少數英語流利的人才輾轉各部門及總統府任職。政府內的美方顧問對他說:只要走上西方式的現代化道路,恐怖主義問題就會迎刃而解。他成為卡爾扎伊政府分管地方治理體系改革的負責人后,發現所有政策都來自各部門外國顧問的提議。
拉波波特的理論認為,國際恐怖主義浪潮都根植于本土政治社會生態,如果當地社會生態改變了,浪潮失去了土壤,就將逐漸平息。他預期,在充分干預的情況下,極端宗教帶來的恐怖主義浪潮會在2025年前后衰退。
但即使是伯納德·劉易斯,也反對直接將外來制度強加給阿富汗基層社會的方式。他說,有些東西“不能強加于人”,西方式的直接民主“是一劑很猛的藥”,必須以小劑量、逐漸遞增的方式給病人服用,否則有殺死病人的風險。

“大多數政策提議并非照搬西方制度,而是曾在南亞或東南亞國家成功落地。”拉德馬得對記者說,“問題在于,阿富汗社會和那些社會也不相同。”他認為,如果一定要比較,阿富汗其實更接近中亞、西亞地區的蘇聯加盟共和國,蘇聯解體使其原有治理體系被連根拔起,但新的體系或未能建立,或上下脫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