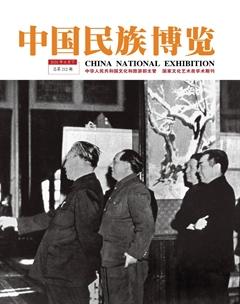基于舞蹈生態學視角的“當代中國古典舞”譜系初探

【摘要】舞蹈生態學構建了一個舞蹈哲學的思想體系,提供了一種科學揭示人類舞蹈文化現象的思路與方法。本文以舞蹈生態學的視角和首都師范大學史紅教授對“北京舞蹈群落”相關研究成果為基礎,在學習、實踐的過程中,對從北京舞蹈群落中生發出的“當代中國古典舞”這一高密度舞種的“源”“流”“形”進行了梳理和分析,以期能夠對當下中國古典舞“重建”和“復現”的理論爭鳴和實踐探索提供有益的參考。
【關鍵詞】舞蹈生態學;當代中國古典舞;重建;復現
【中圖分類號】J72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4198(2021)16-170-03
【本文著錄格式】張銘.基于舞蹈生態學視角的“當代中國古典舞”譜系初探[J].中國民族博覽,2021,08(16):170-172.
基金項目:2020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化和旅游調研項目“探究龜茲石窟壁畫曼妙舞姿,讓千年的龜茲樂舞重現芳華”(項目編號:20WLT2007);新疆藝術學院院級科研項目“龜茲樂舞飛天的舞蹈身體語言研究”(項目編號:2018XYKYYB02)階段性研究成果。
舞蹈生態學從20世紀90年代初建立至今,開辟了一門學科,構建了舞蹈哲學的思想體系,提供了一種科學揭示人類舞蹈文化現象的思路與方法;舞蹈生態學的創立,也將人們對舞蹈的認識和描述由感性的層面提升到了科學理性的高度。其“本位論”的立場,為舞蹈藝術的本體研究奠定了不可動搖的獨立地位。
舞蹈史學界傳統的研究方法大體是:從古籍、文獻中搜尋與舞蹈相關的線索,參照一些文物及其他形象資料,以通用性的斷代體為時序,沿著以事述人(敘舞)的方法予以闡釋。①但是從記載古代樂舞的文獻來看,有關舞蹈的記載基本是歷代帝王的“昭德象功”樂舞,或是詩詞文獻中的輕歌曼舞,常賦予其個人的審美旨趣或對君王的勸誡,由此,歷代封建王朝中的樂人舞伎地位極低,有名有姓者難覓其跡,其舞容舞貌更難以記述流傳,這都會造成舞史研究的局限性。
首先,依循舞蹈的本體特質,舞蹈生態學倡導“以人傳舞”與“以事述人”相結合的辯證舞史觀,不僅古代舞史研究的信度和形象化闡釋有所裨益,而且旨在倡導當代舞史研究之革新,即高度關注專業舞人及民間代表性傳承人的口述歷史及其經典舞目的形象化記錄,結合對其生態環境多維度、綜合性的考察分析,梳理出全景式的舞蹈發展脈絡,為后人留下鮮活有據的舞蹈史。②
其次,舞史研究也應當樹立“舞蹈生態”意識,從舞蹈文化發展的宏觀視角去探尋舞史線索,自覺將各個歷史時期,特定時代的舞蹈蹤跡,與作用其生發興衰的人文環境——生態因素,諸如經濟、政令、宗教、民俗、禮儀、生活起居等結合起來予以系統性的考察,使已知的舞史線索得以拓展、深入,并有望從與舞蹈相關的諸多生態因素中,得到啟迪與提示,實現舞蹈歷史形態的“復活”。資華筠先生曾說過,與舞史研究密切相關的是“中國古典舞”的“復興”與“再造”。③在學界的舞史考察爬梳中,我們有歷史悠久、連綿不絕的不同朝代的或雅俗共賞、或輝煌燦爛、或異峰突起、或融于戲曲的舞蹈發展歷程。但“缺乏現成的、蘊含著傳統文化精髓、以‘人體語言體系為表征的、完整的‘中國古典舞。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當代‘中國古典舞具有‘復興與‘再造意義”。
一、“當代中國古典舞”的特質
“古典舞”并非“古代舞”,這個概念是指各個國家和民族歷史上流傳下來的、具有典范意義的舞蹈。這里的“典范”一詞,傅雷先生在《傅雷談音樂》中做過精辟的闡釋:“‘古典作為一種價值觀念,是在一定文化圈內或在世界規模內從古至今的歷史中繼續保持著恒久的生命力,‘古典意義的最高境界是在其價值觀念方面追求‘經典意義,也就是追求歷史地位上的獨特性及現代意義上的魅力經久性。”與世界各國的古典舞相較而言,西方的古典舞“芭蕾”,自文藝復興之后逐漸發展成熟,形成了具有嚴格規范和程式的舞種,有國際統一的認定標準,東方的日本、韓國、泰國等國家各自保存著歷史悠久、代代相傳的經典舞目和固有的古典舞學體系、學派。再如印度古典舞,以婆羅多、卡塔克、卡塔卡利、曼尼普利、奧迪西、庫吉普迪等為代表的六大學派,業已形成嚴謹、規范的表演、訓練體系,其“復現”過程,一招一式地嚴格依照古代文獻提供的圖文資料,因此被世界公認為保存最完整的傳統舞蹈文化體系。
而今日中國古典舞比之以上,可謂是嗷嗷待哺的新生兒,是由中國當代舞蹈家于20世紀50年代以“古典舞”的名義創建的“古典舞”的形態④,尤其是新中國第一代專業舞蹈人學習中國古典舞,沒有現成的教材和舞目,大都是從學習身段性較強的京劇、昆曲的折子戲入門,老師從戲曲中提煉、整理舞蹈片段:起霸、趟馬、水袖、劍、刀槍把子等當教材,再經過北京舞蹈學院幾代舞蹈教育者的探索,實現了“脫胎”與“再造”。它繼承了中國傳統戲曲、武術中的精華,也借鑒了西方芭蕾舞體系程式化訓練的經驗,提煉了中國傳統藝術神韻的審美特質
二、北京舞蹈群落中國古典舞的“源”與“流”
史紅教授在《北京舞蹈群落的特征》一文中指出:“‘北京舞蹈群落主要是指在北京舞蹈生態環境下所形成的,并與北京舞蹈生態環境相互作用的各個舞種所有的舞蹈團體、組織的共同聚集的組合。其表現是舞種齊全、結構復雜、位勢不一、相互依存。它是中國集聚性最高、舞蹈水平最高、種群數量最多、人才實力最強的群落。⑤
在其對北京舞蹈群落的空間分布特征論述中,她強調海淀區是舞種(特別是當代中國古典舞)起源地、生長地,也是當代中國古典舞表演、教育、創作人才培育中心,其次,基于對當代中國古典舞的教學、創變化使遺傳因子發生變異,或因雜交而分化出新舞種型,這個發生中心也在海淀。同時,海淀區通過舞蹈人才散播其舞蹈思想、方法的這一自力散播,使舞種擴展到新地區。
可以說,在北京的舞蹈生態環境的土壤上孕育了原生舞種——中國古典舞,對其的考查可以總結出該舞種的發生機制。
(一)肇始——發掘戲曲資源
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是中國古典舞的起步階段,這一時期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中國百廢待興,發掘中國古典舞蹈文化,建構中國自己的舞蹈形式,與當時的社會氛圍和國人的心理需求形成了完美的自洽關系,1950年,在歐陽予倩任編劇和導演,為中央戲劇學院舞蹈團創作的大型舞劇《和平鴿》中,他專門請了戲曲老師為舞蹈演員指導教學,雖未明確提出該概念,但受到他的啟發,中國古典舞的前輩葉寧先生首次使用了“中國古典舞”一詞。⑥明確了中國古典舞的發掘整理應當以戲曲舞蹈為基礎,由葉寧先生負責的教研組成為中國古典舞研創的開端。
(二)確立——創建訓練教材
1954年,北京舞蹈學校建立,舞蹈教員訓練班開學,至此開始真正有了中國古典舞課程,此時的學員有李正一、孫光言、孫穎、唐滿城等,日后,他們成為當代中國古典舞的學科帶頭人。從教材建設入手的中國古典舞,以戲曲、武術為基礎,整合了當時唯一能夠被看到和參照的蘇聯芭蕾訓練方法,制定出了一套基礎訓練教材,表現為上肢戲曲身段與下肢芭蕾的結合。囿于歷史和時代的限制,這種中西結合的古典舞訓練體系較多強調了芭蕾在人才培養中重視的訓練性,而忽視了其內核對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把握。
(三)發展——形成審美觀念
1979年,北京舞蹈學校升格為北京舞蹈學院,20世紀80年代初期,北京舞蹈學院教育系招收了第一批中國古典舞專業的本科生,1984年設立中國古典舞教育專業,1985年桃李杯舞蹈大賽中,中國古典舞是主要參賽舞種項目,1987年,北京舞蹈學院撤銷中國舞系,建立中國民族舞劇系,即今天的中國古典舞系,分教育和表演兩個專業。這一時期中國古典舞的重大發展在于觀念上的實質性突破,具體表現有二:一是對中國古典舞“基訓”形式的反思,二是在對中國古典舞訓練課反思形式上成型的“身韻”。“身韻”對古典舞訓練體系及古典舞創作的語言開拓都產生了良性“反哺”作用,也因其部分地解決了古典舞“民族性”或說審美問題,“身韻”當之無愧地在中國古典舞發展史中占據了不可替代的歷史地位。⑦
(四)生發——多元流派紛呈
舞蹈生態學中強調,舞蹈譜系演進特點不是一蹴而就的量子式演化而是漸進式演化。舞蹈譜系具有一種內稟的趨于結構復雜與多樣的演化趨勢,結構層次會增多,分化程度會增大,成為復雜性增長。即便在穩定的舞蹈生態環境中,舞蹈譜系也會不斷演化而向前發展;當環境改變時,舞蹈譜系會做出新的調整,從而逐漸地產生結構變化,往往是微小變異的連續累積。
當代中國古典舞在深入開掘,集成傳統文化精神和凸顯東方神韻方面,有待進一步完善,但可以從各個流派的訓練體系的相對完整,舞蹈語言的相對自洽,已經積累了以其語言體系為創作基礎的優秀舞目等,來驗證這個譜系的發展。
20世紀80年代至今,基本上形成了以北京舞蹈學院“身韻”為核心的中國古典舞教學體系占據主流,以復現漢唐舞蹈文化遺存為支撐的“漢唐舞派”,以敦煌壁畫中的舞姿形象為依據的“敦煌舞派”,以及從昆曲中提煉、生成的“昆舞”流派,還有從漢畫像和龜茲壁畫中的舞姿形象為依據進行重建復現的“漢畫舞蹈”和“龜茲舞蹈”。它們之間既相互關聯,又各具特色,這應當是中國古典舞發展軌跡之必然結果,劉青弋教授亦鮮明地指出“當代中國古典舞的不同流派已有明確分野,各自發展成熟,‘多元化格局得以成立。而且,在不同學派之間的對話中,學科建設也就獲得了生氣,學術思想趨向活躍。”⑧
三、北京舞蹈群落中國古典舞的“形”
當代中國古典舞的“多元”格局,表現在由不同的建構觀念而形成的形式上,其“多”源于人們對“古典”一詞的不同見解和其在歷史形態中的呈現出的不同層次;其“元”則應當是需要有一個體現民族意識形態和美學特征,代表中國傳統文化之精神的“根”。呂藝生先生曾明確指出對中國古典舞的發展不必否定“多”,而是要否定“多元”,因為中國古典舞的“元”只有一個。如果古典舞真的“多元”了,說明古典舞的寶塔根基不牢,如果根基牢固,小風格、小流派、小特點則越多越好。⑨
在舞蹈譜系演進中,由同一親本舞蹈演化而來的舞族、舞支、舞種的性狀與譜系親緣關系呈正相關,如果把中國古典舞看作是中國舞蹈譜系演化樹中的一族,那么“身韻”“漢唐”“敦煌”“昆舞”“唐樂舞”“漢畫”“龜茲”便是同屬于“中國古典舞”的不同語支,在語言形態上互不相融,且教學體系各異,但又被中國古典舞蘊含的文化傳統所制約。
以上對中國古典舞不同語支的分析,會發現中國古典舞從誕生之初發展至今,已取得了一些令人矚目的成果,其形是帶有民族審美特征的“形”,這些創建者們能夠立足于中國優秀的歷史文化傳統,總結前人半個多世紀復興中國古典舞的種種經驗與教訓,認真鉆研,擷取這個根基上生發出的任何有可能的“枝丫”,也正是不同流派的古典舞照亮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兩點,推動了中國古典舞的發展和演進,使之走向“和而不同”。世界是開放的,作為學術與藝術的中國古典舞研究與呈現也是一個開放的體系。
歷史規定了中國古典舞的文化屬性和民族屬性,時代規定了其表現形式特色的有別和審美情感的厚薄,那么中國古典舞的“源”“流”“形”就不可無視歷史和民族的根脈。
基于以上,舞蹈生態學的原理、方法對中國古典舞的探索,既可提供文化探源的理論依據,也有助于“復活”歷史舞蹈形態的實驗。面對當代眾多致力于復興中國古典舞的仁人志士的奮斗與探索以及各種爭議,舞蹈生態學可以提供辨析、論證的科學標準,倡導在中國傳統文化“理一分殊、合而不同”精神的照耀下,以及東方美學意蘊思想的關懷中,中國古典舞呈現出流派紛呈、色彩斑斕的圖景。“在這樣一個日趨‘文明的世界,我們需要建構的恰恰是一個‘文化的中國古典舞”。
注釋:
①資華筠.中國舞蹈生態學研究[M].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16:14.
②資華筠.中國舞蹈生態學研究[M].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16:15.
③資華筠.中國舞蹈生態學研究[M].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 2016:15.
④劉青弋.中國古典舞代表作重建的探索與思考[J].北京舞蹈學院學報,2014(5):22.
⑤史紅.北京舞蹈群落的特征[J].北京舞蹈學院學報,2013(6):26.
⑥田湉.中國古典舞的形式研究[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14.
⑦田湉.中國古典舞的形式研究[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20.
⑧劉青弋.關于中國古典舞的基本概念與范疇叢[J].北京舞蹈學院學報,2006(2):18.
⑨呂藝生.直面中國古典舞的危機:寫于北京舞蹈學院建校60年[J].北京舞蹈學院學報,2014(S2):10.
⑩田湉.中國古典舞的形式研究[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179.
參考文獻:
[1]資華筠.中國舞蹈生態學研究[M].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16.
[2]田湉.中國古典舞的形式研究[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3]劉青弋.關于中國古典舞的基本概念與范疇叢[J].北京舞蹈學院學報,2006(2).
[4]呂藝生.直面中國古典舞的危機:寫于北京舞蹈學院建校60年[J].北京舞蹈學院學報,2014(S2).
[5]史紅.北京舞蹈群落的特征[J].北京舞蹈學院學報,2013(6).
[6]史紅.互動:北京舞蹈群落與經濟[J].藝術百家,2011(5).
作者簡介:張銘(1981-),女,新疆烏魯木齊,副教授,研究方向為舞蹈史、舞蹈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