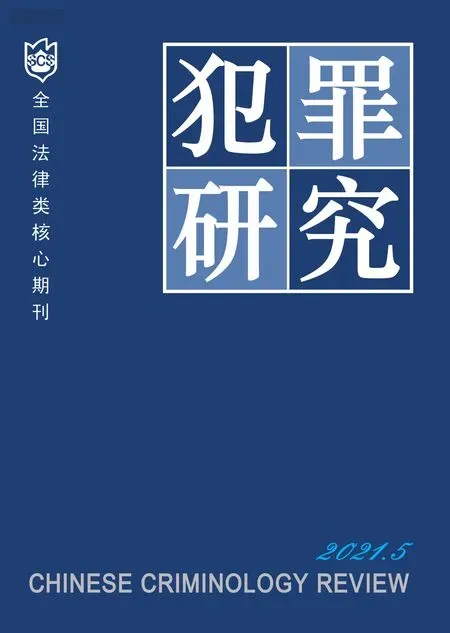猥褻兒童行為違法性評價要素分析
彭志娟
一、問題的提出——由三起泳池猥褻兒童案引發的思考
案例一:2016年8月某日,被告人李某某在某中學游泳池內,以熱心教游泳為由接近被害人方某(13周歲),伺機觸摸其下身私密處,被害人方某掙脫后在同學陪同下離開。法院對被告人李某某以猥褻兒童罪判處有期徒刑5年6個月。
案例二:2020年5月至6月間,被告人朱某在某健身公司游泳池內,利用擔任游泳教練的便利,以隔著泳褲或者將手伸進泳褲撫摸生殖器的方式,先后兩次對被害人趙某(男,7周歲)實施猥褻。法院對被告人朱某以猥褻兒童罪判處有期徒刑1年8個月,并處以從業禁止。
案例三:2018年至2020年的暑假期間,被告人陳某某在某健身會所游泳池內,以熱心教游泳為由,伺機隔著泳衣觸摸被害人張某(9周歲)的臀部、被害人鄭某(9周歲)的腹部,多次觸摸被害人艾某(7周歲)的陰部。法院對被告人陳某某以猥褻兒童罪判處有期徒刑5年6個月。
以上三起猥褻兒童犯罪都發生在游泳池的場景下,形式上都屬于“在公共場所當眾”實施猥褻,但法院判決在量刑上卻相差懸殊,尤其是案例一和案例二。這種差異背后是兩種觀點的碰撞。一種觀點認為,兒童不具備性的自主權,猥褻兒童罪侵害的法益是兒童特有的“性的不可侵犯性”,任何針對兒童實施的與性有關的行為都構成犯罪。泳池猥褻兒童案的被告人主觀上都是出于追求性刺激的卑劣動機,客觀上觸摸的兒童身體部位都不同程度地帶有性象征意義;而且泳衣單薄暴露,相比隔著日常衣著,觸摸行為對性權利的侵害程度尤為嚴重。因此,無須考慮場所等附加要素,被告人的每一個猥褻行為都可以單獨評價為猥褻犯罪。〔1〕參見張明楷:《加重情節的作用變更》,載《清華法學》2021年第1期,第42頁。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兒童的“性的不可侵犯性”體現在一經侵犯肯定追責,但不以追究刑事責任為必然。行為人以不同的侵犯方式侵犯兒童不同的身體部位,對兒童性權利的侵害程度就有了輕重之分,那么對行為人的違法性評價也應有寬嚴之別。若不加區別地將各個行為直接入罪,則有悖于罪刑相適應原則。〔2〕參見趙俊甫:《刑法修正背景下性侵兒童犯罪的司法規制:理念、技藝與制度適用》,載《政治與法律》2021年第6期,第36—37頁。
筆者贊同后一種觀點。基于特殊、優先保護原則,刑法對猥褻兒童行為設置的犯罪構成無須像強制猥褻罪一樣以強制手段為客觀要件,這導致司法實踐中出現一種傾向——凡是針對兒童的猥褻行為被一概入罪且趨于重罰。然而,我國法律規范體系實際上為猥褻兒童的行為設置了不同梯度的責任形式。其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1010條第1款規定:“違背他人意愿,以言語、文字、圖像、肢體行為等方式對他人實施性騷擾的,受害人有權依法請求行為人承擔民事責任。”其中的“他人”不排除“不滿14周歲的人”。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以下簡稱《治安管理處罰法》)第44條則規定:“猥褻智力殘疾人、精神病人、不滿十四周歲的人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由此可見,即使對象是兒童,刑法意義上的“猥褻”也需要限縮范圍,以便為認定悖德不當行為與一般違法行為留出余地。三個案例判罰迥異的癥結問題正是在于如何界分猥褻違法行為和猥褻犯罪行為。
二、猥褻兒童行為違法評價要素之設定
“猥褻”一詞缺乏明確的法律釋義,有學者指出其是“用性交以外的方式對被害人實施的能夠滿足性欲和性刺激的淫穢行為”〔3〕趙俊甫:《猥褻犯罪審判實踐中若干爭議問題探究——兼論〈刑法修正案(九)〉對猥褻犯罪的修改》,載《法律適用》2016年第7期,第81頁。。我國法律認可的“性交”僅限于男性與女性之間生殖器的結合,故而“猥褻”的外延極其寬泛,上至雞奸、口交、異物插入陰道或肛門等嚴重猥褻行為,下至騷擾短信、黃色笑話等悖德行為。近年來還出現了利用網絡實施的裸聊、裸拍等新型猥褻。面對林林總總的猥褻行為,很難在犯罪、違法以及不道德之間做到涇渭分明。這一方面是因為對猥褻的違法性界定富含道德評價色彩,任何一種界定都會遭到立于道德制高點的攻訐;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影響違法性評價的因素舉不勝舉,綜合考察過程中會給予自由裁量莫大的騰挪空間。然而,刑事司法的確定性要求在相對共識的基礎上建立一個猥褻行為違法性評價體系。因為是相對性的共識,這個評價體系囊括的只是就猥褻兒童行為而言通常應當予以評價的要素,包括狹義的行為自身要素和行為外部要素兩個層面。行為自身要素包括侵犯部位、侵犯方式、侵犯時間等;行為外部要素包括侵犯環境、侵犯主體、侵犯對象等。而且應將前者作為影響評價結果的主導方面。
(一)行為自身要素
1.侵犯部位
猥褻行為與“性”相關的聯結點在于其所侵犯的身體部位具有性象征意義,否則行為定性只考慮是否屬于傷害。侵犯部位的性象征意義的強弱直接體現出行為對性權利侵害程度的強弱(見表1)。

表1 以不同侵犯方式侵犯不同性象征意義部位的違法性質判斷一覽表
首先,性象征意義最強烈的身體部位莫過于性器官(或者說生殖器官)。使用性器官或者針對性器官實施的侵犯行為毋庸置疑屬于猥褻,在界分違法性時優先考慮認定犯罪。以強奸幼女的既遂標準“接觸說”為參照,使用性器官直接接觸兒童的性器官,除男性侵犯女童的構成強奸罪之外,其余情形均應當構成猥褻兒童罪;若隔著衣物間接接觸,也應當認定為猥褻兒童罪,原因在于性器官的結合是最大限度地模擬性交行為。使用性器官接觸兒童其他身體部位,或者使用其他身體部位抑或工具接觸兒童性器官,惡害稍次于前者,故直接接觸的應認定為猥褻犯罪,而間接接觸的則應歸入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法》的猥褻違法行為。例如,受托臨時照看鄰居小孩,趁私下獨處之機觸摸兒童性器官,隔著衣物的屬于治安違法行為;若將手伸進褲子貼著皮肉猥褻的,應當作為犯罪處罰。〔4〕如果行為發生在地鐵、商場等公共場所,還要結合行為之外的環境要素綜合評價,但為凸顯單個要素的評價意義,文中對諸要素的逐一分析均為剔除其他要素作用的單獨評價。
其次,公認的具有明顯性象征意義的身體敏感部位(以下稱“性敏感部位”),譬如乳房、臀部、大腿根部三角區域等。針對這些部位的行為屬于猥褻雖無爭議,但在具體行為屬于違法還是犯罪的把握上則有分歧。筆者認為應比照性器官與其他身體部位相接觸的評價標準,直接接觸的認定為猥褻兒童犯罪,間接接觸的歸入治安違法行為。理由包括如下兩點:其一,這些部位的性象征意義都極其強烈,有的甚至不亞于性器官,如女性的乳房。其他即使略有不及,卻同樣毋庸置疑地表征著性權利。無論是針對性器官還是針對乳房、臀部等性敏感部位,行為對性權利的侵犯程度雖有差異卻未達到“質”的差別。其二,近年來實務界多有主張強奸罪立法采納性別中立主義,把“肛交”納入“性交”的范圍。傳統觀念中身體部位的性象征意義正在發生衍變,尤其是針對兒童的性侵犯罪,對象的性別界限遠遠比成年人模糊,男童遭受性侵的案例日漸增多,對性敏感部位提升法律保護量級具有現實意義。
再次,性象征意義存在爭議的身體部位(以下稱“性爭議部位”),譬如腰腹、肩頸、腿部以及唇舌等。通常情況下,這些部位在日常交往中鮮少發生肢體接觸,即使接觸一般也不會令人產生性聯想。從司法實踐看,若這些部位成為系爭行為的指向,往往是行為人蓄意采用帶有性暗示意味的甚至是以露骨的方式進行非正常接觸,故此類違法性評價的首要任務是排除肢體接觸的合理解釋。若確認系爭行為是出于追求性刺激的動機,則綜合主客觀因素可以認定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法》,但入罪則須慎重。需要指出的是,針對性爭議部位的直接接觸行為,有別于必然有衣物遮蔽的性敏感部位,必須將是否排除衣物保護作為違法性甄別要件。理由在于:一方面,性權利主要體現于性的自主性和私密性,是否有衣物遮蔽反映被害人對性爭議部位的私密性保護要求;另一方面,排除妨礙的行為反映行為人明知違背被害人意志而決意實施性侵的主觀惡性。例如,伸手探入兒童衣物撫摸其腹部的行為,可以認定為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法》;看到兒童穿露臍裝而拍打其肚皮,則不宜直接認定為違法。
最后,明顯缺乏性象征意義的身體部位(以下簡稱“中性部位”),譬如手足、胳膊。在日常活動中經常發生合理的肢體接觸,諸如握手、踩腳、挽臂等。〔5〕本文只在通常意義上討論猥褻行為的要素,戀足癖等性倒錯行為不在其列。人們對中性部位的肢體接觸具有較強的心理承受能力,即使行為人的接觸手法帶有性暗示意味,可能會引起被害人的厭惡和不適,卻不至于造成“性恐懼”“性羞恥”等強烈的心理傷害。這些行為屬于“性騷擾”的悖德行為;結合其他要素,情節惡劣的,可以考慮作為《治安管理處罰法》意義上的猥褻處理。
2.侵犯方式
雖然行為人對兒童實施猥褻行為所采用的侵犯方式多種多樣,但在理論與實踐中,主要針對侵入深度和強制程度爭議較多,筆者將重點論述這兩個方面。
(1)侵入深度。猥褻行為對被害人身體的侵入深度越深,則違法性程度越嚴重(詳見表2)。第一,侵入被害人陰道、肛門、口腔等部位的“進入式行為”,具有毋庸置疑的違法性,需根據侵犯或被侵犯部位的性象征意義強弱進一步區分是否入罪。其一,使用性器官實施的“進入式行為”。如前所述,但凡使用性器官實施猥褻,應直接認定為犯罪;若是使用性器官侵入到被害人身體的內部,違法性質進一步惡化,應當作為加重處罰情節。由此,對兒童實施“肛交”“口交”的行為,在刑罰設置上,可以達到與奸淫幼女相當的水平。以上考慮吸收了性別中立主義立法觀,把“性交”的外延從男女生殖器的結合擴張到“肛交”和“口交”。雖然我國刑法對強奸罪的立法尚未采納這一觀點,但是將其要義運用到性侵兒童犯罪的法律規制中,符合性侵犯罪案發態勢的現實需要。其二,使用其他身體部位侵入陰道、肛門的行為,應當認定為犯罪;侵入口腔的,則以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法》作為底線。前者作為性器官或性敏感部位,所具有的性象征意義不容爭辯;后者屬于性爭議部位,需要結合侵入所使用的身體部位來綜合評判,如使用舌頭侵入口腔的,即對兒童實施舌吻,可以認定為猥褻犯罪;而使用手指等中性部位侵入口腔的,則以認定猥褻違法為宜。其三,使用工具實施侵入行為的,工具無所謂性象征意義,主要考察工具的致傷危險性和被侵犯部位的性象征意義。如侵入陰道、肛門的,構成犯罪無虞;侵入口腔的,若工具的致傷危險性較高,可能導致輕傷以上后果,應當入罪追究。

表2 侵入部位與被侵犯部位違法性質判斷一覽表
第二,侵犯深度僅限于被害人身體表面的“體表式行為”,違法性質主要取決于侵犯與被侵犯部位的性象征意義。前文對這一內容已有詳細闡述,此處不贅。在兩兩結合部位相同的情況下,行為的性暗示意味越明顯則違法程度越高。譬如隔著衣物用手觸摸臀部等間接接觸性敏感部位的行為,一般屬于《治安管理處罰法》意義上的猥褻,若將觸摸改成用手指模仿肛交摩擦臀縫,則可以考慮入罪。
第三,不接觸被害人身體的“隔空式行為”。有學者將猥褻兒童的行為分作四種情形:其一,行為人直接對兒童實施猥褻行為或者使兒童容忍第三人對之實施猥褻行為;其二,使兒童對行為人或者第三人實施猥褻行為;其三,使兒童自行實施猥褻行為;其四,使兒童觀看他人的性行為。〔6〕參見段衛利:《猥褻兒童罪的擴張解釋與量刑均衡——以猥褻兒童的典型案例為切入點》,載《法律適用》2020年第16期,第121頁。從行為人的立場劃分,前兩種是有直接身體接觸的猥褻行為,后兩種是無直接身體接觸的猥褻行為。從兒童的立場看,前三者都是接觸式猥褻行為,不論兒童抑或第三人,都是行為人借以對兒童身體實施侵犯的工具人;第四種行為屬于真正無身體接觸的“觀看型猥褻”。無接觸式猥褻還有一種情形,即誘使兒童裸露性器官或者性敏感部位。“觀看型猥褻”導致性喚起效果,主要侵犯性的自主權,而“裸露型猥褻”主要侵犯性的私密權。一般而言,無接觸式猥褻的法益侵害程度輕于接觸式猥褻,違法性評價可以相對降低。例如,直接觸摸兒童性器官的行為構成猥褻兒童罪,而誘使兒童裸露性器官或者觀看性器官則屬于治安違法行為。從近年來的執法實踐看,由公安機關作治安違法處理的猥褻兒童行為,絕大多數是露陰癖。
(2)強制程度。猥褻行為對被害人身體的強制程度越大,則違法性程度越嚴重。在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的指導性案例“駱某猥褻兒童案”〔7〕最高人民檢察院指導案例43號(2018年)。中,駱某通過網上言語威脅、線下指使第三人施壓,強迫被害人自拍裸照供其觀看。一審法院認為強索裸照的行為不構成猥褻兒童罪,而二審法院改判該行為構成猥褻兒童罪(既遂)。如前所述,筆者認為誘使兒童裸露性器官或者性敏感部位的“裸露型猥褻”屬于治安違法行為,但本案中的行為人駱某不僅唆使兒童自拍裸照,而且采用了強制手段,使行為的違法性質升級。
第一,強制手段的加持作用。鑒于兒童對性相關事項缺乏認知能力,猥褻行為即使在形式上得到兒童的同意也視為承諾無效,系爭行為依然屬于違法乃至犯罪。舉輕以明重,在兒童表示拒絕的情況下強行實施猥褻的,強制手段使行為的違法性質升格,原則上應作為犯罪追究刑事責任。
第二,強制手段的成立底線。搶劫罪的本質是通過強制人身來謀求財產利益,而性犯罪是通過強制人身來謀求性利益,故而兩者對強制手段的強度有不同要求。前者要求達到足以壓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而后者重在表征“違背被害人意志”,根據案發情境和被害人身心特征綜合評價,如深夜入戶冒充丈夫與半夢半醒的妻子發生性關系,未使用強制手段也構成強奸罪。這緣于法律的推定,即在此情境下與配偶以外的男性發生性關系會在實質上違背婦女意志。而兒童因其身心發育的限制,難以有效地對猥褻行為表達反對或者進行反抗,往往遭受嚴重心理創傷卻不敢或者不懂如何求助。有鑒于此,在兒童明確地以語言或者行動做出抗拒表示后,行為人繼續實施猥褻行為的,應當認定為使用強制手段猥褻兒童,從而應作違法評價。例如,隔著衣服撫摸兒童乳房,一般屬于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法》;若在兒童掙扎抗拒的情況下緊緊抱住兒童繼續撫摸,雖然沒有毆打、踢踹、捆綁等明顯暴力,但也視為使用強制手段,從而認定其行為構成猥褻兒童罪。
第三,強制手段的加重處罰。使用強制手段導致輕傷以上實害結果的、具有導致重傷或死亡的具體危險的、伴有明顯的肉體或精神痛苦的或者留下嚴重精神創傷甚至引起被害人自殺的,作為加重處罰情節。上述手段勢必嚴重違背被害人意志,對性權利的侵犯程度越高,違法性評價自然應越嚴苛。
3.侵犯時間
猥褻行為的持續時間長短與違法程度高低成正比。如果依據侵犯部位和侵犯方式仍難以對行為作出是否入罪的判斷,說明部位和方式的“性”意義不明顯,則需將侵犯時間作為輔助判斷項。例如,親吻兒童的臉部,屬于“體表式行為”,涉及的部位包括嘴唇或者臉頰、額頭,這些部位都屬于性象征意義存在爭議的部位。若是短時間接觸,如快速親一兩下,難以區分是表達喜愛的親昵行為,還是滿足性欲的猥褻行為;但若是長時間地反復親吻,吻住不放地吮吸、舔舐,則應歸入猥褻違法行為;若是長期多次實施這種猥褻行為,則可以認定為猥褻兒童罪。
(二)行為外部要素
1.侵犯環境
猥褻行為發生的環境影響對性的私密性的侵犯程度,故法律規定對在“公共場所當眾”實施猥褻的行為加重處罰,何謂“公共場所當眾”在司法實踐中爭議不絕。對此,筆者認為應主要把握以下兩個方面:
(1)“當眾”是環境要素的核心。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印發的《關于依法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以下簡稱《性侵意見》)第23條的規定,在校園、游泳館、兒童游樂場等公共場所對未成年人實施強奸、猥褻犯罪,只要有其他多人在場,不論在場人員是否實際看到,均可以認定為在公共場所“當眾”實施犯罪。自此開啟了對“公共場所當眾”的擴張解釋。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典型案例“吳茂東猥褻兒童案”〔8〕參見張先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三起性侵害兒童犯罪典型案例》,載《人民法院報》2014年1月4日,第4版。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的指導性案例“齊某強奸、猥褻兒童案”〔9〕最高人民檢察院指導案例42號(2018年)。進一步表明,只要場所具有相對公開性,且有其他多人在場,有被他人感知可能的,就可以認定為在“公共場所當眾”實施猥褻。學校的教室,乃至集體宿舍,都可以視作“公共場所”。從上述解釋的演變趨勢看,“公共場所當眾”的重心日漸向“當眾”傾斜。筆者對此的理解是,“公共場所”指向的法益偏重于“社會風尚”或者說“公共秩序”,“當眾”指向的法益則偏重于“性的私密性”,而猥褻犯罪保護的核心法益是性權利,故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解釋的法益保護取向是合理的。在人群聚會的私人住宅里當眾實施猥褻,相比在空無一人的夜半公園,前者的性質更為惡劣,所以環境要素的關鍵是如何理解“當眾”。
(2)“公然”是“當眾”的核心。《性侵意見》對“當眾”的解讀是“只要有其他多人在場,不論在場人員是否實際看到”。這種理解在嗣后的實踐中受到一定限縮,“其他多人一般要在行為人實施犯罪地點視力所及的范圍之內”,但僅此仍不足以遏制“當眾”情節泛化而導致的罪刑失衡問題。筆者認為要回歸“公然”這一“當眾”的本義,從而凸顯行為人嚴重侵犯性的私密性的主觀惡性和客觀危害。事實上,許多猥褻行為人之所以選擇在人群中作案,是因為如此才能更好地接近作案目標。行為人主觀上并不愿意暴露自己的猥褻行為,客觀上便采取了借助外物或體位進行遮擋或者采用隱蔽的作案手法,使在場的他人難以發現,事后證明也確實沒人發現。在這種情況下,盡管有其他多人在行為人視力所及范圍之內,也不宜認定“當眾”,否則公共場所的“咸豬手”都將以犯罪論處,甚至被科以重刑。“當眾”的認定應當兼顧主客觀兩方面。若行為人主觀上無所顧忌,甚至追求被發現、被圍觀的刺激,客觀上采取的行為方式也很容易被發現,甚至吸引他人注意,則不論在場人員是否實際看到,都應認定為“當眾”實施猥褻。若行為人主觀上不希望被發現,客觀上也采取了切實有效的遮擋、隱蔽措施,雖然無法完全排除被發現的可能性,但可以參照過于自信的過失處理原則,即以結果論,猥褻行為客觀上被他人發現的,認定“當眾”實施猥褻,反之則不予認定。“當眾”實施猥褻的,對行為的違法性質應當升格評價。
2.侵犯主體
主體要素中需要重點關注行為人的職責、前科等事項,至于行為人的性別,無論男女應予一視同仁。
(1)主體性別無關評價。司法實踐中,對女性猥褻男童的行為存在非罪化處理的傾向,尤其是在男童發育健壯又對性行為采取主動的情形下。這種傾向源自傳統兩性關系的影響,女性長期居于弱勢地位,形成了在性行為中被動的、吃虧的固化印象。然而,在猥褻兒童的涉性行為中,相對于身體和心智都未發育成熟的兒童,女性卻是處于優勢地位的一方,給兒童造成的身心傷害并不遜于男性,同樣可能使兒童終身對性感到恐懼或者厭惡。在“13歲男童浴場接受‘性服務’案”〔10〕參見金澤剛:《由男性遭受性侵害案看性犯罪的法律變革》,載《法治研究》2015年第3期,第39頁。中,即使涉案男童已具備性能力,主動要求發生性關系,對涉案“女技師”也應當認定為猥褻兒童罪。如果性別角色互換,對于“男技師”認定為強奸罪,應該不會有太大爭議。
(2)特殊職責從重處罰。根據《性侵意見》第25條的規定,對未成年人負有特殊職責的人員、與未成年人有共同家庭生活關系的人員、國家工作人員或者冒充國家工作人員,實施強奸、猥褻犯罪的,更要依法從嚴懲處。《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簡稱《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了“負有照護職責人員性侵罪”,雖然該罪的侵害對象特指“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未成年女性”,但立法精神一脈相承,可以貫徹到猥褻兒童罪的司法實踐中。行為人濫用基于身份或者職業而形成的與兒童之間的信賴關系,侵害了基于信賴本應受到其保護的兒童的性權利,使之陷入更加無助的危險境地與惡害之中,應當對其從重處罰。
(3)再犯行為評價升格。性侵犯罪再犯率高,大多是由于生理和心理雙重因素的影響。相關調研發現,對有性侵記錄的群體進行長期跟蹤,時間越長,再犯率越高。〔11〕參見《中國應該“化學閹割”強奸犯嗎?》,載中華網2016年11月3日,https://news.china.com/socialgd/10000169/20161103/23846038.html。換言之,性犯罪的欲望并不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淡化。有些國家嘗試用化學閹割來遏制性侵犯罪增長,但此舉面臨社會安全防衛和基本人權保障之間的價值沖突。從防控再犯風險的角度看,筆者建議對于曾有性侵前科或劣跡的重點人員,一旦再次實施猥褻兒童的行為,無論前后行為之間間隔多少年,均應當將再犯情節作為入罪的充分條件。若猥褻行為已然構成基本犯,具有再犯情節的,應當加重處罰;若猥褻行為具備其他加重情形,同時又系再犯,應當處以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罰。
3.侵犯對象
猥褻兒童罪的對象是不滿14周歲的兒童,包括男童和女童,常見爭議集中在是否細分加重處罰年齡和男女性別平等保護等。
(1)不宜細分重罰年齡。《刑法修正案(十一)》對奸淫幼女的行為,在“以強奸論,從重處罰”的基礎上,增加了“奸淫不滿十周歲的幼女”加重處罰的新規,從而產生了是否需要對猥褻兒童罪比照執行的問題。探究細分年齡段的初衷,應該是考慮到年齡越小則性侵行為對其造成的身心傷害越嚴重。但是,處于生長發育期的兒童有別于成年人,個體之間的身心發育狀況差異巨大。一方面,“一刀切”的年齡標準所具有的科學性與合理性令人生疑;另一方面,該標準也難以回答為什么不選擇推定“明知”幼女的12周歲或者與無民事行為能力相匹配的8周歲。其實,年齡越小則傷害越大的邏輯只在典型的性侵行為模型中成立,而奸淫幼女的既遂標準依然采用“接觸說”,接觸式的奸淫行為對已滿10周歲的幼女或者未滿10周歲的幼女,在侵害程度上并無實質性差別。在以往實踐中,對幼女實施接觸式強奸的行為人一般判處4年左右有期徒刑,今后將以被害人是否年滿10周歲為分水嶺,驟升至10年以上有期徒刑。如何調整罪刑之間的平衡,將是對司法智慧的考驗。猥褻兒童的各種行為方式之間的輕重差異較之強奸更為懸殊,若按照對象年齡截然劃分刑罰輕重,勢必帶來更多操作上的困境。依筆者看來,性侵低齡幼童的特殊危害可以通過其他指標得以體現,如侵犯方式對身心造成傷害的結果或者危險等。將細分年齡段作為加重處罰情節,不僅沒有必要,恐怕還有重復評價之嫌。
(2)平等保護不分性別。筆者始終堅持性別中立主義,主張對遭受性侵的兒童不分性別地予以同等保護。雖然針對男童的性侵行為,即使強行實施性交,也只能以猥褻兒童罪規制,而男性對女童實施性交的則構成強奸罪,但是兩者在施加的刑罰量上可以相對地保持平衡。正常性交之外的“肛交”“口交”等“進入式”猥褻行為,無論是針對男童還是女童,應當參照強奸罪科處大致相當的刑罰量。
上述針對行為自身要素和行為外部要素所作的單個猥褻行為的違法評價,僅僅是實踐中在通常情況下的考量,無法囊括所有影響因素。在進行具體評價時,行為自身要素是每一個猥褻行為的必備要素,也是評價的基本要素,對于違法性質的判斷具有決定性作用。行為外部要素屬于選擇性要素,在特定情形下對猥褻行為的違法評價具有加持作用,如“當眾猥褻”“猥褻再犯”等。單個猥褻行為的違法性質,在遵從罪刑均衡原則的前提下,最終取決于行為自身要素和行為外部要素的疊加作用。需要說明的是,筆者未將“社會惡劣影響”納入評價,是出于以下兩方面的考慮:一方面,若惡劣影響緣于行為人實施猥褻的方式、造成的結果或者自身的職責等案件事實要素,可以通過對這些要素的嚴厲評價從而折射出社會影響;另一方面,若是與案情無關的社會情緒宣泄,不應成為對行為人的譴責事由。司法者通過合理評估涉案要素,無須“社會影響”指標項,足以使裁判效果達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
三、猥褻兒童行為違法評價要素的實踐運用
(一)“當眾猥褻”的法律適用溯及力
《刑法修正案(十一)》對猥褻兒童罪一改以往參照強制猥褻罪從重處罰的立法模式,規定了專有的兩檔刑罰并列舉了4項加重處罰情形。其中,第2項加重情形“聚眾猥褻兒童的,或者在公共場所當眾猥褻兒童,情節惡劣的”,脫胎于舊法“聚眾或者在公共場所當眾犯前款罪(強制猥褻罪)的”,變化之處是“在公共場所當眾猥褻兒童”之后,加上了“情節惡劣的”后綴語,由此引發對新法溯及力的討論。有論者認為該處“情節惡劣的”是新增加的對加重情節的限制適用條件,〔12〕參見李琳:《《刑法修正案(十一)》中猥褻兒童罪加重情節的理解與適用》,載《現代法學》2021年第4期,第199—200頁。意即新法輕于舊法。筆者對此持不同意見。誠如參與法律修訂的專家解讀,《刑法修正案(十一)》列舉的4種加重情形,旨在發揮立法規范指引、行為評價的功能,可用舊法“有其他惡劣情節的”加重情形予以涵蓋。〔13〕參見張義健:《〈刑法修正案(十一〉)的主要規定及對刑事立法的發展》,載《中國法律評論》2021年第1期,第52頁。“有其他惡劣情節的”加重情形由《刑法修正案(九)》增設,是與“聚眾”猥褻、“在公共場所當眾”猥褻等加重情形并列的兜底性規定,同屬《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以下簡稱《刑法》)第237條第2款。根據同類解釋規則,并列的情形之間應當危害程度相當,“在公共場所當眾”猥褻在作為加重處罰情形時,達到“情節惡劣”的程度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對于《刑法修正案(十一)》在“在公共場所當眾猥褻兒童”后面追加的“情節惡劣的”表述,只能視作提示性規定,在修正案生效前發生此類情形的,按照“從舊兼從輕”原則,應當適用舊法。
(二)“多人或者多次”的加重處罰條件
“猥褻兒童多人或者多次”是《刑法修正案(十一)》在猥褻兒童罪中列舉的4種加重情形之一,如前文所述,可由舊法“有其他惡劣情節”所涵蓋,在作為加重處罰情形時,同樣要達到“情節惡劣”的程度。若單純按照人次計量,各種猥褻行為的危害輕重懸殊,輕微危害行為縱然多次累加,也難以匹配法定刑升格的嚴厲性。筆者認為“多人或者多次”的情形要達到“情節惡劣”應當滿足兩個條件:其一,“每一人”或者“每一次”均單獨成立猥褻兒童罪的基本犯。參照《刑法》其他類似規定,在將多次行為作為“多次犯”的基本犯構成時,不要求每次行為都構成違法,但是在將多次行為作為加重處罰情節時,卻要求每次行為單獨構成基本犯。例如,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搶劫、搶奪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中規定,“對于‘多次’的認定,應以行為人實施的每一次搶劫行為均已構成犯罪為前提”。其二,至少有“一人”或者“一次”系完全基于行為自身要素而構成猥褻兒童罪。如果允許行為外部的要素不受限制地疊加評價,可能導致本身違法性質輕微的行為被過度評價而壘高刑罰。
(三)對三起泳池猥褻兒童案的個見檢視
將三起泳池猥褻兒童案置于筆者所設定的違法評價體系中,逐一分析如下:
關于案例一。被告人李某某伺機觸摸被害人方某下身私密處,采用的侵犯方式是體表式行為,且系間接接觸,方式的違法程度一般;下身私密處指陰道,作為性器官具有最強烈的性象征意義,直接接觸的構成犯罪,間接接觸屬于違法,故從行為自身要素考察,被告人李某某的猥褻行為只是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法》。再考察行為外部要素,從“被害人掙脫后在同學陪同下離開”的表述推斷,被告人李某某在猥褻行為被拒絕后,當著第三人仍繼續糾纏,主觀上并不排斥被他人看見,符合公然的特征,屬于“在公共場所當眾”猥褻的情形,從而導致違法性質升格。所以,對被告人李某某的行為應當整體評價為猥褻兒童罪的基本犯。法院判決對其適用加重處罰,未免過度評價違法程度。
關于案例二。被告人朱某一次將手伸進泳褲撫摸被害人趙某的生殖器,系采用體表式行為直接接觸性器官,僅憑行為自身要素已然構成猥褻兒童罪的基本犯;另一次隔著泳褲間接接觸被害人性器官,屬于猥褻違法行為。同時,被告人作為游泳教練利用教學期間的職責便利猥褻學員,行為外部要素的主體要素具有從重處罰情形。即使不考慮環境要素是否屬于“當眾猥褻”,或者對象要素是否對男童同等保護,法院判決對被告人朱某僅處以有期徒刑1年8個月兼從業禁止,處罰明顯偏輕。
關于案例三。被告人陳某某隔著泳衣分別觸摸三名兒童的陰部、臀部、腹部,系采用體表式行為間接接觸性器官、性敏感部位和性爭議部位。從行為自身要素考察,前兩個行為屬于猥褻違法行為,摸腹部屬于性騷擾行為。再考慮行為外部要素,被告人陳某某在有人近距離旁觀的情況下偷摸女童陰部,又在有家長警告之后猥褻其他兒童,證明其主觀上不排斥被人發現,可以成立“在公共場所當眾”猥褻的情形,因而三個行為的違法性質升格;但“摸腹部”的行為升格之后仍不構成基本犯,“摸陰部”“摸臀部”是將“當眾”的環境要素納入評價才構罪,“摸陰部”的“多次”中沒有一次是基于行為自身要素達到犯罪程度,所以本案并不符合“多人或者多次”作為加重情形時的“情節惡劣的”要求,在基本犯的刑罰幅度中從重處罰足以體現罪責刑相適應,法院對被告人陳某某適用加重處罰的判決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