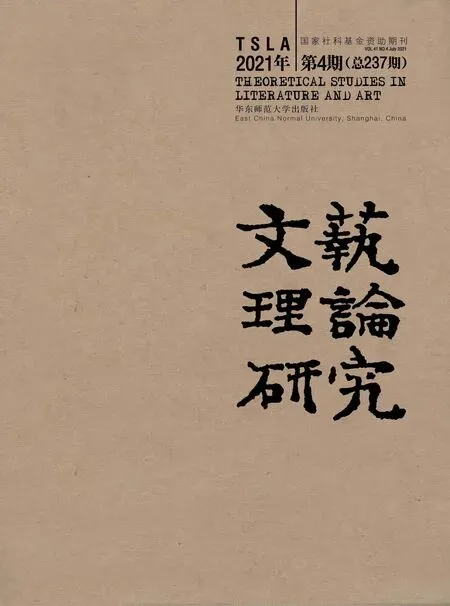崇高的性別維度
——女性主義視野中的崇高論
陳 榕
2015年,美國文學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發表了《神魔知道》,這是他生前最后一部聚焦美國文學的專著,其副標題是“文學的偉大與美國的崇高”。布魯姆在書中列出了符合他心目中崇高尺度的12位美國偉大作家: 拉爾夫·瓦爾多·愛默生、納撒尼爾·霍桑、赫爾曼·麥爾維爾、瓦爾特·惠特曼、艾米麗·迪金森、亨利·詹姆斯、馬克·吐溫、羅伯特·弗羅斯特、華萊士·史蒂文斯、T.S.艾略特、威廉·福克納與哈特·克蘭。其中只有一位女性: 詩人艾米麗·迪金森。他在2011年的《影響的剖析》中也討論過崇高的文學傳統,當時他的討論重點是英美詩歌史,三位代表性作家分別是作為“文學的崇高的代表”的威廉·莎士比亞(Bloom,The
Anatomy
41)、“理性崇高浪漫主義者”的珀西·比希·雪萊(143)、“美國崇高”代言人的瓦爾特·惠特曼(9),均是男性作家。著作還提及了數十位詩人,男性作家占絕大多數,其中約翰·彌爾頓、威廉·華茲華斯、W.B.葉芝、T.S.艾略特、克萊恩·哈特等均有相當篇幅的論述,女詩人只有3人被提及,分別是艾米麗·迪金森、伊麗莎白·布朗寧和伊麗莎白·畢肖普,而且每個人都是浮光掠影地簡筆帶過。布魯姆是一位在當代一直堅持高揚朗吉努斯所創立的崇高傳統的批評家。公元1世紀,朗吉努斯寫作《論崇高》,指出“真正崇高的文章自然能使我們揚舉,襟懷磊落,慷慨激昂”(朗吉努斯82),所體現的是心靈的高度,“崇高的風格是一顆偉大心靈的回聲。”(84)隨著這部手稿在近代被發現,以及法國評論家布瓦洛等人的譯介,崇高不僅再度成為文學批評的核心詞匯,也引發了啟蒙思想家的關注,英國保守主義思想家埃德蒙·伯克和德國哲學家伊曼紐爾·康德分別對這一概念進行了重要擴充。埃德蒙·伯克將心理學維度引入崇高理論,指出崇高是恐怖引發的緊張焦灼和它的紓解帶來的愉悅,是痛和快樂共存的情感: 崇高來源于“心靈所能感受到的最強烈情感”(伯克36)。伊曼紐爾·康德則將崇高引入哲學領域,指出崇高感源于超出認知邊界的審美對象造成的挑戰,在崇高客體的激勵下,想象力被延伸,借助理性的參與,對無法把握的形式進行有效的捕捉,是“自己超越自然之上的使命本身的固有的崇高性”(康德,《判斷力批判》101)。朗吉努斯的崇高文體、伯克所言的痛與樂共存的審美體驗,以及康德所強調的主體超越感,都是布魯姆崇高論的理論基礎。布魯姆在《西方正典》中提出追求崇高,是在“追求超越極限”(Bloom,The
Western
524)。在《影響的剖析》中,他指出崇高的作品會以美學意義上的“艱辛的喜悅”作為我們審美的回報(The
Anatomy
17)。在《神魔知道》中,他贊美崇高的價值在于“試圖超越人的界限,同時又對人文主義有所堅守”(Bloom,The
Daemon
1)。顯然,布魯姆所繼承的是朗吉努斯—伯克—康德一脈的崇高論,這也是經典崇高論的主調,人們早已習慣在這個框架之內討論崇高的人性、超越性和審美體驗。問題在于,這種崇高美學的核心詞是“人性”“超越性”“美感”等具有普世意義的詞語。然而,當布魯姆用崇高性作為英美文學經典的鑒別尺度時,上榜的女作家為什么會如此鳳毛麟角?我們是應該將這種稀缺歸咎于女性作品沒有超越性,無法體現崇高之美嗎?有沒有可能布魯姆所秉持的崇高論存在某種隱形標準,不兼容女性的經驗,所以女性作家才無法上榜呢?
這種疑惑也在提醒著我們,在把崇高作為衡量作品價值的標準之前,有必要審視崇高本身的價值框架。崇高作為審美范疇,看似價值中立,具有普適性,然而,如果用性別政治的角度來審視它,就會發現布魯姆所繼承的崇高傳統,有著男性中心主義的政治無意識。這從崇高論的衍生同義詞中就可以看出端倪: 在不同的語境下,“the sublime”可以被翻譯為壯美、壯闊、雄渾、雄奇、陽剛之美……18世紀以來,崇高論衍生出諸多版本,但是這一基調始終存在。進入當代,隨著女性主義批評的深入,相關的理論反思才逐步展開。
20世紀80年代末,陸續有學者對傳統崇高論對女性寫作以及女性藝術的美學偏見提出異議,嘗試尋找、發現與定義女性崇高的特征。1989年,帕特麗莎·雅格爾發表了《朝向一種女性崇高》,該文章收錄于論文集《性別與理論: 女性批評對話》,是較早的批評嘗試。20世紀90年代,安妮·K·梅勒的《浪漫主義與性別》和芭芭拉·克萊爾·弗里曼的《女性崇高: 女性小說中的性屬與過度》兩部代表性專著相繼問世。進入21世紀,隨著《論蜘蛛、賽博格和神圣存在: 女性與崇高》《女性解放與崇高: 女性主義、后現代主義與環境》等著作的發表,學界對該論題的研討一直在持續。女性主義與崇高論的相遇與論爭,以及對彼此理論視域的補充,構成了當代詩學與美學理論領域頗為精彩的一頁。遺憾的是,我國學界對其關注少之又少,對崇高論的理解依舊沿用朗吉努斯—伯克—康德—布魯姆一脈的經典框架,未有涉及性別政治角度的深入討論。因此,本論文旨在呈現女性主義為崇高理論提供的新視野,辨析傳統崇高論的父權權力-話語機制,探討女性主義對崇高美學的重塑,理解基于女性經驗的審美范式、主體立場以及倫理驅動是如何影響當代的概念演進,并使崇高理論更體現問題意識和時代關切的。
一
第三版的《勞特里奇美學指南》收錄了美國美學家卡倫·漢森所撰寫的獨立詞條“女性美學”。在詞條中,漢森梳理了女性主義與美學的交織所帶來的美學意義的擴展:“由于‘美學’可能意味著與藝術的創作、屬性和接受相關的哲學分支,也可能是有關美與審美的理論,也可能是對感性知覺的研究”,所以女性主義美學可能涉及如下方面,即“通過批評實踐搜尋與拯救被藝術史所排斥的女性;或者是對審美概念以及理論的男性偏見進行批評審視;或者是發展其他方案,對藝術的創作和效果進行‘以女性為中心’的描繪;或者是在感性認識的表述中加入性別的敏感度”(Hanson499)。女性主義與崇高理論的相遇也符合以上女性主義美學的總體潮流,隸屬于“對審美概念以及理論的男性偏見進行批評審視”的做法(499)。它始于20世紀80年代末,從時間上看,晚于藝術領域對女性藝術傳統的探尋,藝術史學家琳達·諾希林(Linda Nochlin)早在1971年就發表了《為什么沒有偉大的女性藝術家?》的文章;也晚于女性主義在文學研究領域倡導的女性文學傳統的發掘,比如桑德拉·M·吉爾伯特(Sandra M. Gilbert)和蘇珊·古芭(Susan Gubar)合著的《閣樓上的瘋女人》發表于1979年,伊蓮娜·肖爾瓦特(Elaine Showalter)的《她們自己的文學》出版于1982年。但是正因如此,對崇高論的檢討才在一開始就吸納了女性主義成熟期的諸多思想,展現出強大的理論沖擊力。它不僅包含從理論角度的批評再審視,同時也關心對女性理論傳統的再發現、對女性經驗引入崇高論的新思考,以及對理論當代相關性的延伸討論。當然,這一切的基礎是它首先聚焦了經典崇高論所隱藏的歧視性意識形態。這是女性主義為崇高論帶來的重要視角: 反思經典崇高論的思維框架,從根本之處入手,拆解崇高美學的父權話語機制。
康德曾經說過:“鑒賞判斷必定具有一條主觀原則,這條原則只通過情感而不通過概念,卻可能普遍有效地規定什么是令人喜歡的、什么是令人討厭的。”(《判斷力批判》74)康德認為審美具有中立的共通感。女性主義卻發現,在崇高審美的“普遍有效的規定”中,什么是“普遍有效”的標準,是由男權話語所界定的。“崇高”原來僅僅是美的雜多樣式中的一種,它真正成為經典審美范疇,乃是通過與“優美”形成對比,使紛紜的美感被統攝于崇高與優美的兩極,在與優美這個同屬于廣義之美的范疇的對比中,崇高找到了自己的參照系:“美學史上,崇高經常被看作與優美對立的范疇,對崇高的研究也常常是在與優美的比較中進行的,因此崇高的特征大多與優美相對立。”(彭峰72)這種對位關系依托具有結構主義經典意義的二元對立框架,在男權中心主義的話語體系中,迅速和性別政治的二元對立機制嵌合在一起。男性理論家們在定義崇高的同時,也書寫著自身的性別屬性。崇高區別于優美,一如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的分野。為此,我們有必要回到崇高論的理論源頭,即朗吉努斯的《論崇高》,來看一看他的理論是如何為其后的父權話語的介入提供契機的。
朗吉努斯在《論崇高》中將崇高定義為一種修辭術,是語言能夠激動人心、提升靈魂的力量。為了進行形象直觀的說明,朗吉努斯將語言所激發的情感力量與我們面對壯美自然時的心理感受進行了類比,即崇高的文字對我們的靈魂沖擊,類同于我們面對浩瀚江海、面對星漢燦爛或者巖漿噴涌的壯觀場景時的心潮澎湃。當我們看到柔緩的潺潺溪流、燧石激發的微火,不會有激情,只能體會到溫和的愉悅感(朗吉努斯114)。朗吉努斯的類比法為崇高概念的拓寬打開了方便之門。第一,文學與自然物的類比,使后來的理論家可以對崇高進行跨學科跨領域的闡釋。朗吉努斯關心文學文體以及政治修辭術的崇高特征,但藝術、自然、文化現象等更廣泛的對象也可以引發同樣的審美情感。第二,朗吉努斯將作為審美主體的“我”引入崇高性的討論中,審美客體在“我”心中喚起的強烈情感是崇高審美的重要標識。第三,崇高在與之形成對位的優美中確立了它的審美范疇: 江河海洋在小溪的映襯下,格外波瀾壯闊。小溪的清澈引發和諧之美,卻無法喚起崇高的審美通感與愉悅共存的復雜體驗,也缺乏恣肆豐沛的感情強度。
正因如此,17世紀后期,當埃德蒙·伯克以及伊曼紐爾·康德化用朗吉努斯的理論,探索拓展這一概念的文化與美學維度時,都借用了朗吉努斯筆下小溪與大海、燧石與星光的對比,在此基礎上,建構起優美與崇高的概念對位。雖然伯克和康德對崇高論的關注各有側重,即伯克強調情感與文化的重要性,康德關心理性與道德的意義,但當他們將朗吉努斯的自然類比進行性別政治的引申時,兩者卻不謀而合地從自然現象移向文化現象,把海洋與小溪的類比,變成了男性與女性的類比、力量與柔弱的類比。性別刻板印象的植入,幫助男性氣質與崇高性掛鉤,女性氣質被界定為優美。女性主義所關注的就是這種話語機制對女性經驗的貶低和對女性主體性的剝奪。
首先,在這種話語機制中,女性與男性的差異被放大了,進而形成優美與崇高的審美兩極。男性與女性身高、體重、體力、皮膚等生理性差異被賦予了不同的審美屬性,女性柔弱、溫和、重情感等與文化塑形有關的特點也被進一步固化。朗吉努斯—伯克—康德一脈的崇高論的共性是對強力、高度以及龐大體積的推崇,男性的生理優勢變成了他符合崇高審美標準的例證,繼而又被用來印證他的精神和人格的力量,成為男性從自然屬性到精神力均優于女性的證據。
埃德蒙·伯克在《關于我們崇高與美觀念之根源的哲學探討》中形容道:“崇高的事物在尺寸上是巨大的,而美的事物是嬌小的;美的事物應該是平滑、光亮的,而崇高的事物則是粗糙不平的;[……]美不應當曖昧不明,而崇高則傾向于黑暗和晦澀;美應當柔和、精細,而崇高則堅固甚至厚重。”(伯克106)小溪—燧石—女性,她們同享嬌小、平滑、光亮、柔和、精細的屬性。海洋—星空—男性,他們共有巨大、粗糙、神秘深度、厚重的特點。康德在《論優美感與崇高感》中專設一節,標題是“論崇高和優美在兩性相對關系上的區別”,也沿用了女性優美的性別屬性設定。女性是和“我們男性有著顯著的不同”,愛打扮,喜歡輕巧的東西,“比男性精致,也脆弱”(37)。就像勞拉·朗格在《英國文學批評的性別與語言》中所注意到的,自然屬性與文化屬性的雜糅,最終是要為文化定義服務的:“優美代表著光滑、柔弱、微小、和諧,是新古典主義藝術想要表達的溫柔的情感和特質,體現著18世紀對女性氣質的要求。”(Runge174)
其次,在經典崇高論的話語機制中,女性的力量得不到承認,被貼上優美的標簽,以滿足男性對欲望客體的掌控感。力量與超越性是男性氣質的專利,與女性氣質的分野一起被建構成社會常識,“脆弱”“嬌柔”“精致”……伯克和康德用這些詞匯界定女性特質,它們蘊含著父權社會對女性的期待,承擔著規范社會秩序的作用,影響著女性的自我認知,逼迫女性主動內化這種看似“優美”實則柔弱化的設定。
康德認為女性的脆弱性導致了精神力的不足。“每種具有英勇性質的激情(也就是激發我們意識到自己有能力攻堅克難的激情),在審美上都是崇高的。例如憤怒,甚至絕望。”(Kant113)女性“多愁善感”又“慵懶”,缺乏崇高性,連負面情緒也不配擁有。伯克說:“我們臣服于我們所敬慕的,卻都喜愛那臣服于我們的,在前一種的情況下,我們是被控制的,而在后者我們則滿意于其溫順。”(伯克96)男性敬慕崇高的自然,喜愛溫婉可人的女子,這種喜愛難掩輕視。所以,伯克在《關于我們崇高與美觀念之根源的哲學探討》中將女人與寵物歸于同類。在“嬌嫩”一節中,和優美女性作類比的是小灰狗、塘鵝、阿拉伯小馬等。男性的隱喻動物則是獒犬與戰馬。在“平滑之美”一節中,伯克寫道:“漂亮的鳥類和獸類,身上那平滑的皮毛;美麗女人身上,那光潔的皮膚。”(97)在“漸進的變化”一節中,他贊嘆鴿子作為鳥類的完美線條,繼而贊美女性的身體也同樣順滑:“請來一位最美麗的女人,細細觀看她的脖子和乳房: 平滑,柔軟,線條流暢。”(伯克98)
伯克的三個例子,尤其是最后兩個,有著男性中心主義欲望驅動的赤裸目光。勞拉·普威在《十八世紀的審美與政治經濟: 性屬在知識的社會構成中的地位》中提醒我們,伯克的美學審視受到了18世紀社會政治經濟體制的結構性支撐。男性在婚姻市場占據主導地位,是審美主體:“女性是‘性’;男性是文化,是女性的甄別者。[……]將女性與身體相捆綁的歧視都是這樣一個系統所造成的效果。”(Poovey96)
第三,在經典崇高審美的話語機制中,女性經驗得不到認可,男性主體性成為現代性主體性的唯一模板。康德是啟蒙時期最關注現代社會的主體性生成問題的哲學家。但是,他對女性的主體能動性保持懷疑。在《論優美感與崇高感》中,他宣稱如果女性擅長希臘文,也會思考物理學中的力學,那可是了不起的成就,“簡直就可以因此而長出胡須來了”(Kant37)。這種論調被劍橋英文版《論優美感與崇高感》的編者帕特里克·弗雷爾森和保羅·蓋伊批評為“帶有厭女癥的傾向”(xxix)。但是康德的刻薄話不只是為了澆滅女性追求知識的熱情,他是在質疑女性是否具有學習知識所需要的理性。理性匱乏,又如何能駕馭審慎的道德反思?照此邏輯,學不好希臘文和力學的女性,是連道德自律都成問題的。然而,女性的日常經驗在反駁著他的論述: 在生活中,女性往往更善良,也更有同情心。可是康德認為這只能說明女性有好心腸,不能指望“這個優雅的性別能夠有道德原則”(39)。
康德的時代,正是啟蒙時代,西方世界以神為中心的世界讓位于世俗世界,人的主體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顯,這使天賦人權觀逐步成為社會共識。這個時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全方位的深刻變革,也在激勵著身處其中的女性的啟蒙與覺醒。康妮利婭·克林格注意到康德在此歷史時刻高揚崇高論,“這不是一個歷史偶發事件。它恰恰發生在性別關系產生變化的時代”(Klinger194)。康德用區別兩性關系的優美與崇高的二分法,將審美與文化和性別與父權制機制融合在一起,以普適性的審美合法化了父權制對女性的歧視: 女性在體力上柔弱于男性,在精神意志方面也缺乏能動性。她只有自發的道德情感,沒有理性的協助,無法實現對庸常生活的超越。男性相比而言缺乏天生的道德情感,但他更具理性,有冷靜的判斷力,能夠恪守道德律令。他有堅韌的勇氣,能夠征服自然,為自然立法;也能夠借助理性、想象力和實踐的多重力量,超越自身的有限性,因此,他是崇高的,這種崇高體現了“人類自由以及理性的成就。[……]將人與自然相區別,讓他獨立于自然,凌駕于自然之上”(Klinger196),也凌駕于“自然屬性”的女性之上。新誕生的現代性主體便是以這樣的崇高男性主體性為范式。它成為“在自然影響面前堅持我們的獨立性的一種強力[……]絕對的偉大只建立在他(主體)自己的使命中”(《判斷力批判》109)。男性得到了理性與力量的完滿承諾。女性無法談及主體,又何談能動性,故而她們拿不到超越性崇高的資格認證。
二
在辨析伯克以及康德所奠基的經典崇高論的性別壓迫機制之后,女性主義批評家們將思考的視角轉回了自身: 自18世紀崇高概念進入西方美學領域,成為核心范疇以來,在近三個世紀的時間里,崇高論默認男性主體性立場,反映男性經驗,推崇男性氣質。女性作家是否曾經嘗試爭奪審美場域的話語權,對男性理論家的女性歧視進行抗辯呢?她們是否感受到崇高論的評估體系的壓力,曾經有意識地思考過應對策略呢?
當代學界對女性主義發展史的全面梳理,讓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這位18世紀英國女性思想家回到了我們的視野。她曾經以英國思想家威廉·葛德文的妻子、小說家瑪麗·雪萊的母親、詩人波西·雪萊的岳母、政治理論家托馬斯·佩恩的朋友而聞名。在建構女性主義理論譜系時,她被溯源為女性主義的先驅思想家。20世紀后期,在深入研究她的理論貢獻時,人們才意識到她同時是一位美學理論家,作為埃德蒙·伯克和伊曼紐爾·康德的同代人,她曾經參與過有關崇高論的論爭,并從女性的角度,對以伯克為代表的男性崇高理論家提出了挑戰。
沃斯通克拉夫特對崇高論的興趣源于她的政治訴求。沃斯通克拉夫特對激進革命抱有友好的態度。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1790年11月,埃德蒙·伯克出版《反思法國大革命》,表明自己支持既有制度的保守主義立場。一個月后,沃斯通克拉夫特發表《為人權一辯》,作為閱讀伯克一書的回應:“(伯克)的復雜論證喚起了我的憤怒,時時讓我坐立不安。按照自然情感和普遍常識來看,(伯克的觀點)有很多問題。”(Wollstonecraft3)《為人權一辯》的行文形式是致伯克的一封信,實則是尖銳的批評檄文。伯克與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交鋒在于如何理解法國革命,再往深處看,是在于如何理解人權、人性和道德。伯克承認革命存在合理主張,但是他對人性善持有懷疑態度,認為社會的積弊在于人性之惡。激進革命無法成功,是因為它無法改造人性,革命暴力卻有巨大的破壞性:“唯見斷頭臺。”(Burke66)為此,他提出良好的社會秩序依靠社會成規的約束性力量,這種約束之力就是道德。沃斯通克拉夫特則認為人是有內在的道德感和理性的,所以人性向善。她認為社會之惡,惡在制度,既有的君主制維護貴族權益,漠視平民利益,這是對天賦人權的違反。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政治理念主張理性與平等,反對壓迫與剝削。在《為人權一辯》中,她期待法國大革命能夠推翻貴族統治,建立起人人平等的共和國。
基于同樣的天賦人權以及人人平等的立場,她反對伯克等男性理論家的審美體系對女性的貶低和排斥,并在《為人權一辯》中加入了自己捍衛女性審美權利的辯護,批駁了伯克在《關于我們崇高與美觀念之根源的哲學探討》一文中的性別偏見。沃斯通克拉夫特不反對伯克所提出的崇高和優美的審美范疇二分法,但是她反對伯克將女性摒棄在崇高審美之外。她發現伯克將男性形容成強者,因其有勇氣、有力量,所以崇高;而將女性刻畫成弱者,使得柔與美成為同義詞,女性只能順從男性對她的定義,乖乖待在優美的審美領域。
為了駁斥伯克的崇高審美排斥女性的荒謬性,她決定以伯克之矛,攻伯克之盾。在《為人權一辯》中,她采用了“翻轉戰略”(Wollstonecraft14),強調自己品格中的沉著冷靜與嚴肅真誠。她筆下的伯克虛榮、膽怯、瑣碎,喜歡大驚小怪,行為方式恰恰如伯克所鄙薄的女性。伯克懼怕革命、墨守成規,何來崇高的勇氣可言?他表現出的不正是所謂“女性化的軟弱”嗎?沃斯通克拉夫特將自己塑造成伯克的對立面: 她擁抱變革的力量,不畏懼新生事物,用理智指導行動,富有道德感,比伯克更符合崇高的標準。
沃斯通克拉夫特捍衛女性在崇高審美中的基本權利。為此,她把審美上升到神的賜予的高度:“沃斯通克拉夫特相信個人良知,將對神的敬畏融入她的崇高觀。”(Bromwich634)她提出崇高來自理性和道德的雙重加持,它不是男性的專利,而是上帝惠賜給每一個人的力量。在《為人權一辯》中,她寫道:“我畏懼崇高的(神的)權力,它創造我的動機一定是智慧的以及良善的。我依賴于他,所以我嚴格遵守自己的理性總結出的道德法律。[……]對上帝的畏懼讓我尊重我自己,是的,先生,我看重誠實的名聲,與有德之人的友誼,但是它們都遠遠不及我對我自己的尊重,這是一種啟蒙的自愛。”(33)沃斯通克拉夫特視上帝為崇高的最高形式,看似持有一種反啟蒙的立場,事實上,她的崇高觀從敬神入手,實現的是對自我的肯定。“神是理性的最高形式”(Mallinick9),女性和男性在神的面前一樣平等,一樣有理性,有資格進入崇高的審美領域。
沃斯通克拉夫特撰寫《為人權一辯》時,沒有提及康德。但是她認為崇高審美與理性有關,這一點和康德的觀點不謀而合。然而,康德認為女性沒有理性,無法實現崇高,對此沃斯通克拉夫特絕不會同意。如果沃斯通克拉夫特讀過康德的《論優美感與崇高感》,看到會希臘語的女性是要“長出胡須來”的論述,應該會和康德展開一辯。她很可能還會和康德展開另外一場辯論,原因是他們在如何認識女性情感的問題上也有分歧。康德認為女性的道德情感是自然之力,比理性劣等。沃斯通克拉夫特則認為女性之美包含情感之美。她不反對伯克為女性貼上優美的標簽。優美審美中的情感力量可以促進美德,令人向善,只有過度的柔弱和多愁善感不值得鼓勵。她的審美觀突破了伯克以及康德的崇高/優美所劃定的性別禁區。理性與情感、崇高與優美,都集合在女性身上,她們有著和男性同樣的精神世界。所以克里斯汀·斯科爾尼克指出沃斯通克拉夫特在致力于“讓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屬脫鉤”(Skolnik208)。珍妮特·托德認為這種性別觀念反映出沃斯通克拉夫特具有“雙性同體”的思想(Wollstonecraft14)。
然而,無論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思想多么超前于她的時代,都存在著這樣一個事實: 她的討論始終停留在男性理論家框定的概念領域之內。她反對同時代男性理論家的性別偏見,肯定女性的力量,但是只要不修訂崇高性的標準,崇高論對女性經驗的漠視和壓制就始終存在。崇高論歌頌強力,女性的生存現實是她們屬于社會弱勢群體。崇高論歌頌自由,女性在父權制社會卻一直被束縛在家庭的方寸之地,被鼓勵要做“家中天使”。在文學領域,女性作家的創作被批評為格局太窄,話題缺乏崇高性。連女性寫作本身都要遭受非議,在男性眼中,她們是一群“涂鴉女人”。以沃斯通克拉夫特本人的經歷來看,她試圖與同時代的男性思想家比肩,積極參與崇高理論的辨析與論爭,自覺運用崇高修辭進行文學實踐,然而,她在美學史上長期被忽略,影響力無法與同時代的伯克以及康德相比。她有女性主體意識的覺醒以及從男性手中奪取話語權的理論自覺,但其主張中不乏對男性話語的依賴,這說明了女性尋找獨立美學價值體系的艱難。
三
有沒有可能讓崇高審美表達女性經驗,對崇高論進行重新定義?有沒有可能建立女性崇高的評估體系,用新的審美標準來重新解讀女性書寫傳統?這是近三十年來女性主義批評家們的努力方向。伊蓮娜·肖瓦爾特在梳理英國女性文學傳統時,將這一傳統命名為“她們自己的文學”。20世紀末期女性主義者對崇高論的修正,則可以理解為對“她們自己的崇高”的探索。
崇高審美此前一直默認男性主體為理想審美主體。1989年,帕特麗莎·雅格爾撰寫《朝向一種女性崇高》,率先對這一立場提出了挑戰。她指出男性崇高是“唯我獨尊的帝國主義”模式(Yaeger192),主張征服他者,是一種互不相容的垂直思維。女性崇高則是水平式的,更有包容性,“向他者延伸,將自己延展向復數性的存在”(191),保留自我的邊界,同時擁有探索主體間性的樂趣。她用心理分析的方法來解釋這種差異性的成因: 傳統崇高建立在俄狄浦斯情結之上,充滿自我與他者的對抗;女性崇高是前俄狄浦斯式的狂喜,是對他者的向往(209)。雅格爾的文章篇幅有限,對女性文學詩學特征的分析不夠充分,但是它開啟了對女性崇高的理論探索。
如果在崇高論中加入女性的經驗與立場,用它重新思考文學史傳統,是不是可以發現被此前的崇高論所遮蔽的女性崇高的文學史風景?1993年,安妮·K·梅勒出版了專著《性別與浪漫主義》,就是要回應女性崇高文學傳統的問題。她將研究目光聚焦在崇高論影響力最大的浪漫主義文學時期。她認為浪漫主義研究不應該局限在享譽最多的詩歌領域,只關注華茲華斯、柯勒律治、拜倫、雪萊等男性詩人。能夠展現浪漫主義文學思潮復雜性的綜合考量應該把1780—1830年的文學通盤納入研究視野。如此一來,為數眾多的女性作家得以浮出地平線,也凸顯出男性浪漫主義和女性浪漫主義的差異: 它們在“主題關注、形式實踐以及意識形態定位等領域”都有所不同(Mellor2)。男性浪漫主義的成就集中在詩歌領域,作品反映了現代性主體在巨變時代的多樣化體驗。崇高審美源于男性對主體性的堅決捍衛,大寫的人站在宇宙中心,是意義的賦予者。面對壯美自然,華茲華斯式的孤獨者體會到靈魂升騰,外界回應著對自我的肯定;自我包容了整個世界。柯勒律治式的想象者將自我看作一種空無,空無的靈魂與神性之間搭建起永恒的關聯,消融了他者的特異性,將它收納入神性的大我之中。兩種立場的地基都是“想象力、視野性以及超驗性”的男性化視角(1)。女性浪漫主義所青睞的文類是小說創作。男性浪漫主義的崇高英雄進入女作家們的筆下世界,變成了哥特小說中的父權制暴君。他們為世界立法的狂妄、為所欲為的自大、不受控制的力量,是邪惡的源泉。
該如何鑄造有別于男性崇高傳統的女性崇高?梅勒發現女性浪漫主義的選擇是承認崇高客體的異質性特征,以女性經驗對它進行接納。所以“在女性浪漫主義傳統中,崇高與優美結合,產生的不是幾位男性浪漫主義詩人尋求的孤獨的幻象性的超驗體驗,而是把不同的兩個人連在一起的共通感”(Mellor103)。女性親近崇高自然,在自然的啟發下,人與人締結紐帶,家庭關系變得更加緊密。所以,梅勒稱這種女性崇高是“家庭化的崇高”(103)。
顯然,梅勒想讓女性崇高反映浪漫主義時期女性的日常生活經驗,讓女性所珍重的家庭價值、情感價值為崇高審美添加新維度。然而,當她使用“家庭化”(domesticated)這個詞匯時,不知道是否考慮到它的另外一個含義,即“馴化”。將崇高性引入家庭生活,是在馴化它,讓它變得可控。經過軟化的崇高是否會喪失它應有的力量?這和男性想要通過優美審美控制女性的力量,讓她們安居家庭空間的策略有什么不同?經由馴化調和過的崇高還是崇高嗎?抑或是它已經滑向了“優美”的范疇?
其實,這些問題可以簡化成一個問題: 男性崇高強調“力的崇高”,女性崇高是不是需要用力量的弱化來體現其與男性崇高的差異?女性批評家芭芭拉·克萊爾·弗里曼在《女性崇高: 女性小說中的性屬與過度》中給出了堅決的否定回答:“反對將崇高進行馴化。”(Freeman3)弗里曼認為康德式的崇高隱藏著怯懦的內核: 懼怕挑戰,所以強化主體建構,以壓制差異;畏懼崇高客體的力量,所以對他者實行征服和控制;畏懼越界,所以強調安全的距離。經典崇高主體對客體保持警惕,以防止引發狂喜、越界、入迷,而狂喜、越界、入迷其實也是深具崇高性的審美體驗。
女性崇高所珍視的正是這種被男性崇高論視為危險的崇高力量。它是偏離了標準的力量,是對男性崇高論的基本邏輯的顛覆,即反對邏各斯中心主義,反對二元對立思維模式,反對身份認同的僵化建構,主張與絕對的異質性的相遇。這種無法被語言與文化的象征秩序所收編和壓制的絕對的異質性,是無法被身份政治所錨定的存在,挑戰著父權制表征體系的極限。瑪麗·雪萊的《弗蘭肯斯坦》中的怪物、托尼·莫里森《寵兒》中的幽靈“寵兒”,他們身上就閃現著這種異質性。釋放異質性,拆除藩籬,讓生命力流動起來: 因此女性崇高追求邊界美學,關注“邊界的建構與破壞(這些邊界可能是美學性的、政治性的或者是心理性的)”;持有流變的身份觀,關心文學文本如何表達“身份的建構與解體”;承認表征的有限性,努力探索它的邊界,讓文本敞開,聽語言言說其不可言說之意(Freeman6),從而帶來闡釋的多重性和意義的漫溢。
在弗里曼看來,凱特·肖邦的《覺醒》就是這樣一部體現女性崇高性的文本。小說結尾,艾德娜·蓬特利爾夫人在大海中溺亡。這是一場事故,還是有意為之的自殺?如果是自殺,那么艾德娜是在海中游泳,感到脫力后,一剎那對生命的倦怠感涌上心頭,所以放棄了求生,還是早有此意,順勢而為?對于這些問題,文本只提供了一些相互矛盾的線索,而沒有清晰的解釋。在艾德娜溺亡后,再追溯她的生前,艾德娜在渴望著什么、在欲求著什么,這些問題的答案也只能靠文本的蛛絲馬跡去揣測。在她的身上,有一種異質性的含混,這含混源于婚姻、母親的身份、友情、身體的欲望、經濟獨立的愿望等眾多力量對她的拉扯。但是,她也有一種異質性的決然。那是一種破釜沉舟、不甘為父權制所鉗制的能動性,是一股不肯安于現狀、拒絕被馴化的力量。凱特·肖邦的女性崇高式的寫作,也很好地展現了這種含混與決絕交織的復雜性,開放的結尾更使文本的意義總在延宕,不肯終結。類似的作品還有伊迪斯·華頓的《歡樂之家》、簡·里斯的《早安,午夜》等。
總結這一時期女性崇高論的不同版本,我們可以看到它們的共性: 反對父權體制和男性主體觀,質疑二元對立思維的合法性,肯定女性經驗的意義,提倡更為多元的價值觀,將跨越邊界的流動性和開放性作為女性崇高論的力量源泉。這也是為什么批評家們在討論女性崇高時,避免過激論斷,不愿將男性排除在女性崇高之外的原因。安妮·K·梅勒認為在浪漫主義詩人中,約翰·濟慈的寫作就有女性浪漫主義的特征。芭芭拉·克萊爾·弗里曼指出她的著作之所以不談論男作家,不是因為女性崇高是男性的禁地,而是因為她要集中精力討論女性的社會困境(Freeman6)。生物學意義上的性別以及社會學意義上的性屬不是女性崇高的先決條件,女性崇高“不愿意將崇高直接等同于女性化”(5)。非此即彼的排他性策略會違反女性主義介入崇高論的初衷。因此,當她們提倡“女性”崇高時,“女性”一詞不定義性別本質,而只是一種斗爭工具和書寫策略,用以與崇高詩學傳統中的男性中心主義傾向相區別。
四
女性主義對崇高論的再審視始于20世紀80年末,在21世紀之前的十年時間里,“女性與崇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學詩學與藝術美學領域。隨著21世紀的到來,哲學家、倫理學家、文化批評學者也展現出了對這個議題的濃厚興趣,他們從政治美學、性別差異、倫理立場等多種角度,對已經被融合進當代社會文化肌理的崇高審美進行深入分析。
崇高論研究的女性主義視域拓展在出版于2001年的《論蜘蛛、賽博格和神圣存在: 女性與崇高》中已現端倪。在這部著作中,喬安娜·賽琳斯卡像梅勒、弗里曼等學者一樣關心女性主義崇高詩學。她將它推進一步,探索崇高風格的女性表達,進而發現法國后結構女性主義學者茱莉亞·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以及海倫娜·西蘇等倡導的“女性書寫”符合女性崇高書寫的特征,具有開放性、異質性、流變性。西蘇在《美杜莎的笑聲》中寫道:“我們如狂風驟雨;我們的自身若有部分脫離,也不會讓我們畏懼虛弱[……]。笑聲從我們的所有的口中溢出;我們的血流淌,我們延伸著自己,永無盡頭。”(Cixous349)這是典型的女性崇高文本,表達著女性的經驗與存在: 復數的“我們”中有一個個“我”,也包含著可脫離自身的“非我”的異質性,身體與精神、有限與無限同在。這里的言說方式也是流動的,意象化的文字帶來詩情和復義性。
然而,賽琳斯卡研究崇高詩學,不是為了用它指導文學批評實踐,而是因為她發現崇高詩學內嵌政治-倫理立場(Zylinska69),詩學同時也是倫理學以及政治學。賽琳斯卡指出,女性崇高是“新舊交織的話語”(38),“舊”是傳統之舊,它建立在對傳統崇高論進行批判的基礎之上;“新”是立場之新,借鑒了讓-弗朗索瓦·利奧塔(Jean-Fran?ois Lyotard)的后現代理論,也吸納了當代女性主義的思想。所以,女性崇高論將傳統崇高論的“有所畏懼”——即崇高感來自對死亡、虛無、自我的解體等恐怖的規避或征服——改造成了“無所畏懼”——即女性崇高“放棄了伯克式的安全距離以及康德式的安全位置”(34),以更開放的態度面對恐懼,接納愉悅與痛苦的混雜,不畏懼生與死的可通約性,認可自我的流動性。由此,一個新的政治-倫理向度在女性崇高的維度上敞開: 經典崇高論將陌生的他者的異質性視為危險與威脅。女性崇高詩學中的“我”,自身就有異質性,面對他者不會因恐懼而退卻,能夠承擔起伊曼努爾·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所倡導的“對于他者的絕對的倫理責任”(Hand56),這也是一種政治立場。
如果說賽琳斯卡的著作預示著崇高詩學研究介入倫理以及政治議題的野心,那么在“9·11事件”后,審美與政治深度地交織在一起,凸顯出女性主義崇高研究介入當下現實的必要性。2001年9月11日,塔利班恐怖主義極端分子駕飛機沖向美國資本主義文明標志物的雙子塔,造成數千人的死亡。“事件總是某種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發生的新東西,它的出現會破壞任何既有的穩定框架。”(齊澤克6)9·11就是這種意義上的“事件”,它是重大的歷史拐點,西方世界的自我認知與想象自此改變,西方世界突然感知到了恐怖和危險,陷入了妄想癥式的焦慮,每一張陌生的中東人面孔都暗示著一名潛在的恐怖分子的可能性。在此背景下,崇高美學強勢回歸。美國及其盟友隨后發動了兩場反恐戰爭: 阿富汗戰爭以及第二次海灣戰爭。戰爭動員、媒體宣傳、部隊部署、戰斗場面展示,都伴隨著對崇高美學的征調。因此,2006—2007年,兩部從女性主義視角反思崇高美學的理論著作相繼問世,它們都探討了恐怖暴力與崇高美學的深層關系問題。
讓我們先來看看《崇高、恐怖以及人類差異》一書。這是一本哲學著作,作者是著名女性主義哲學家克莉絲汀·巴特斯比。巴特斯比在序言中指出:“現代政治恐怖的表征無一例外以這樣或者是那樣的方式和崇高的概念相關聯。”(Battersby3)在“9·11事件”后,有音樂家宣稱他從飛機撞擊雙子塔的壯觀場面中獲得了創作交響樂章的靈感。他的言論招致了輿論的大力譴責。但是,“9·11事件”后,人們反復觀看電視臺播放的恐襲場景回放;阿富汗戰爭以及第二次海灣戰爭中的軍事行動常常能登上CNN等美國電視臺的頭條——這些暴力場景帶動出的審美快感,符合伯克與康德的崇高定義: 我們體會到危險與威脅的迫近,又隔著安全的距離,可以進行審美觀想。而最終將實現某種征服與超越。如果音樂家不應該對“9·11事件”進行審美解讀,觀看美軍作戰的電視觀眾的審美體驗是否也應該受到質疑?是否要首先問責媒體為何在煽動崇高的視覺欲望?是否需要反思為什么當今社會有這么多暴力場景可供觀看?此時,讓我們再回到崇高審美的討論中——崇高審美與暴力究竟是什么關系?
這是巴特斯比想要回答的問題。為了尋找答案,她決定回到18世紀崇高美學經典化的源頭進行考察。她發現崇高美學自啟蒙時代起就攜帶了暴力基因,它感應了法國大革命的恐怖,主張在混亂與恐怖之上建立超驗的秩序,必要時可以動用強力。它歌頌人類勇氣,而勇氣是彰顯男性氣概的重要品質,其激情源自“我們意識到自己有能力攻堅克難”,所以勇氣允許展示力量,允許為了抵抗恐怖而訴諸武力。在此前提下,康德這位“永久和評論”的支持者承認戰爭這架暴力機器可能引發審美感:“如果戰爭能夠按照秩序和對平民的權利的尊重而展開,是具有一定的崇高性的。”(康德,《實踐理性批判》433)按照這個邏輯來判斷,9·11的恐怖襲擊不符合崇高美學。但是,以消滅恐怖分子為名義的阿富汗戰爭和第二次海灣戰爭能進入審美領域。西方軍隊裝備精良,來到蒙昧的東方土地,如同天神般將憤怒降給螻蟻般的敵人,這是具有崇高性的。
問題在于,在這種崇高論中,被施以暴力壓制的生命是被客體化了的抽象生命,他們無面目,無個性,只能以一種可怖的異質性集體身份存在著。他們是西方人眼中長得都挺像的穆斯林人。崇高論的主客體分離切斷了道德共情的紐帶,也阻斷了倫理責任的承擔,使審美愉悅沒有了負擔。它推崇力量,啟動征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合法化了暴力和沖突。為此,巴特斯比認為崇高論的傳統中埋藏著今日世界沖突的影子:“不寬容、全球爭議以及價值沖突,當今世界的這些紛爭都有審美的參與。”(Battersby206)崇高審美不是社會暴力泛濫的根源,但是,它在渲染著恐怖,對差異化的生命進行著壓制,激發出暴力,甚至會造成它的升級。
在劍橋大學出版的《女性解放與崇高: 女性主義、后現代主義與環境》一書中,邦尼·曼同樣在討論后“9·11事件”的政治美學,她關心的是國家和媒體如何共同征用了崇高審美。“9·11事件”后,美國“用暴力和權力的奇觀化”來包裝主權國家形象,以期震懾敵人,讓他們感到敬畏,“重新向我們俯首稱臣”(Mann, Women’s Liberation176)。媒體則迷戀力量的展示和視覺的奇觀化,渲染毀滅與恐怖的崇高。觀眾的感官被一幕幕崇高場面震撼到麻木,無暇思考,無暇質疑。
為此,邦尼·曼認為應該拋棄男性崇高模式,從女性崇高論中尋找新的政治美學方案。弗里曼在《女性崇高》中將女性崇高比喻為交界地帶,自我和他者在邊界相遇,接納雜糅,有脆弱的易感性。這種易感的脆弱和朱迪斯·巴特勒的脆弱生命觀有吻合之處。巴特勒在《脆弱不安的生命: 哀悼與暴力的力量》中指出,人們生活在人世間,相互依賴,同時也容易受到彼此的傷害:“我們都如此脆弱,易受他人傷害的弱點是我們有朽之軀的組成部分[……]。認識這一弱點有助于人們以此為基礎探索非暴力政治解決方案,而沉湎于制度化的統治妄想及否認這一弱點則會招致兵戎相見。”(Butler28-29)所以邦尼·曼將承認脆弱性的女性崇高視為男性暴力崇高的解毒劑。在女性崇高中,勇氣不是戰場上的沖鋒陷陣,而是承認肉身易朽,愛惜生命珍貴,堅韌地承受精神以及肉體的痛苦,不逃避絕對的倫理責任。“崇高要求我們面對那些我們嚴重傷害過的他者(以及那些可能傷害過我們的他者),承認我們休戚與共,至少我們同在一個地球共居一方空間。”(Women
’s
Liberation
177)正因為缺乏反思,這種生命倫理一直無法建立,相反,崇高論的男性模式卻一直在被強化。所以,2014年,邦尼·曼專門撰寫了《主權男性氣概》這部著作,來解釋作為國家主權集體形象而存在的“自我”是如何與這種崇高美學相重疊的“主權男性氣概”一起為美國的國家形象建構服務的(174)。這種建構的本意是用優勢性的實力和英勇無畏的氣勢對抗恐怖,驅逐恐懼,但造成的后果是崇高審美墮落為無底線的暴力宣泄。自我與他者、主體與客體,如何理解這兩組關系,是區分男性崇高與女性崇高的重要標志之一。在男性崇高審美中,自我/他者、主體/客體,它們形成二元對立,分列清晰的界墻兩端,這座界墻依靠強力維持,其力量體現在秩序的建立中。在女性崇高審美中,自我-他者、主體-客體,它們是共生關系,身份可以流動轉換,其力量體現在包容、越界與寬恕中。2017年,厄林·斯皮思在《性別與主體間性: 福克納、福斯特、勞倫斯以及沃爾芙的崇高》中重回文學領域討論崇高詩學,對這兩組關系的可能模式進行了新的探索:“當主體不再將他者視為客體,不再借助他者來進行自我認定、自我否定或者自我懷疑,會發生什么?”(Speese11-12)通過對威廉·福克納、E.M.福斯特、D.H.勞倫斯以及弗吉尼亞·沃爾芙的作品進行分析,她發現隨著主客體模式的放棄,“一種互惠的、共情的、主體間性的崇高就會在兩個主體的互動之中涌現”(4)。在《到燈塔去》中,麗莉·布里斯庫想為拉姆齊夫人畫像,卻不愿意也沒辦法用藝術家客體化藝術品的方式來捕捉她的復雜性。十年后,拉姆齊夫人去世,麗莉感悟到夫人的關懷依然感召著她,通過設身處地的共情,理解了夫人的主體性,隨之頓悟,畫出了心目中的理想畫作,“她在極度疲倦中放下畫筆,心想,是的,我已經有自己的視野”(Woolf211)。當自我與他者形成了“主體-主體”的關系,客體化的策略會失效,唯有關懷倫理能夠給主體以力量,使其超越自身的封閉經驗,抵達崇高。
自此,讓我們回到開篇,重新回顧哈羅德·布魯姆在《影響的剖析》《神魔知道》等作品中提倡的崇高論。顯然,布魯姆所繼承的崇高美學傳統是具有局限性的。空泛地談“激情”“超越”與“人性”,卻不愿意討論超越的標準中隱藏的性別限制性條款,這是在制造一種男性話語權的烏托邦。而且,這種崇高忽略了歷史的陰影和當下的復雜性,阻斷了抵達崇高的其他路徑,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超越。這也是為什么近三十年來,女性主義在哲學、文化、政治、藝術、文學諸領域對崇高美學進行全方位再審視的原因。如何讓崇高美學標準能夠與女性經驗和女性傳統相契合?如何站在女性立場,為崇高美學提供新的思考視角?如何秉持女性主義主體觀,行踐對他者的崇高倫理責任?……女性主義批評家們正在進行著積極的探索。一種跨越邊界、尊重情感、擁抱異質性、提倡主體間性的新的崇高美學主張正在形成中。這是女性主義為崇高美學的理論場域帶來的新動能。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Battersby, Christine.The
Sublime
,Terror
and
Human
Difference
. New York: Routledge, 2007.Bloom, Harold.The
Anatomy
of
Influence
:Literature
as
a
Way
of
Life
.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 -.The
Daemon
Knows
:Literary
Greatness
and
the
American
Sublime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 -.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
. New York: Harcourt, 1994.Bromwich, David. “Wollstonecraft as a Critic of Burke.”Political
Theory
23.4(1995): 617-634.埃德蒙·伯克: 《關于我們崇高與美觀念之根源的哲學探討》,郭飛譯。鄭州: 大象出版社,2010年。
[Burke, Edmund.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
Trans. Guo Fei. Zhengzhou: Elephant Press, 2010.]- -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 Ed. Frank M. Turn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Butler, Judith.Precarious
Life
:The
Power
of
Mourning
and
Violence
. London: Verso, 2004.Cixous, Hélène. “The Laugh of the Medusa.”Feminisms
. Eds. Robyn Warhol and Diane Price Herndl.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7.347-362.Freeman, Barbara Claire.The
Feminine
Sublime
:Gender
and
Excess
in
Women
’s
Fiction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Hand, Seán.Emmanuel
Levinas
. New York: Routledge, 2009.Hanson, Karen. “Feminist Aesthetics.”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Aesthetics
. Eds. Berys Gaut and Dominic McIver Lop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3.499-508.Kant, Immanuel.Observations
on
the
Feeling
of
the
Beautiful
and
Sublime
and
Other
Writings
. Eds. Patrick Frierson and Paul Guy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伊曼紐爾·康德: 《判斷力批判》,鄧曉芒譯。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4年。
[- - -.Critique
of
Judgement
. Trans. Deng Xiaomang.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4.]——: 《實踐理性批判》,鄧曉芒譯。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4年。
[- -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 Trans. Deng Xiaomang.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4.]Klinger, Cornelia. “The Concepts of the Sublime and the Beautiful in Kant and Lyotard.”Feminist
Interpretations
of
Immanuel
Kant
. Ed. Robin May Schott. University Park, P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7.191-212.朗吉努斯:“論崇高”,《繆靈珠美學譯文集》第1卷,章安祺編。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77—132。
[Longinus. “On the Sublime.”Translations
on
Aesthetics
by
Miu
Lingzhu.
Vol.1. Ed. Zhang Anqi.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1998.77-132.]Mallinick, Daniella. “Sublime Heroism andThe
Wrongs
of
Woman
: Passion, Reason, Agency.”European
Romantic
Review
18.1(2007): 1-27.Mann, Bonnie.Sovereign
Masculinity
:Gender
Lessons
from
the
War
on
Terror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 -.Women
’s
Liberation
and
the
Sublime
:Feminism
,Postmodernism
,Environment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Mellor, Anne K.Romanticism
and
Gender
. New York: Routledge, 1993.彭峰: 《西方美學與藝術》。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
[Peng, Feng.Western
Aesthetics
and
Art
.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Poovey, Mary. “Aesthetics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Place of Gender in the Social Constitution of Knowledge.”Aesthetics
and
Ideology
. Ed. George Levine.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4.79-105.Runge, Laura L.Gender
and
Language
in
British
Literary
Criticism
,1660-1790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Skolnik, Christine M. “Wollstonecraft’s Dislocation of the Masculine Sublime: A Vindication.”Rhetorica
:A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Rhetoric
21.4(2003): 205-223.Speese, Erin.Gender
and
the
Intersubjective
Sublime
in
Faulkner
,Forster
,Lawrence
,and
Woolf
. New York: Routledge, 2017.Wollstonecraft, Mary.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n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An
Historical
and
Moral
View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 Ed. Janet Tod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Woolf, Virginia.To
the
Lighthouse
. Ed. Mark Hussey. New York: Harvest Books, 2005.Yaeger, Patricia. “Toward a Female Sublime.”Gender
and
Theory
:Dialogues
on
Feminist
Criticism
. Ed. Linda S. Kauffma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9.191-212.斯拉沃熱·齊澤克: 《事件》,王師譯。上海: 上海文藝出版社,2016年。
[?i?ek, Slavoj.Event
. Trans. Wang Shi.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2016.]Zylinska, Joanna.On
Spiders
,Cyborgs
,and
Being
Scared
:The
Feminine
and
the
Sublime
.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