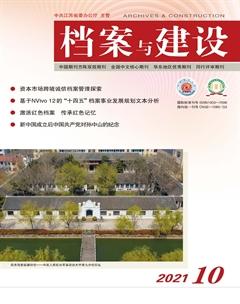武昌起義后蘇北地區的光復
劉小寧
1911年武昌起義后,蘇南地區紛紛響應,迅速光復,革命軍兵鋒直至蘇北地區。
張氏兄弟策動?通州和平光復
江蘇的通州,于1911年11月8日(清宣統三年九月十八日)宣布光復。1912年,江蘇省臨時議會議決廢府州廳,省以下設縣,通州改稱南通。
清末,通州是一個偏處江北海隅的中等城市,相當于府一級的直隸州,下轄如皋、泰興兩縣。其時,實業家張謇已在通州創辦了新型工廠,同時又興辦了學校。
通州扼長江門戶,唐、宋以來一向是軍事重地,清初此地設置狼山鎮總兵,總統綠營水陸兵勇,與隔江南岸設置的福山鎮總兵分別扼守江南江北要地。鴉片戰爭以后,這支軍隊的重要性逐漸下降,已是名存實亡。到了辛亥革命前,軍隊編制的名冊上還記載著三五百人的名額,實際留駐城防的陸軍士兵只剩下提著馬提尼或林明敦舊槍,改練所謂新式兵操的百把老兵弱卒。加上軍政廢弛已久,武官們總在上行下效地靠吃空額、索陋規過日子。
通州的文官以知州為首。到了宣統年間,知州在統治集團中的分量已大大降低,他們經常面對的不再是供驅使的督董、廂董、保甲董事,而是鄉紳張謇在試辦自治名義下產生的地方自治公所。早先憑仗科名銜職或門第而作為大小紳董的一類,除進士出身、做過戶部主事的孫寶書還擁有部分勢力外,這時差不多已被代替。張謇、張詧兩兄弟為首的新興實業家、知識分子以及部分城鄉地主結合成的混合集團,形成了“紳重官輕”的特殊局面。
武昌起義消息很快從上海傳到了通州。其時張謇趕回通州,與其兄張詧商量對策,二人都認為通州當務之急是防備大局未亂地方先亂。幾天后,通州商會在張謇的主持下,決定成立協防團,全部使用快槍一類的新式武器,淘汰了舊式槍支。后來,又成立了中央隊,屬于駐在州城的協防團核心組織。
10月30日,張謇到了上海。這時,湘、晉、陜等地先后獨立,各處兵變消息日緊。他在上海滯留的兩三天,正是各派革命黨人在上海醞釀上海、蘇州光復之時。同盟會、光復會都把張謇作為重點的爭取對象,陳其美、李燮和兩方均把他作為東南最有聲望的社會名流來看待,并已經通過種種渠道與張謇取得了聯系。
11月2日,張謇回到通州。接著便是上海、蘇州先后獨立,連他的摯友、浙江著名的立憲黨人湯壽潛也回到了杭州,成為獨立后的浙江都督。這一來,通州獨立的問題馬上就顯現出來。
通州地方一直沒有新軍駐扎過,只有狼山鎮綠營兵,總兵叫張士翰,已六七十歲了,老態龍鐘,根本不可能發動或響應革命。此人手下有一二百來人,多數是些營混子,加上幾百支破槍,完全不頂事。而通州地方的士紳不是“舊”的就是“半新不舊”的。舊的大多從八股眼兒里鉆出來,生怕革命剪掉了辮子;“半新不舊”的就是讀過些《新民叢報》之類的書刊,思想屬于立憲派或準立憲派。文官如州官之類,既不掌兵,又無群眾,更想不到革命。聽到武昌起義而有所觸動的,只是少數青年知識分子。通州雖然有過光復會的外圍組織,但成員大多是青年學生,人少、活動范圍狹窄,只做了一些宣傳工作,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通州地方對時局趨向的決定權,自然而然地落到了張氏兄弟身上。正在此時,上海出版的《時報》制造出一條新聞,竟登載了狼山鎮已經懸掛白旗反正的報道。這其實是輿論在督促通州盡快行動。在吳淞接受招降的清軍水師舊官又派來秘密使者,對狼山鎮官兵進行活動。這時,張氏兄弟再三權衡得失,決定響應光復。
原福山鎮駐吳淞水師參將許宏恩,數年前做過狼山鎮右營游擊,并與狼山鎮的一些官兵有關系,如今受上海光復會派遣到通州,秘密向總兵張士翰及其部下游說。許宏恩一至通州,便通過舊誼與張謇兄弟取得了聯系,并和孫寶書一起商量,進行部署。許宏恩前往大生紗廠向張謇匯報經過,張謇表示全部同意,但表達了對南京何時攻克極為關注。
1911年11月8日,許宏恩率“擎電”號兵艦到達通州。全城機關、學校于前一天已得到通知,連夜作了歡迎的準備,對外仍保守秘密。通海五屬公立中學在當天下午課畢后,就提前開晚飯,鳴鐘集合,列隊出發,前往蘆涇港輪埠,而市民則被告知革命軍將于次日5時后登陸。歡迎隊伍由孫寶書率領,整個隊伍大約四五百人,包括地方官學代表,商業、工業兩體操會成員,師范、中學學生。在左臂上皆戴有白布臂章一道,這是通行的革命標志。兩體操會成員和學生隊伍大多是肩荷步槍,身穿制服。自動參加的民眾也不少。
“擎電”號兵艦屬于江防水師的淺水小艦,到達蘆涇港碼頭時已是黃昏時分,艦上共40余人。
這一晚,家家懸掛起紅燈籠。街邊商店有的掛起當天趕制的旗幟,有的臨時以方幅白布系在竿頭代替,也有的在白旗上寫了“光復大漢”等振奮人心的語句。晚8時左右,在沿途百姓的簇擁下,革命軍開進城中。
隊伍最后到達東大街的舊總兵衙門,在西花廳小休片刻,便集合到大堂舉行通州光復的儀式。革命黨人作了闡明光復大義的演說,說到決心推翻清朝統治時,激動地舉起指揮刀用力砍掉公案的一角,接著推翻了公案。
狼山鎮總兵張士翰早已從衙門遷出,印信關防托由部下代管,軍械庫也封了。因此光復沒有遇到任何麻煩。
光復儀式后,安民布告發布,宣布通州已經光復,軍政分府已經成立,安定民心。大家覺得新鮮的,是“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的第一次出現。
同一天,位于柳家巷的總商會召開各界人士參加的推舉大會,推定張詧為總司令長,孫寶書為民政長,許宏恩為軍政長。
揚州二次光復?乘勢光復鹽城
清末的揚州府轄二州六縣,即高郵州、泰州、甘泉縣、江都縣、儀征縣(宣統二年改稱揚子縣)、興化縣、寶應縣、東臺縣。其中江都縣署、甘泉縣署與揚州府署同設于揚州城內。
1911年11月7日鎮江宣告光復,成立軍政府。就在當天,一江之隔的揚州發生了孫天生光復揚州的起義。孫天生是揚州的失業游民,曾亡命湖北、上海等地。武昌起義后,孫天生回到揚州,秘密策動了定字營清軍起義。11月7日晚,他在揚州城南靜慧寺的定字營駐地積極鼓動士兵起義,并揚起了“光復大漢”“還我河山”的旗幟,之后就沖進了揚州城。
揚州的清廷官員和紳商頓時驚慌失措。知府聞風躲入天寧寺,把官印扔進了瘦西湖,后逃往高郵。鹽運使慌忙越墻而走。江都和甘泉知縣未逃走,只得跟隨孫天生鞍前馬后地伺候。
孫天生光復揚州后,立即做了兩件事:第一,下令打開江都、甘泉二縣監獄,放出所有犯人;第二,打開鹽運司署的銀庫,將銀兩分給起義士兵和貧苦百姓。第二天,孫天生還以揚州軍政府都督的名義正式宣布揚州光復,并通令百姓安居樂業,三年不完糧,捐糧全免。同時,嚴禁奸商哄抬物價,限定大米每石不得超過3元,豬肉每斤不得超過200文。為穩定秩序,孫天生還傳見紳商代表,要他們聽從吩咐。但部分紳商陽奉陰違,當面點頭稱是,背后卻通宵密議。他們一方面應付孫天生,避其鋒芒;另一方面派人到江南,邀請徐寶山等人迅速來揚,鎮壓孫天生。
徐寶山,字懷禮,喚虎兒,江蘇丹徒南門人,早年入了幫會,渾名“徐老虎”。后接受了清政府招安,當上了緝私營管帶。辛亥革命前夕,兩江總督張人駿曾撥款10萬元擴編巡防營,以徐寶山為統領。這支隊伍成為鎮揚一帶一支重要的武裝力量。
辛亥革命爆發后,革命黨人林述慶、李竟成在鎮江醞釀光復。李竟成利用和徐寶山的親戚關系,爭取徐寶山響應革命。徐寶山看到形勢急轉直下,遂一方面通過在求實書院的親友在上海與光復會接洽,商討起義事;另一方面,又與李竟成周旋與聯絡。他最終答應了李竟成參加起義,但提出一個條件,即在局勢穩定后不去做官,而仍然從事鹺務,保證鹽稅收入。李竟成答應了他的要求,并在雙方訂立的契約中言明“將來革命成功,許以特別揚鹺利益。”
鎮江光復后,揚州部分紳商接連派人請求派軍隊去揚州。李竟成、徐寶山很快就率部過江,直奔揚州。徐寶山的部隊在揚州南門鈔關登岸,11月9日進入揚州城。揚州紳商人士在教場口擺筵接風。正在這時,孫天生率一小隊起義軍突然出現在教場口,當即向徐寶山據理力爭,但徐寶山不為所動,并立即下令向孫天生開槍,因寡不敵眾,孫天生趁亂逃脫,徐寶山下令關閉城門四處搜查。第二天,孫天生在多寶巷一家妓院里被捕。徐寶山將孫天生帶到泰州,欲利用孫天生收繳泰州一帶定字營散兵的武器,孫天生不從而被殺。
11月10日,徐寶山宣布光復揚州,并立即成立揚州軍政分府,自己擔任了軍政長,由李石泉任民政長。
徐寶山二次光復揚州后,繼續前往蘇北里下河地區。徐寶山率部至泰州,11月16日宣布泰州光復,同時招降了部分嘩變清軍。接著又抵達興化,11月19日宣布興化光復。11月20日,徐寶山率部乘船到達鹽城,宣布鹽城、東臺、阜寧等地光復,并幫助維持地方治安。
淮安光復與周實、阮式之死
淮安(舊稱山陽)位于蘇北平原腹地。清代淮安府轄二州九縣。津浦鐵路通車前,淮安是南北水陸交通樞紐,號稱“七省之咽喉,京師之門戶”。經濟上物產豐富,古鎮河下是淮鹽集散地,清政府在城中心設有“漕運總督署”。清后期,海道開通,鐵路鋪成,淮安地位下降,但地理位置仍然十分重要。
淮安原有舊城、夾城、新城三道城池,城內房屋鱗次櫛比,街道縱橫,店鋪林立,商業十分發達。由于得天獨厚的優越條件,諸多外籍告老退休的大官僚也來淮定居,致使淮安保守勢力頗為強大。20世紀初,清王朝殘酷的壓迫剝削激起了淮安人民強烈的不滿和反抗,鄉間破產的農民組織“大刀會”“小刀會”,以反清為宗旨進行半公開的活動。
辛亥年間,距淮安僅30里的清江浦駐有新軍第十三混成協,而淮安城內卻兵力空虛。武昌起義后,兵備道尹奭良畏罪逃走。受革命影響的第十三協官兵曾舉行起義,攻占清河縣城,但由于組織領導無方,軍紀松弛,起義后散兵游勇四處流竄,搶劫商號富戶,市民備受其害。
淮安局勢極度混亂下,周實受同盟會、南社派遣回到淮安。周實,字實丹,生于淮安車橋鎮一個窮書生家庭,18歲入縣學為秀才,后來就讀于南京寧屬師范學堂、兩江師范學堂。1909年,反清革命文化團體南社成立,周實欣然參加,是南社最早的成員之一,與柳亞子等人有密切的交往,被稱為“社中眉目”。
阮式,字夢桃,出身于淮安城內世代書香的大家族,16歲入泮,后讀于江北高等學堂,又與周實共讀于寧屬師范學堂。先后任宣城模范小學、山陽高等小學教習,上海《女報》編輯,《克復學報》撰述,曾應周實之約共創“淮南社”。
周實、阮式少年時代讀書勤奮,又較早接觸了西方文化,產生了反清反帝思想,立下了救國救民的志向。
武昌起義消息傳來,周實、阮式欣喜若狂,躍躍欲試。上海、蘇州等地相繼光復后,只有南京仍為清軍所盤踞,清軍妄圖憑借高大的城垣、林立的炮臺負隅頑抗。在南京兩江師范讀書的周實會同城中各校學生700余人,約定于11月7日舉事。后聽取柳亞子的建議,決意歸淮,相機行事。
周實回淮安后,立即與阮式商討光復之策。于是召集旅寧旅滬回淮學生及本城中學生八九十人開會議事,成立“學生隊”,周、阮分任正副隊長。當時晚清縣政權已癱瘓,城內無兵可用,大戶豪門惶惶不可終日。民團不足以防御散兵游勇和土匪的擄掠,鄉紳亦希望有人出頭來負守城之責,乃說服民團供給學生槍支、子彈。
學生隊員獲得武器后,到署前放了一排槍,又將清朝黃龍旗扯毀,插上了白旗。周、阮率領隊員日夜奔走于城上城下,分兵在城門口巡查奸宄。一時間,城內秩序井然。周、阮又下令商店照常營業,并派人積極準備組織淮安軍政分府。紳董見學生們奮發保衛鄉里,紀律勝于團勇,就將學生隊改為“巡邏部”,周、阮分任正、副部長,守城之責也由巡邏部擔當。學生武裝荷槍持械,來回巡邏,日夜不輟。周、阮還指派南京陸軍中、小學學生二人分別教操和訓練。巡邏部完全控制了全城局勢,清河縣的第十三協亂兵近在咫尺,淮安卻安然無恙。
1911年11月12日,清河光復,陸軍參議蔣雁行被推為江北都督。同日,蔣傳檄淮安(即山陽)反正,并邀淮安官紳赴都督署議事,清朝山陽縣令拒不前往,當地士紳當即推舉周實等五人赴會。
周實赴清河回淮安后,于11月14日在舊漕署召開大會,宣布淮安光復。阮式也即席發言。
淮安光復后,反動勢力很快麇集在一起,擬定了謀殺周實、阮式的計劃。11月17日,周實應邀赴學宮議事。此時學宮內早已布滿伏兵,周實不知有詐,剛入學宮,就身中兩彈倒地,又被補了五槍,當即殞命。隨后團勇又包圍阮宅,以請阮式議事為名,將阮誘至府學后捆綁。阮式痛罵:“要殺就殺,快刀立斷,勿延!”地痞無賴遂將阮式刳腹剖胸,殘忍殺害。被害時,周實年二十七,阮式年僅二十三。
這是辛亥革命中又一起繼徐錫麟、秋瑾之后,震動全國的慘案。南社社員不僅用筆墨宣揚革命,而且前赴后繼為革命獻出了頭顱和熱血,周實是社中第一人。柳亞子驚悉噩耗,悲憤欲絕地寫下《哭實丹烈士》,詩中有“淮南秋老桂先焚”“一語無端死伯仁”句,表達了對烈士的哀悼。
1912年2月11日,《克復學報》社、南社、淮安學團在上海西門外江蘇教育總會聯合召開了“山陽殉義周實丹、阮夢桃兩烈士追悼會”。臨時大總統孫中山親送挽聯:喋血于孔子廟中,吾道將衰,周公不夢;陰靈繞淮安城上,窮途痛哭,阮籍奚歸。
宿遷光復的一波三折
宿遷位于江蘇省北部,徐州、淮陰(今淮安,曾稱清江浦)、海州(今連云港)三大重鎮的中心地區。地勢平坦,物產豐富,交通便利,有京杭大運河縱貫其中,津浦鐵路通車后仍為東南地區運輸的通衢,也是歷來兵家運兵的必經之地。
清政府為維持其搖搖欲墜的統治,對于反清的會黨和革命黨人殘酷鎮壓。當時宿遷有重兵把守:城區駐守備營;清軍悍將張勛部署的江防營駐窯灣、皂河;馬隊五營、步隊一營駐農村集市,洋河、新安鎮各由一名游擊鎮守。這些清軍的首領大部頑固保守,但士兵和下級軍官大多數傾向革命。
1911年11月6日,新軍第十三協在清江浦起義,宿遷西鄉的會黨積極響應,揭竿而起,聚眾數百人,設指揮機關于褚廟。會黨沒有具體的綱領、組織,也無新式武器裝備,聚眾起義后只是忙著開倉放糧,接濟百姓,對抗擊強大的敵人卻無足夠準備。宿遷縣知事仰仗清軍勢力,蓄意與革命為敵,在接某鄉董密報后,遂下令“格殺勿論”,調集大批清軍、鄉勇,將起義骨干四五十人圍困于褚廟。起義人員寡不敵眾,有的突圍逃離,有的被捕遇害,其他人紛紛逃散,起義遂告失敗。
起義失敗后,縣北鄉的興中會會員等革命黨人收容十三協起義失敗后的潰散士兵和武器,并招募青壯年百余人,組成義軍,按同盟會宗旨宣傳革命,然后樹起白旗,宣布光復。
與此同時,睢寧縣興中會會員也將收容的十三協人馬及宿睢邊界青年三四百人組成義軍,并通知宿遷義軍來宿會師,共同開赴清江。11月13日,睢寧義軍來宿,宿遷地區清軍嚴密布防,起義軍與清軍在縣城西南古城交戰。清軍馬隊五營統領戰敗回城,隨后令哨官攜犒勞費500元與起義軍議和,起義軍予以堅決拒絕,并當場將哨官擊斃。起義軍經洋河前往清江,沿途受到商紳軍學各界的熱情迎送,聲威大振。同時,興中會會員積極在清軍守備營中進行策反,宣傳民軍即將北伐。守備營軍心頓時大亂,開始潰散。
宿遷縣知事為了保存實力,待機而動,對起義軍不采取敵對行動,而是提出召開應變會議,邀請起義軍領導人及新學人士參加會議。起義軍提出只要換掉清朝龍旗,懸掛漢旗,起義軍可以不攻城,也不請民軍北伐。新學人士以時機緊迫,也要求知事擁護共和,并以公推民政長等為條件。知事才同意在馬陵山頂豎起一丈見方的大白旗,張貼布告,宣布光復。新學人士在皂河也樹起白旗響應。這樣,宿遷縣宣告光復了。
正在此時,傳來袁世凱的北洋軍進攻漢陽,炮擊武昌的消息。由山東南下的清軍前鋒也已抵達皂河。知事等人又迫不及待地以民政長名義對興中會會員等起義首領以“匪”名進行捕殺。新學人士處境危險,紛紛遠逃外地。宿遷光復就此夭折。
12月2日江浙聯軍攻克南京,民軍朱占元部進軍宿遷,首戰皂河,再戰高作,擊潰清軍張勛的江防營。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宣布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2日,宿遷各商店、學校張燈結彩,歡欣鼓舞,各界人士召開大會,慶祝共和。
民眾群起反抗?海州光復
清朝末年,海州(今連云港)轄有54鎮,北起贛榆,南臨漣水,西至馬陵山,東瀕大海。海州一帶發生嚴重水災,饑民遍地,官府和地主豪紳照舊催交租稅,以致民眾不斷地進行反抗。海州饑民萬余人包圍了海豐面粉公司,拆毀了院墻,燒壞公司前后門和麻袋船,奪了萬全酒坊豆餅船只。
1908年10月16日,兩江總督端方、江蘇巡撫陳夔龍、陸軍部右侍郎兼江北提督蔭昌,在致軍機處電報中稱:“海州匪徒滋擾,當經會派參謀鄢玉春、緝私營王曜等率帶營隊并水師兵輪分赴剿辦。”海州士紳也紛紛籌辦民團,準備配合清軍鎮壓民眾反抗。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后,海州所屬新安鎮農民聚集3000多人,出面維持地方治安,向地主富戶借款借糧;海州所屬灌云縣大伊山鎮民眾聚集起義;甚至連秀才等也舉起了義旗,以陳勝、吳廣自居,宣布跟清王朝決裂。
民眾的反抗斗爭,使清朝統治者膽戰心驚,清廷資政院議員在致袁世凱的稟報中驚呼:“時海州土匪蜂起,千百為群,警報頻來,乞援急足。”
海州州官迫于形勢,在海州城內關帝廟召集地方士紳和教育界人士開會,當場宣讀了兩份來電:一份是江北都督蔣雁行的電報,通知江北已經獨立,他已就任都督;一份是清朝山東巡撫孫寶琦的電報,表示清王朝大勢已去。州官宣讀了這兩份電報后說:“海州南面是江北都督蔣雁行的駐地,現在他已宣布獨立了;北面是和海州接壤的山東,情況也有了變化。海州究竟何去何從?應該早做決斷,否則就要陷入孤立。”經過激烈爭論,最后,到會的海州士紳激于“兄弟也是漢人”的民族自尊,宣布海州獨立,脫離清政府,成立海州自治會,推擁州官出面維持地方治安。會后,州官即跟地方綠營子弟兵聯絡,同時招募新兵加強城防和自衛。
1911年11月22日下午4時,駐扎在海州城南白虎山下碧霞宮內的海州鹽防營的士兵接受了革命的宣傳,毅然舉起了向清王朝宣戰的大旗,舉行了起義。十多名士兵武裝入城,鳴槍沖進海州衙門,砸開牢房,戴著鐐銬的囚犯們也加入起義。州官的護兵也紛紛響應,放火焚燒了州官住宅,州官嚇得攜帶家屬倉皇出逃。一時間街市秩序大亂,市民紛傳“革命軍來了”。
11月23日,已經與海州起義軍取得聯系的江北新軍第十三協派何鋒鈺率領一營人馬開進海州,海州各界人士紛紛到東門外列隊歡迎。入城后,新軍就駐扎在海州的石室書院。11月24日,海州光復,軍政府成立,何鋒鈺擔任了海州民政長。
海州光復后,老人和青年們紛紛剪去了長辮子,戴起了招檐帽,社會風氣為之一變。擁護新政的地方士紳組織了“籌防局”,目的在于維持地方治安,興辦福利事業,保障士紳的利益。這是新政權的參謀咨詢機構。籌防局總辦用以工代賑的辦法,興辦了龍尾河、善后河、車軸河等水利工程以及拓寬板浦的外圍河道。
北伐軍壓境?徐州光復
徐州位于蘇、魯、豫、皖四省通衢的核心位置,南北戰爭必以徐州的得失為勝負關鍵。南方稱之為“北門鎖鑰”,北方號之為“南國重鎮”,實為兵家必爭之地。武昌起義四個月后,北伐軍于1912年2月11日光復徐州,控制了南北東西的咽喉重地。清政府鑒于大勢已去,被迫宣告清帝退位。
北洋陸軍第十三協(駐防在徐州以南的清江浦)有兩個步兵標,輔以炮、騎、工、輜各個兵種。該協新軍受到新的教育,具有民族觀念。辛亥武昌起義后,受革命的影響,官兵們都躍躍欲試,以推翻清朝為目的。但因無人領導起義,在清江浦光復后,全協發生了嘩變。
徐州人徐占鳳起先擔任該協協統(旅長),后被清廷撤職,回家閑居。十三協官兵多為徐州人,對此極為不滿。在部隊嘩變后,大部官兵全副武裝來到徐州,投奔前協統徐占鳳。徐州軍事當局得知變兵整隊北上后,頓時驚慌失措,為了維持局面,立即慫恿各地各界共推徐占鳳為該軍司令,出面收容改編,以平息風波。十三協部隊到徐后,即被改編為“徐防新軍”。
徐州地方官紳以形勢緊張為由,經過多次會議,宣布成立軍政府,公推徐占鳳為軍政長。但在張勛抗拒北伐,兵敗退入徐州后,該軍政府便無形中消失了。
張勛所部清軍以革命軍日漸迫近,知大勢已去,在進駐徐州后便大肆劫掠,徐州四關和近郊、壩子街等處被搶劫一空。尤其南關的上街(即彭城路)、馬市街、笆子巷(道平路)、下街(三民街)等商業精華地區,于洗劫之后又付之一炬,商民損失不可計數。而其官長也習以為常,從不加以制止處罰。徐州人民經過幾次浩劫,對張勛恨之入骨。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南北議和在上海久拖不決,于是孫中山決定北伐。中路為粵軍,沿津浦線北上;右路為滬軍、鎮軍,經揚州北進;左路為淮泗討虜軍,自壽州經正陽關、濉溪、蕭縣向北推進。三路均以徐州為目標,計劃在徐州會師北上。
1912年2月11日,北伐軍前鋒進抵三堡車站(距徐州15千米),地方各界前往歡迎。張勛聞之即北竄山東兗州。徐州即宣告光復,各界共推韓志正為民政長。
北伐軍入城后,立即北上跟蹤追殲張勛軍。次日至韓莊(在蘇魯交界,距徐州50千米)車站,清帝退位的消息傳來,南北統一,臨時政府的北伐也就此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