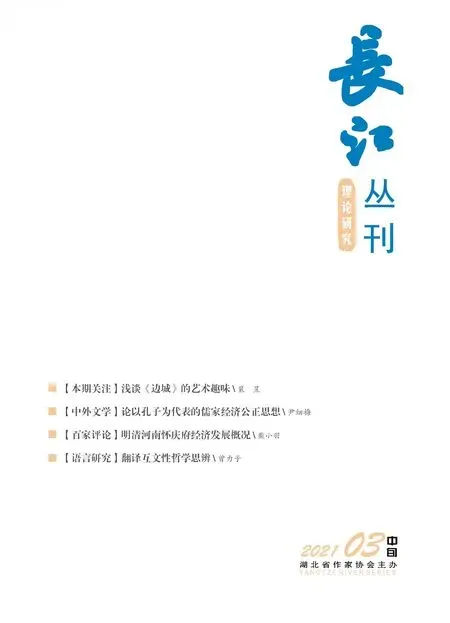死亡哲學中生命的價值
■張雨墨/哈爾濱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從古到今,死亡都是哲學家們討論的話題之一。死亡這個概念本身的未知性和迷惑性也導致了人們對他的恐懼和好奇。西方對死亡哲學的研究歷史悠久。哲學家們對于死亡的研究從古希臘開始。伊壁鳩魯認為“最可怕的惡是死,但死卻與我們毫無關系,因為我們活著的時候,死亡還不存在;當死亡來到的時候,我們又已經不存在了。”中世紀封建社會的死亡哲學的基本邏輯程式是“若不能死,就不能生”。近代隨著文藝復興和科學實驗的出現哲學家們開始懷疑“勿忘死”的思想,并對中世紀時的死亡觀念進行了批判。經歷了近代的過度,現代的死亡哲學理論則更加理性和系統化。哲學家們對死亡的討論更加純粹,排除了外界因素的影響。研究方向轉向死亡的本質、死亡價值、死亡意義、人類對待死亡的態度等角度。
一、死亡的概念
死亡與生命是一個相對的觀念,在研究死亡的本質時,首先要明確生的概念。眾所周知,生的概念就是“活著”,即一個生命體能夠進行各種生命活動,身體一直保持活性的一種狀態。但是我們也會說逝者永遠活在我們心中,對于英雄我們會說永垂不朽。這也意味著我們對生的觀念不僅限于生理上能夠進行生命活動,也包括了精神方面的存續。在這個角度上身體的死亡不再重要,靈魂是可以脫離身體存在的,“活著”意味著靈魂的存續。不同時間,不同環境,不同時代對“生”這一概念有著不同的解釋。相對的,對于“死亡”這一概念的理解在不同情況下也就不盡相同。對于生命的不同觀點對應了死亡的不同概念。
最普遍的“死亡”的概念是指身體的死亡。這也是我們一直在使用并且每個人都了解的概念。人的身體會隨著時間衰老直至死亡。在心跳停止的那一瞬間人即被宣布死亡。其他的則有精神層面的死亡。精神層面的死亡并不是指神話中所謂“魂飛魄散”的概念,而是說一個人的同一人格消失了。作為能夠思考的智慧生物,每一個人都有其獨特的思維,有著不同的人生觀和價值觀。這是每一個個體的獨特性所在。那么假設一位腦死亡且確定無法恢復的人,他的生命特征依然存在,但是能夠確定他是其本人的最重要的東西——思維,已經不復存在了。在精神層面上,這個人已經死亡了。如果有足夠高的科技能夠將另一個人的思維記憶等大腦活動內容全部復制到這位腦死亡患者的身上讓他醒來,我們會說醒來的人是被復制大腦活動的人而不是曾經腦死亡的人。腦死亡者在我們的概念中已經死亡。假如科技發展到一定程度后人類的壽命極大地提高。經歷漫長的時光之后,對于年輕時的記憶幾乎全部消失,三觀,思維都與曾經的自己完全不同。在這個情況下我們能否像上一個例子一樣認為曾經的那個人已經死亡,現在活著的是一個新的人呢?從某種意義上來看這是有一定道理的。人格同一性決定了一個人是甲而不是乙,那么當這個人格消失時,我們也可以定義為這個人已經死亡。
由此可見,思維、意識、精神,或者說人格的消亡也是死亡概念的一種。雖然現階段沒有技術可以分離人的身體和意識,但是這種想法是值得思考和研究的。
對于生者而言的死亡。死亡這一概念本質上對死者是沒有影響的。一個人死亡以后他本身不會再感知到世界,世界也不會對他有任何影響。對于死亡的概念其實是生者的想法。這其中寄托了對于逝者的懷念,以及逝者的精神和思想對生者的影響。例如哲學家,思想家等偉人,在他們的角度上自己已經死亡,但是他們的思想對于其他人的影響時長是遠遠多于他們的生命的。再比如親人或者朋友的死亡帶給我們的影響要比陌生人大的多。對于親人朋友本身而言生命的結束就是終止,但是對于生者而言依然要承受他人的死亡帶給自己的影響。我們在一些節日中會進行祭祀,在封建社會甚至認為人死后依然能夠享受祭祀和供奉。這也間接說明了死亡的概念不僅限于身體的死亡。在進行祭祀的人眼中,被祭祀者是能夠接收到這些祭品的。他們依然“活”在人的臆想中。而當無人祭祀,漸漸被遺忘的時候,他也就“死亡”了。所以也有文學和影視作品說“最終的死亡是遺忘”。
不論從哪個角度來看,死亡都是我們想要逃離和躲避的一種狀態,那么人類是否能夠避免死亡或者如何避免死亡就成了值得研究的問題。
二、人類能否避免死亡
人類身體的死亡是無法避免的。一些科幻題材的影視或者文學作品中有將人冷凍或者更換器官來維持壽命的劇情。這種方法可以延長人的生命很長時間,但是最終還是會死亡。
如果將一個人人格的消失定義為死亡的話,那么即使他的身體能夠一直支持生命活動,在他的人格消失(不論是由于移植了其他人的大腦還是漫長的時間使人格完全改變)的時候,我們自然認為他是死亡的。多數人認為精神或者意識比身體更加穩定,更不易摧毀。但是根據分析我們能看出精神的存續并不如身體穩定。因為一個人的人格,三觀會隨著他的經歷以及所處環境潛移默化的改變。當這種改變進行到一定程度時“我”就不再是曾經的那個“我”,針對“新我”而言,“舊我”就已經死亡了。擁有多重人格的人思想中有多個人格,在不同的時間和環境里展現出不同的人格。在與人交流時不同的人格會出現不同的反應。看起來根本不像同一個人。經過治療以及時間的推移有一些人格會消失,這也可以說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死亡”。由此可見,精神層面的死亡是完全無法避免的。
身體和精神剝離開本身就是一個統一的整體,現階段并沒有科學依據證明他們能夠被分離。即使可以,我們也還是逃脫不了死亡。所以死亡是每個人都需要面對的無法回避的狀態。那么人對于死亡的看法和態度就至關重要了。
三、人類對于死亡的看法
人類對死亡是恐懼的。人類社會中很少有人不畏懼死亡。即便有“舍生取義”的道義,那也是對這種道理的贊揚和褒獎,如果死亡不可怕,舍生取義就沒有被歌頌的必要性了。死亡本身對于個人而言并沒有值得恐懼的東西,因為沒有人知道死后是什么樣子。不清楚死后是痛苦還是美好,那么恐懼死亡本身并沒有意義。可是為什么人們會懼怕死亡呢?其實人對于死亡的恐懼來自于未知。沒有人知道死后的世界,這種未知是完全的未知,沒有任何跡象可尋。能夠尋找到的東西越少,對于未知的不安感越強烈,懼怕心理就會越強。所以人類對死亡的恐懼本質上是對未知的恐懼,是對于自己無法了解到又無法避免的事物的恐懼。
死亡具有孤獨感。因為死亡的過程需要一個人承擔和度過。沒人能經歷你的死亡,這個過程是必須要自己進行的。即使是在同一場事故中身亡的人也要經歷各自的死亡過程。這個過程是充滿了孤獨的。沒人能替我死,死亡是每一個人都必須經歷的,不論是誰都不可能代替其他人經歷死亡。我們經常說某人為救他人為人而死,但是這只能把死亡到來的時間延后,并不能讓人避免死亡。死亡是不能代替的。總有一天,死亡會到來而且人會獨自一個人死去。
四、研究死亡問題的意義
死亡的未知性讓我們想要探索它。但是死亡本身是與生活割裂開的,單純研究死亡而不思考研究它能帶來什么是沒有意義的。從哲學上來說,個體的死亡并不代表事物的結束。個體死亡,但是他的遺產、問題、關系等等并沒有消失,而是被繼承,或者被瓜分。我們無法避免死亡,但是死亡的未知又讓人恐懼。對比之下生命的價值就體現出來了。
我們無法避免死亡,所以人在生活中就會更加努力,由于生命的有限而更加珍視生命。對于死亡的恐懼讓我們能夠積極發展醫學延長人們的生命。因為死亡終將來臨,所以我們更加珍惜生命,努力的生活為了讓自己生活的更好。每個個體的努力能夠促進整個人類社會的不斷地發展與進步。看的更高更遠的偉人們把目光放在整個國家和世界,他們的努力并不僅僅為了自己,也是為了整個人類社會繁榮的未來。也有許多為了國家和人民把生死置之度外的英雄,他們值得人們敬佩正是因為他們克服了對死亡的恐懼。每個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在這有限的生命中做些什么事人人都要思考的問題。當我們對于死亡有著一定了解時,對于生命和如何生活這一問題也會有一個新的思路。我們“探究死”是為了“珍惜生”。死亡哲學也是如此,無論是什么時期,對于死亡的研究都對應著現實的生活。這也是研究死亡問題的意義——為了能夠更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