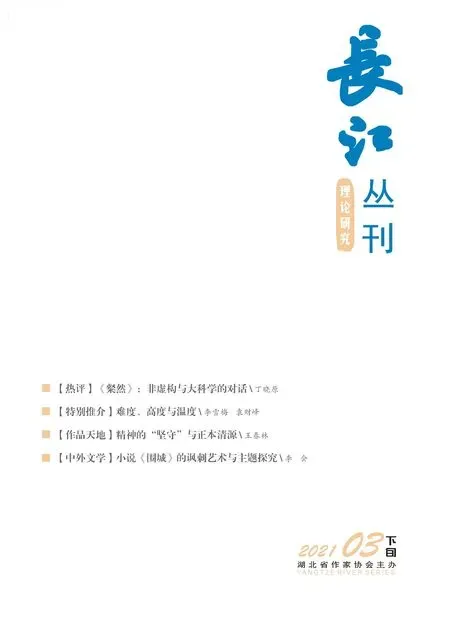翻譯層次論視角下的日語慣用語漢譯
■ /
日語“慣用句”,根據日本《大辭林》的定義是指“由兩個以上的詞組合而成,作為一個整體表達固定的意思。”其漢語表達,有人譯為“慣用句”,有人譯為“慣用語”,本文采用“慣用語”這一說法。
慣用語是各民族人民在社會生活生產實踐中形成的語言的精華,是民族智慧的結晶,代表了人民樸素的價值觀念和審美情趣。關于日語慣用語的漢譯策略和技巧,許多學者都通過研究進行了總結。如宋長營(2007)分析了日語慣用句翻譯的對比原則、神似原則和漢化原則,強調譯詞要形象生動。徐瞾瑢(2010)在對與動物有關的日語慣用句的漢譯策略進行分析時,提出了直譯法、套用法、替換法三種策略。王和平(2012)就將日語慣用語的漢譯技巧歸納為直譯、意譯、借譯等,強調了文化翻譯的重要性。直譯、意譯、套用法、替換法,這些都是從翻譯策略和翻譯技巧的角度進行的經驗主義的探討和研究,鮮少有人通過翻譯理論分析日語慣用語的翻譯。翻譯策略和翻譯技巧固然重要,能夠為我們進行日語慣用語的漢譯實踐提供寶貴的參考意見。但對翻譯實踐進行理論式探討也不可或缺,有助于高屋建瓴地理解翻譯活動,指導我們的翻譯實踐。
許鈞(1987)在《論翻譯的層次》一文中,明確提出了翻譯具有思維、語義和美學這三個層次的觀點,認為一個成功的翻譯不可能在一個層次完成,它應該是各個必要層次和諧統一的產物。之后,許多學者從思維層次、語義層次、審美層次這三個翻譯層次出發,進行了關于詩歌的翻譯實踐和翻譯評析。
本文將嘗試以許鈞的翻譯層次論為理論支撐,通過具體例句分析日語慣用語翻譯的步驟、翻譯技巧的選擇與取舍和具體譯文的評價標準,以期能為日語慣用語的漢譯提供新的思路,進而豐富日語慣用語漢譯實踐。
一、許鈞的翻譯層次論
1987年許鈞在《中國翻譯》發表了《論翻譯的層次》一文,經局部調整又于1989年在《現代外語》發表了同名論文,并在其編寫的全國翻譯碩士專業學位(MTI)系列教材之一的《翻譯概論》一書中再一次指出翻譯具有思維、語義和美學這三個層次。
許鈞的翻譯層次論是受法國著名符號學家皮埃爾·吉羅將語言符號分為邏輯符號、語義符號和審美符號的啟發而提出的。其在文章中指出具有全人類性的思維是翻譯活動的基礎,翻譯主體(也就是譯者)是借助于思維作用對翻譯客體(也就是原作)進行翻譯活動的。語言作為思維的材料,是以其語言結構和語義系統幫助實現思維,完成其表義、表感和表美等功能的。翻譯不可能囿于思維這一層次,翻譯還要按照不同語言符號達意、傳情的規律,用一種語言符號傳達另一種語言符號的意義,這就構成了翻譯的又一層次,即語義層次。思維層次與語義層次的關系是十分密切的,思維層次是語義層次的基礎,語義層次是思維層次的體現。關于語義的范圍,許鈞借鑒了索緒爾對于語言和言語的認識,即語言和言語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言語是說話人的行為和結果;語言是從言語中概括出來的規律的總和,它存在于言語之中,因此,語義可相應地區分為語言意義和言語意義。語言意義是語義的基本層次,它包括詞匯意義(即詞匯的所指意義)、句子結構意義(語法意義)和句子之間的關系意義;言語意義即是在特定的上下文中(廣義的上下文,包括語言環境)詞或句子乃至整個話語的特殊含義以及人們在參與言語活動的過程中賦予語言符號的附加意義,主要體現為語境意義與修辭意義或蘊涵意義。語言除了傳情、達意之外,還有審美職能,對于文學語言而言,審美職能甚至是其最重要的職能。一部作品的翻譯,除了思維層次和語義層次的活動外,有著更高層次的要求,這就是文學翻譯的最高層次,即審美層次。
二、翻譯層次論指導下的日語慣用語翻譯
(一)翻譯過程中翻譯技巧的選擇
從許鈞提出的翻譯的思維、語義和美學這三個層次,不只是平行的三個層次,它其實代表了從理解到表達的翻譯過程。可以通過逐層次分析,從思維層次向語義層次再到審美層次,由內而外、由抽象到具體、由局部到整體一步步樹立起翻譯的城堡。
例如:①關于日語中“很忙”相關慣用語翻譯。
根據許鈞的翻譯層次論,我們首先要從思維層次著手,首先搞清楚慣用語中一系列的概念意義。思維是對客觀事物的反映,雖然語言作為思維的材料,帶有任意性和約定俗成性的特征,但是反映的客觀事物卻能夠大致一致,因此在概念這一層次上就可能取得較為一致的對應。就這句慣用語來說,概念意義對應較為簡單,可以以此過渡到語義層次中的詞匯意義。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要運用判斷、推理等手段辨清概念的確切含義,確定其詞匯意義。含義的基礎上,理清概念之間的邏輯。日語中有一句關于很忙的慣用語翻譯過來是:
“貓/的/爪/借/想/程度/忙”
這只是詞匯的簡單組合,不符合漢語語法規律,下一步我們就要根據漢語語言規律直譯其語法意義和邏輯意義。
“忙得連貓爪都想借來一用。”
確定了語法意義和邏輯意義只是確定了其語言意義,語義層次還包含言語意義,即語境意義與修辭意義。日語慣用語就廣泛使用了比喻的修辭手法,修辭手法的處理和修辭意義的表達可以有兩種方式,一是保留其原喻體和修辭形態,有時可以通過加譯的方式表示出喻體代表的屬性。例如日語慣用語中以動物為喻體的條目很多,其中“貓慣用語”的大量存在尤為突出,而在眾多慣用語中極少有贊揚貓的,貓所代表的形象通常是無能之輩、無用之才或無恥之徒。保留其喻體和修辭形態可以譯成:
a “忙得連沒用的貓爪都想借來一用。”
另一種方式是去除其修辭形式,進行意譯出其蘊涵意義:
a′ “非常忙”
一些自然科學類的科技類的文章,一般翻譯到語義層次就算完成了。但是慣用語一般應用于會話和文學作品中,還需要進行審美層次的翻譯,也就是從接受美學的角度,充分考慮接受者(也就是讀者)美學感受的基礎上,首先對原文進行審美,再通過調整譯文的文字、韻律、節奏、結構等形式因素來傳達原文的美。
通過語義層面的直譯和意譯分別形成了a和a′兩個譯文。首先從讀者接受度來看,a很明顯不合適,a譯文對于中國人來說,雖然能大致明白其意思,但是因為日語中貓的形象和漢語中貓的形象有所差異,漢語中關于貓的慣用語也非常少,所以這種表達并不符合漢語習慣,讀起來也別扭。a′譯文意譯出了原文要表達的意思,但是只是普通的敘述句式,沒有表達出原文具象化、形象而生動的美感。
要做出符合原文審美的譯文,首先可以考慮漢語中形象生動地表達其基本語義“非常忙”這一狀態的表達方式,比如:
b “忙得恨不能有分身術。”
b′ “忙得恨不能多長一雙手。”
也可以充分利用漢語詞匯的優勢進行“功能代償”,比如利用一些三字、四字詞匯:
c “忙得團團轉”
c′ “得不忙可開交”
最終再根據不同的語境選擇不同的譯文,b組譯文更形象生動也更俗語化。
(二)翻譯評價
翻譯層次論,不但指導我們逐層次推進翻譯過程,對于我們進行翻譯評價也提供了清晰的標準。古今中外的翻譯學家關于翻譯的定義與對翻譯活動的認識有眾多版本,但卻一致認為傳達意義是翻譯的目的所在,是翻譯的核心和根本。所以我們在做翻譯評價時,首先要確認語義層次的正確性,確保“譯得對”,然后再從審美層次上確認是否完成傳情、共感,是否傳達韻律等形式之美,也就是“譯得好”。具體到日語慣用語的翻譯就是,是否表現出其通俗性、習用性、生動性和形象性。先語義再審美,切不可前后顛倒、主次不分。如:
②關于日語中“百密一疏”的慣用語翻譯,對應為漢語的慣用語有:
d 常在河邊走,哪有不濕鞋。
e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
f 猴子也有從樹上掉下來的時候。
g 人非圣賢,孰能無過。
h 老虎也有打盹兒的時候。
i 千里馬也會失蹄。
猴子是爬樹好手,有時也會從樹上掉下來,這是一種比喻的說法。
采用套譯方法的譯文d“常在河邊走,哪有不濕鞋。”看似和原文意思吻合,仔細分析其實不然。“常在河邊走”指的是常處在某種環境,“哪有不濕鞋”表示一種必然的結果,講的是環境對人的影響,常用于勸誡人不要有僥幸心理。
譯文e“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出自《晏子春秋》,意思是不論多么聰明的人,也會出現個別失誤。從語義層次看與原文非常接近,主體相對,事項相近。從審美層次看“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作為漢語成語,四字對仗,形式工整,和原文形象、生動的具象化表達,各有千秋。兩者之間的細微差異在于漢語偏雅,原文偏俗,漢語偏謀事,原文偏做事。這也是現有慣用語詞典普遍采用的譯法。
直譯的譯文f“猴子也有從樹上掉下來的時候。”,從語義層次看,大致能夠表達原文的意思,但是從審美層次看,同原文相比出現了感情偏差,在原文中“猿”擅長爬樹,所代表的是能力卓越的人,帶有褒義色彩。翻譯成漢語時,如果保留原喻體“猴子”,中國人聽起來會感受到些許貶義色彩,因此不適用于安慰他人。但是少許比較隨意的會話中,單純講述事實時偶可使用。
譯文g“人非圣賢,孰能無過。”出自《左傳·宣公二年》:“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意思是一般人不是圣人和賢人,誰能不犯錯?錯了能夠改正,沒有比這更好的了。其主體是一般人,事項是犯過錯。而原文的“猿”是爬樹的能手,也會從樹上掉下來,其主體是能手,事項是失敗。
譯文h“老虎也有打盹兒的時候。”比喻精明或厲害的人也難免有疏忽的時候。和原文意義相近,為中國人所熟知,根據具體的語境,有時也不失為一個好的譯文。和原文相比,語義側重在疏忽、大意。
譯文i“千里馬也會失蹄”源于成語“馬失前蹄”,“馬失前蹄”比喻偶然發生差錯而失敗受挫。“千里馬”是馬中的佼佼者,可日行千里,長于腳力,和原文中擅長爬樹的“猿”相對應,可以說是和原文從語義到審美最為契合的譯文。
以上是把慣用語作為獨立的語句,從翻譯層次論的角度對譯文進行的評價。但是在實際翻譯實踐中,任何的詞句無論是思維層次、語義層次還是審美層次,意義都是動態的,而非靜態的,是和語境密切相關的。
例1:日語中類似“老師有時也會出錯”的慣用語。
譯文:智者千慮,必有一失。老師有時也會出錯。
例2:日語中“專業人士也有失誤的時候”的慣用語。
譯文:老虎還有打盹兒的時候呢,美國棒球聯盟的選手也會有三擊不中的情況。
三、以翻譯層次論為指導,發揮主觀能動性,充實日語慣用語翻譯
并不是每個日語慣用語都被錄入到了慣用語漢譯辭典,即便被收入到了漢譯辭典中,也是直接給出的譯詞,并非對語義的解析,所以譯詞有限,審美層次表達較單一。在翻譯層次論指導下,根據不同的審美層次探討,發揮主觀能動性,可以創造出不同風格的譯語。一些語義和審美皆契合、互為套譯關系的漢日慣用語,在不同語境審美下,不一定是最佳譯文,要將更多的近義慣用語納入視野,合理選擇,這都將豐富日語慣用語的漢譯庫。
高寧(2015)在關于詞匯的翻譯中強調“日語選義,漢語選詞。”這也適用于慣用語漢譯。這就意味著我們在確定慣用語的語義時,首先要查看日語的慣用語辭典釋義,然后選擇合適的譯詞。選擇譯詞不局限于漢譯后的慣用語辭典,而是從豐富的漢語語言寶庫中尋找素材,進行創造。如:
③虛禮不如實利。
這一慣用語并不像慣用語①②那么常見,一些慣用語辭典并沒有把這一詞條納入其中,在線諺語辭典解釋為“比起口頭語言上的答謝,更樂意得到金錢”。《詳解日語慣用語詞典》的翻譯為“虛禮不如實利”,這一譯文從語義層次看解釋準確,從審美層次看“虛”“實”相對,“禮”“利”諧音,達到了思維層次、語義層次和審美層次的和諧統一。“虛禮不如實利”并不是漢語的固定慣用語或諺語,是編者憑借自身深厚的語言功底所譯,不屬于翻譯技巧中的套譯法。
從審美層次看“虛禮不如實利”偏書面語正統風格,并不能滿足所有審美需求,因此需要也能夠在理解核心語義的基礎上,運用漢語豐富的韻律,創造出審美各有側重、風格不一的好譯文。如:
j 口再甜,不如錢”(頗具口語性和漢語諺語風格,又兼具諧音,在口語化的表達中不失為一個好的選擇。)
k 噓寒問暖不如打筆巨款(頗具流行語特征。)
l 好話不如現鈔(和“虛禮不如實利”相比,更通俗,更具形象性。)
m 好話千遍不如鈔票一疊(巧妙加譯“千遍”和“一疊”,通過強烈的數字對比,強調語義。)
四、結語
在實際翻譯實踐中,會遇到對應多個可套譯漢語慣用語的詞條,也會遇到漢語中并無可套譯或替換的固定慣用語的詞條,還會遇到慣用語辭典的譯語單一、不能符合語境審美要求的詞條,甚至會遇到日漢慣用語辭典并未收錄的詞條,面臨日語慣用語的漢譯選擇和創造,我們可以從“思維、語義、審美”三個層次,步步為營,創造出三個層次和諧統一的好的譯語。
注釋:
①例句123均取自網絡https://www.tedukurikotoba.com/entry/1069.html,譯文為筆者自譯。
②大連理工大學出版社出版井上宗雄主編的《日語慣用句用法辭典》、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出版王銳編著的《日語慣用語、諺語詳解》以及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葉琳主編的《常用日語慣用句》沒有收錄該詞條。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劉振宇和劉劍主編的《詳解日語慣用語詞典》中有收錄,譯為“虛禮不如實利”。
③https://kotowaza.jitenon.jp/koto-waza/346.php.
④Jklm是選自網絡、論壇中較好的譯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