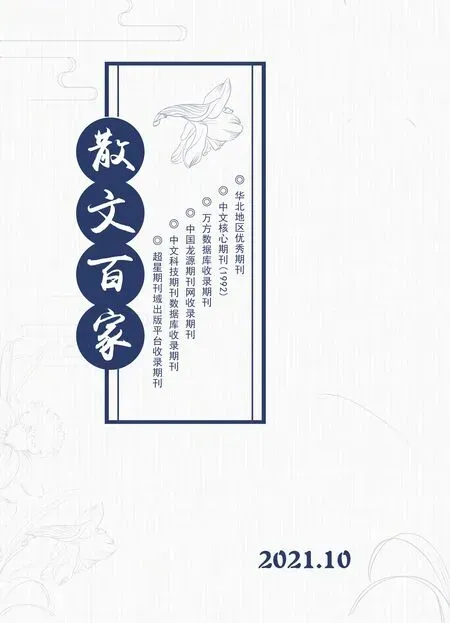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蔣 穎
揚州大學
最可厭的人,如果你細加研究,結果總發現他不過是個可憐人。
如果你認識從前的我,那么你就會原諒現在的我。
——張愛玲
最初接觸到張愛玲的作品時,我并不了解她這個人,只是單純地讀她的天才之作,卻最終深深為她吸引,我驚嘆于她的才華,她的冷傲,她的清高。但當我后來讀了許多張愛玲的傳記后,我漸漸深入地走近她,了解她所處的那個戰亂的時代,那個曾經歡樂但又無限黑暗的家庭,那個她不斷追尋卻又不斷被遺棄的愛情,那個她投入甚多的友情,我才發現她也不過是一個可憐的人。張愛玲小時候就很喜歡《紅樓夢》,張愛玲的人生也與《紅樓夢》有著驚人的相似點——皆是圍繞一個“情”字展開的。
親情: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
她愛自己的父親。父親張廷重也很看重女兒的文采,常常把女兒的大作展示給親友看。父女倆常常一同出去看戲、買點心,回到家便就那些戲曲和小說侃侃而談,她和父親更像是精神上和文學上的知己。當她每每同父親討論《醒世姻緣》《紅樓夢》等小說的優劣時,父親張廷重總是細心傾聽著,并幫她分析辟理。她在父親這里,獲得了她想要的尊嚴,獲得了傳統文化的熏陶。她喜歡那些秀麗端整的對仗,一口氣寫了三首七絕,其中一首《詠夏雨》“聲如羯鼓催花發,帶雨蓮開第一枝”,夏雨如緊湊的鼓聲般催促著杏花早日綻開,晶瑩剔透的圓珠從荷葉上滾落,愈是襯出滿塘中第一朵蓮花的搖曳之姿。清新如斯,淡雅如畫,正如她的父親給她的溫雅的愛。
然而后來,父親又娶了一位后母,愛玲更是經歷了難以言狀的悲慘,她開始漸漸怨恨父親的家,直到后來父親出手打了她,并聲稱要將她打死,甚至幽禁了她長達大半年之久。很難想象,她這大半年來是如何熬過的,她得多么絕望難耐。她對父親的依賴與聯系就此決斷,她對父親的愛漸漸模糊了,顯現出來的是恨意。如果了解到她的這番經歷,就能夠原諒她的冷血、無情與冷漠。她只能一個人躲在小房間里思考人生,在內心里和自己對話,這也成就了她后來小說中心理描寫的深刻和細膩,成就了她對人性思考的深度。
除了父親,她也愛著自己的母親。她總是貪婪而緊張地到處收集著有關母親的回憶。她喜歡一切她媽媽喜歡的事物:藍與綠、繪畫、鋼琴,她喜歡母親夸獎她,她喜歡母親給她取的名字——張愛玲。在父母離異后,張愛玲忍受不了在父親家中的排擠、黑暗與孤獨,她決然選擇逃跑,去找她的母親。母親對兒時的張愛玲來說就是美,就是愛,就是整個世界。她與母親在一個小洋樓里過著拮據但幸福的生活,她們一起洗衣、做飯、逛街,參加聚會。但是漸漸地,母愛消散了,因為在生活中張愛玲“愚魯”得一塌糊涂——她不會削蘋果,不會補襪子,這些讓母親黃逸梵異常沮喪與惱怒,母親曾對她說:“我懊悔從前小心看護你的傷寒癥,我寧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著使你自己處處受痛苦。”字字誅心,句句刻薄,再沒有什么怨毒的話,能比母親的否定更讓敏感的她愈發自慚形穢。任何感情都是可以被耗盡的,若它不能被滋養與灌溉,便只會日漸干涸,終至消逝。后來,黃奕梵去了歐洲,而曾經的甜與苦,都被稀釋、被暈染、被漫漶,直至消失。
晚年的張愛玲,一直尋求著自我靈魂的救贖。當她知道母親臨死前將自己遺留的古董都寄給了她,母親的身邊也一直保留著自己那張眉眼清淺的畢業照時,她終于明白了:“行至水窮處”,母親還是愛她的,盡管這愛不完美,不濃釅,亦如這世間每一個千瘡百孔的人生。所以,在她的《愛恨錄》中,她還是將母親歸入自己愛的人。她常常自言自語,“來日,我一定會去找她賠罪的,請她為我留一條門縫!”
張愛玲的冷傲孤僻的性格不是一開始就形成的,她也曾熱烈,她也曾深情。這個世上,有一種情不可替代,那便是親情。然而,乍暖還寒的親情最讓人難耐。也正是這乍暖還寒的親情,造就了她冷若冰凌的心。
愛情: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
張愛玲在尋覓愛情的過程中先是遇到了胡蘭成,“見了他,她變得很低很低,低到塵埃里。但她的心里是歡喜的,從塵埃里開出花來。”她不論世人如何看她,她只想去追尋自己想要的幸福。因為童年的她感受不到她想要的父愛,所以他一直在尋找她內心空缺的那個父親。因此,當她看到胡蘭成時,便認定了他。但是,胡蘭成并沒有父愛的情懷,所以這兩個人在一起就注定了張愛玲悲劇的人生,她過得太辛苦了。后來胡蘭成四處逃難,她還將自己的30萬稿費全部寄給了胡蘭成,對,在那樣一個國家動亂、民族危亡的時代之下,她顯得有些自私小我,她變得有些遲鈍麻木。可是她的內心也很痛苦,痛苦到只能安慰自己說:“因為愛過,所以慈悲。因為懂得,所以寬容。”從此,悲涼、荒涼、蒼涼、凄慘是張愛玲生命的底色,也是從頭到尾她作品的底色。
年輕時,她選擇一個中年人做伴侶。
中年時,她選擇一個老年人做伴侶。
她定居美國后,遇到了作家賴雅,并與之結婚。也許這段婚姻談不上什么愛情,但是這卻和親情有關。她擇偶的強迫性重復,均來自她對父愛的渴望,對親情的渴望。由于張愛玲始終無法擺脫自己的戀父情結,然而現實的矛盾也更加造就了她悲涼凄慘的人生。
在愛情中,她不斷地“尋尋覓覓”。她成了她筆下的“紅玫瑰”王嬌蕊,熱情而又幼稚,能夠拋棄一切去追尋自己心中的愛情,證明自己曾經愛過;她也成了她筆下的“白玫瑰”孟煙鸝,寂寞凄清,空虛恐懼,生命逐漸變得蒼白;她也成了她筆下的白流蘇,如一葉枯草,無所依傍,而這無所依傍使她變得防范自私。尋覓之中,她的生命也變得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她對愛情、對男人的理解都更加深入了,她逐漸看透了所謂的“死生契闊,與子成說”,這些從來都是一剎那的刻骨銘心,卻永遠沒有地老天荒的相依相守。
友情:一片冰心在玉壺
她對待友情,是任性的,是隨心而走的,她很單純,誰對她好,她就對誰好。
她寫給同學的留言是最用心的,她不敷衍不虛偽,當然也不落窠臼,她在自己的內心世界里對著每一個人笑,但是他不會外露出來,在表面上只做出一副我冷傲我孤芳自賞的樣子。
在香港,她交到了一個好朋友,那就是炎櫻。她欣賞她,因為炎櫻是除她以外另一個特立獨行的人,兩個性情相投的人注定是要惺惺相惜的。她們都是異想天開的奇女子,一個將女人比作“紅玫瑰”與“白玫瑰”,一個將蝴蝶比作花的鬼魂;她們都是勇敢大膽的叛逆者,一個策劃離家出走,一個在流彈打碎浴室玻璃后還能穩坐不亂,從容地潑水唱歌。她們一起設計服裝,一起穿著奇裝異服,招搖過市。她們一起度過了最快樂的大學時光。當喜歡一個人時,會把自己所有最好的都獻給她。張愛玲也不例外,她只有才華,便為炎櫻寫作,為她作畫。她把一切能夠給她的都獻給了她。
然而,張愛玲既然能對炎櫻“濃情”,也能對她“寡情”,甚而“絕情”,因為這才是一個古靈精怪、陰晴不定的張愛玲。炎櫻定居日本后,愛玲移居美國,炎櫻多次給她寫信,問她:為什么莫名其妙不再理我?張愛玲說:“我不喜歡一個人和我老是聊幾十年前的事,好像我是個死人一樣。”她對待友情,真可謂是純真任性無比,她看重友情,為其傾盡所有,但她又踐踏友情,使它變得一文不值。在她的眼里,“情”貌似可有可無,但實際上她是因為太重“情”而對“情”寄寓了太多的厚望,而事實總是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
她對待友情,是溫和真誠的,卻也是隨性淡然的,她的心像在玉壺中的冰一樣潔白透明,但也不妨有些冷凄冰涼,真可謂是“一片冰心在玉壺”。
才情:自是花中第一流,情疏跡遠只香留
張愛玲是一個天才兒童,6歲入私塾,在讀詩背經的同時,就已經開始小說創作。她寫過一篇名為《快樂村》的類似烏托邦式的小說,寄托了她對未來的幻想。她十二歲時發表的處女作《不幸的她》,語氣老成,完全超出了同齡人的水準。她十四歲時寫的《秋雨》,字里行間都流露出一種壓抑悲涼。現代女作家有以機智聰慧見長者,有以抒發情感著稱者,但是能將“才”與“情”打成一片,在作品中既深深進入又保持超脫的,張愛玲算是絕無僅有的一人。
她的才情“自是花中第一流”,她多舛的命運,她的親情、友情、愛情無一成就了她的才情。可是當張愛玲發現胡蘭成對她的愛情燃燒殆盡時,凋謝的不只是張愛玲的心,她驚世駭俗的寫作才華亦隨之而逝,使她“情疏跡遠只香留”。
共情:夜半無人私語時,怎一個“悲”字了得
很多人說張愛玲身上沒有煙火氣,她不是一個世俗之人,她與世隔絕,但是她也是個想要尋求共鳴之人的人。“夜半無人私語時”,她便通過她的作品在與世人交流來尋求一種共情,她希望別人能夠理解她。她曾反省過自己自私、可厭,可她缺少的是一個能夠真正懂她的人,如果細加研究她,就會發現她不過是一個尋求共情卻又不得的可憐之人。
她不能為世人所理解,她只能與她心目中的自己共情,因此她挖掘出了最深刻的人性、最真實的人情,她與宇宙萬物共情。她不斷追尋著人類美學的最高境界——悲劇。她用傳奇性的畫筆描繪了一個個充滿悲劇色彩的故事,刻畫了一個個充滿悲劇色彩的人物,營造了一個陰森蒼涼的人間世界。她與她所創造的人間世界里的人物對話,她與她所創造的人性對話,她在不斷尋找著共情的對象,但是她又尋不到,這些,又“怎一個悲字了得”!
她的一生為情所困,她的親情使她不斷追尋充滿父愛的愛情,她的愛情燃燒盡了她驚世駭俗的寫作才情,然而又是這些世俗之“情”成就了她的才情。親情的“乍暖還寒”、愛情的“尋覓凄慘”、友情的“玉壺冰心”、共情的“無人私語”,還有時代的無限愴痛皆在張愛玲的心里留下了抹不去的陰影,形諸文字。因此,她的文風看似綺麗多姿,但若滿眼望去,卻又盡是蒼涼的底色。對于張愛玲,沒有人能夠完全讀懂她的“情”,誰也不敢說能準確地透析其作品喧鬧色彩背后的無盡意味,是怎般的心緒,又是何種蒼涼。
“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張愛玲用盡一生之情以極大的勇氣去追尋本該屬于自己的那份幸福生活。在此過程中,也許我們會發現她是自私的,她是“小我”的,她冷漠寡情,獨標清高。但是,當我們站在她的角度來思考時,當我們去回想她所處的那個戰亂年代時,當我們真的走進她的親情、愛情、友情,真正走近她的內心時,就會發現她真是一個可憐之人,她的一生都在尋覓“情”,但終又不得。她反省過自己,揭示自己身上的劣根性,她曾說過:“以年輕的名義,奢侈地干夠這幾樁樁壞事,然后在三十歲之前,及時回頭、改正。從此褪下幼稚的外衣,將智慧帶走。然后,要做一個合格的人,開始擔負,開始頑強地愛著生活,愛著世界。”她知道自己做了錯事,所以她的后半生一直在救贖著自己,在紀念匆忙的輝煌過后神秘的淡出,承受燦爛奪目的喧鬧與極度的孤寂,暗灑一路幽香,任由裙裾飛揚。這也許正是張愛玲所追求的生命效果,所追求的“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的境界。
張愛玲是一口古井,淘不盡,挖不完,深不見底,秘不可探;張愛玲是一杯苦酒,時間或許會濾去其中苦烈的部分,那淡淡的余香卻永遠令人回味。張愛玲是近代民國文學史上的一朵奇葩,一朵脈脈含情的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