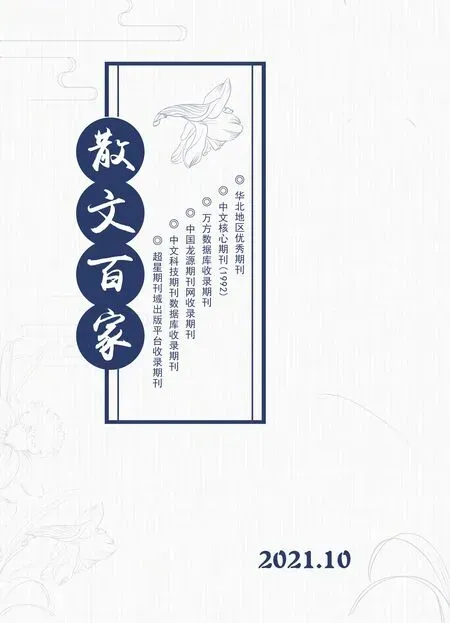《雪國》的空間敘事與倫理訴求
孫甜甜
河南大學外語學院
20世紀以來,人文社會學科的“空間轉向”成就了空間敘事學的興起。在文學研究的“空間化”視野中,空間敘事學重在考察文學作品中空間書寫的文本結構、象征意義、社會屬性和文化內涵。文學作品建構的空間類型(如物理空間、社會空間、生存空間、文本空間、精神空間等)多種多樣,它們相互交織、相互補充,共同完成對小說主旨的呈現。運用空間敘事學理論分析文學作品中不同空間的建構及其意義,可以為我們理解敘事作品的情節發展、人物形象以及多重主題提供獨特的研究視角。
本文以“空間敘事”這一角度為切入點,旨在揭示“空間”這一因素在《雪國》中的作用以及空間與人物、時間的互動,進而試圖從物理活動空間深入到人物的精神空間以及作家空間設置與人物塑造的倫理訴求。
一、空間敘事類型
1.物理空間。
董曉燁指出“空間在文本建構和營造氛圍具有重要的作用。空間不僅僅是客觀世界的真實反映,還受到讀者的主觀影響。阿伯特“探討了空間建構對于營造氣氛的積極作用,并提出‘行動制造了空間’。”雪國、隧道以及東京成為《雪國》物理空間構建的重要元素。根據列斐伏爾的社會空間理論,敘事作品的空間在一定程度上同任何社會一樣具有身份和主體性。“社會空間具有建構力量,能夠影響、制約社會和人們的行為和存在,是一個無限開放并且充滿了各種矛盾的過程,是各種力量形成對抗的場所”。文章的開頭部分如下:穿過縣界長長的隧道,便是雪國。夜空下一片白茫茫。(《川端康成全集、第10卷》新潮社9頁)這一句是給讀者留下鮮明印象的最有名的一句。“國境”是關東和越后的邊境分水嶺的三國山脈,“隧道”是“清水隧道”。昭和6年,隧道開通之前,縣界山的對面是某個不知名的村子,是村民都相互不認識的山間僻地。《雪國》的原型是有人居住的地方,被稱為世界上屈指可數的暴雪地帶的越后湯澤地區。同時,島村通過葉子和站長的對話,第一次意識到這里是因雪崩而火車屢次進退不得的暴雪之地,是與島村日常生活的“場所”不一樣的“空間”。
在整個雪國深層敘事之中,隧道一直作為核心的意象,成為貫穿始終的結構性象征。川端以長長的隧道為界限,以從“現實的世界”到“非現實的世界”這樣的心境來展開小說的情節。在此用“現實”這個詞語來表現隧道對面的世界,用“非現實”來表現隧道這邊的世界。穿過隧道在這邊的雪國是與現實世界不一樣的世界,是“超脫人世的象征的世界”。因此其中的人類的行為在島村眼里顯現出來的是“透明的幻象”。隧道是島村從現實世界到非現實世界的通道,有通過儀禮有著某種內在的關聯。簡單來說,通過儀禮具備以下三方面的特征。第一,某個個體從他所屬的集團或社會中分離隔絕出來。第二,從中有了新的體驗。這些體驗大多是困難的、伴隨痛苦的。在某些場合暴露出死亡危險的事物。第三,再次回歸到集團或者社會,經營共同生活。那個時候,與分離隔絕的時候有著質的不同。即:實現了可以稱之為“生的覺醒”“再生”的面貌改觀,簡單來說,變成“脫胎換骨的存在”。小說由“穿過縣界長長的隧道”一句開頭具有這樣一種效果:讓讀者領會到潛入隧道之前的世界和潛入之后的世界是完全不一樣的,主人公島村從穿過隧道以前的道德和生活中得以解放,或者忘掉這些,開啟新的生活方式變得非常自然。潛入隧道的島村沒有被以前的生活所拘束。總之,誕生了新的島村,讀者也不會考慮潛入隧道之前的島村的職業、家室以及社會地位,或者那種探索變成了被拒的情節。事實上主人公島村通過新的道德,與以駒子為首的人結成了新的關系,過上了潛入隧道之前沒有想過的、不被允許的生活。讀者只能是很自然地承認這些。潛入隧道再次折回東京的話,別的生活在等著島村。由此看來,經過在雪國發生的一系列事情之后,島村在某種程度上獲得了精神上的成長。
東京地區與雪國之間構成了中心與周緣之間的二元對立。“長長的隧道”對面的東京地區是近代西歐文明泛濫的地方,與之相比,雪國地區還沒有被近代西歐文明侵蝕,還殘存著日本的傳統文化。作為作品世界的中心舞臺,在雪國地區中設定了溫泉村,隧道開通以后,吸引了來自東京的各種各樣的客人:春天和夏天的登山者、秋天觀賞紅葉游客、冬天滑雪的客人,因為越來越多的觀光客人的出入,溫泉村被設定為傳統文化逐漸衰弱的空間。這里的東京是發源于人為創作的都市文明的空間,在都市文明的背后潛藏著近代西歐文明。另一方面,設定為與東京相對立的雪國是被自然現象所支配的空間,其背后潛藏著日本乃至東洋的傳統文化,并且其基盤中存在著“自然”。
總之,《雪國》中的物理空間向讀者提供了了解該作品創作背景、社會環境和時代風情的窗口,不僅呈現出作品題旨,還成為讀者理解和思考作品特定背景的重要途徑。
2.人物精神空間。
(1)駒子。駒子出生在雪國地區的某個港町附近。她來到港町,在港町舞蹈老師門下學習,上完短期藝伎課程之后,她十六歲的時候去了東京,輾轉于飯館等地方,體驗了為期一年半左右的東京生活。在十七歲的時候再次回到雪國。暫時留在雪國的港町,在火車開通前跟隨舞蹈師傅來到溫泉村。這樣看來,駒子的東京生活僅維持了一年半左右的時間。反過來說,刨除這一年半的時間,駒子十九年的時間都在雪國度過。雪國的人們“在雪中繅絲、織布,在雪水里漂洗,在雪地上晾曬”。雖然駒子本身沒有做那樣的生計,但是既然她生活在雪國,就是生于雪國、長于雪國,用雪融化的水清洗身心,在雪中生活的人。正因為如此,在生活于東京的島村眼里,駒子是潔凈的女性。總之,島村被雪國代表性的自然物—雪打磨的駒子“潔凈”的身心所吸引,對她持有興趣。
在雪國文本中是這樣描寫駒子的嘴唇的,“像蛭之輪一樣伸縮流暢”、“沉默的時候也像在動一樣”、“濡濕發光”。嘴唇可以說是作為駒子的肉體以及“情欲的象征”來描繪的,從這件事也可以看出對于男人,她是具有非常強的性牽引力的女性。而且,從島村居住的東京的角度來看,駒子完全是異域的居民,但精神上卻是“拖著東京的影子”生活著的極為現實的人,中村光夫先生刻畫了這樣的駒子的形象,這樣評價道:“純粹的日本式的東西”—從民眾中走出來的、像是民眾的代表人”。
(2)葉子。葉子是《雪國》中另外一個重要的出場人物。葉子的聲音“優美而又近乎悲戚,那嘹亮的聲音久久地在雪夜里回蕩”。在島村看來,葉子的眼睛“有點”粗獷。葉子的眼睛可以說是雪國的象征,在故事中多次被描寫,與近乎悲戚的美麗的聲音并列表現出葉子的特點。但是,這雙眼睛不單單是粗獷,隨著島村與駒子的關系加深,島村感到“刺穿般的”眼神。川端在《獨影自命》中注解葉子是“閃爍的葉子”。確實,僅僅以聲音和目光為特征的葉子的存在,不能成為故事的中心人物,也缺乏生活感,這些都是事實。然而,在這個故事中,因為“自然”被細致地描寫了出來,所以“本地姑娘”葉子的生活場所比讀者所接受的印象還要細膩。在作品中,葉子是一個對島村和駒子都有懲罰能力的存在,總之葉子有著對主人公兩人行動進行限制的能力,在這一點上,可以說她是掌握故事決定權的人物。葉子是鏡中的人物,帶有虛像的性質,葉子的出現豐富了對島村和駒子的描寫。
通過對人物形象的塑造,折射出《雪國》兩位女主人公的性格特征與精神空間,推動了作品情節的發展,增強了作品的表現力和感染力。
二、空間與人物的關系
島村的興趣從東京轉移到雪國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是因為他有直接接觸雪國的自然物、恢復自己斷絕的生命體系這一意圖。《雪國》的主人公島村探訪雪國自然的理由是:因為失去了對自然和自身的嚴肅認真,喚回這個的話去山上比較好,經常一個人去山上散步。對自然和自身的嚴肅認真過于漠然,不得要領,這部作品中洗掉污濁這一主題時隱時現。在雪國站下了車,堵塞的鼻子一下子就通透了,一開始寫道“似乎是臟東西洗掉了”。在伊豆把臟東西洗干凈的是水,就像后面看到的這里是雪,是火。有像舞女一樣的純潔的女人。并且不僅僅是一個人,駒子和葉子這兩個女人分別把島村洗干凈了。“要喚回對自己容易失去的真摯感情”,深入到自然中,即:作為恢復失去的人性的手段,把自己沉浸到自然之中,是人類經常用的方法。這種自然與人類之間的連接方式,很早就固定在日本人對自然的態度中,是非常常見的態度。通過沉浸到自然中,人們希望撫慰、凈化受傷、衰弱的心靈。通過自然的生命力恢復人類本來的力量。
島村探訪雪國的小山村,除了喚回“嚴肅認真”之外,還有很明顯的理由。就是駒子。要說駒子的什么把他迷住了,就是她的性的魅力與純潔。對島村來說,擁有清純妻子要素的女性同時也是具有強烈母性要素的女性。對皮膚白皙、微胖的中年男子傾注了自己全部的愛情,擁護男子的任性的性關系,要理解駒子這種不可思議的深愛的樣子,只能是考慮駒子的母性要素。因為駒子是戴著妻子面具的母親,所以幾乎無條件地原諒了島村,并擁抱了他。而且,被擁抱的島村也是充分滿足被母親庇護的條件,被賦予了可以稱之為永遠的少年的要素。與有秩序、對立、排他的男性文化相比,女性文化帶有一定的包容性,另外涉及到島村對母親的“子宮幻想”。
三、《雪國》空間的倫理訴求
“空間敘事不僅是一種形式技巧,還具有倫理意義”。黑格爾指出:“藝術的內容就是理念,藝術的形式就是訴諸感觀的形象,藝術要把這兩方面調和成為一種自由的、統一的整體。”江守義也指出,“任何敘事形式中都包含著道德因素,換句話說,任何敘事最終都指向某種倫理訴求”。因此,上文論證的敘事空間作為《雪國》敘事的外在表征必然含有其深刻的倫理意蘊。
川端在《雪國》中成功地將敘事形式與倫理內涵有機結合,以高超的空間敘事藝術和倫理線的并置凸顯了小說核心人物島村及其敘事功能,同時也表達了作者的倫理思考。正是獨特的空間敘事形式和深刻的倫理內涵的有機統一成就了該作品,因而對《雪國》空間敘事和倫理內涵的觀照是挖掘這部作品審美價值的重要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