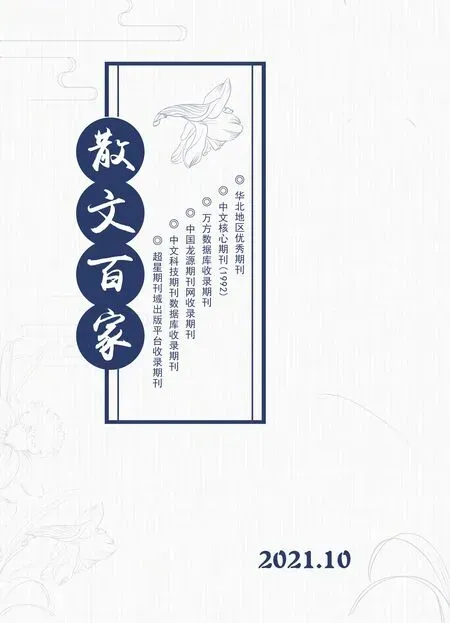凌叔華在京派中的獨特創作
張晨光
延邊大學
凌叔華是現代文學的重要作家,也是京派的先驅成員,她以出色的編輯、翻譯、創作能力為京派作出過巨大貢獻,在京派的發展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但是,有關凌叔華與京派關系的研究,要么將其與林徽因、楊絳等京派女作家歸為一類,從女性視角去探討她們對京派的視覺填充,要么就讓其滯留在邊緣地帶,時隱時現。雖有個別學者針對凌叔華與京派的關系發表過真知灼見,但大多寄居于凌叔華傳記、京派文學研究以及各類文學史、散文史中。凌叔華的創作個性被淹沒在京派的審美共性中,其與京派的關系愈加撲朔迷離。筆者力圖從凌叔華及京派眾人的創作個性入手,抽絲剝繭,層層深入去探尋凌叔華與京派文學的共性,以便在整體關照下精確把握凌叔華的創作特色,從細微處去窺探京派群落的審美理念和創作實情。
探究凌叔華與京派文人的人文關系,追溯凌叔華與京派的淵源,理清凌叔華與京派的師承脈絡,考證凌叔華在京派的文學活動。此外,她在文學創作上力求突破現狀,以個性化的文藝作品塑造著流派面貌,進一步拓展了京派文學的審美風貌,為京派的發展崛起作出了舉足輕重的貢獻。
凌叔華在五四時就師從周作人,凌叔華最初走上小說創作的道路,與周作人的指導、提攜密不可分,而雙方相似的文學主張及美學格調使他們走向共同的文學流派。在京派活動期間,兩人均參加過京派組織的文學沙龍、約稿聚餐,還共同擔任了京派刊物《文學雜志》的編輯,為京派“自己的園地”出謀劃策,盡心盡力。但她在步入京派的過程中,就文學創作而言,與以周作人為宗主的前期京派關聯不大,其審美取向與創作風格更接近以沈從文、朱光潛為核心的后期京派。而凌叔華進入京派的過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她是沿著“現代評論”派、新月派等自由主義文人集團的發展脈絡,走向共同的流派——京派。而后期京派作家既繼承了周作人文學自由與寬容的觀點,捍衛文學獨立、自由、寬容的精神,追求文學的純正性,又傳承了五四時期理性的人文精神,做出一系列“嚴肅”文壇之舉,凸顯人的自然神性,以期重塑國民精神。凌叔華的文學創作與審美取向,顯然與后期京派更為投合。
凌叔華作為京派的資深前輩,其文學創作不僅對京派有著相當程度的繼承,而且還拓展了京派文學的審美風格。女性敘事、兒童視角、自然描摹,是京派作家都曾涉及到的題材,也是他們探尋人性之美的生命源泉,但由于家庭環境、文化背景的差異,注定了彼此的人生視域及創作角度的不同。在凌叔華的筆下,女性、兒童、自然構建起了人性理念的三位一體,作者以富有同情心的眼光來看待她作品中的人與事,不自覺地表現出愛與憐憫。正如夏志清所言:“作為一個敏銳的觀察者,觀察在一個過渡時期中國婦女的挫折與悲慘遭遇,她卻是不亞于任何作家的。”凌叔華用她那雋秀精致的筆觸為讀者構建了一個民國時期的“女兒國”,里面既住著天真無邪的小女孩枝兒(《鳳凰》),又有慈祥溫厚的老太太章老太(《有福氣的人》),更多的是二三十歲的青春少婦,她們有的是舊式貴族家庭的太太(《太太》),有的是新時代的知識女性(《綺霞》),還有的是來自于社會底層的貧苦婦女(《奶媽》)。在這個全由女性構成的大觀園中,女子經歷“成長——學習——戀愛——工作——結婚——生子”等人生軌跡,女性身份職責在不停變化,原本溫順柔婉的性格變得絮絮叨叨(《中秋晚》),活潑可愛的天性被瑣屑生活碾碎(《小劉》),但無一例外均淪為婚姻家庭的犧牲品。舊的家庭生活消磨掉女性的銳氣,毀壞了女性的青春,腐蝕著女性的靈魂。凌叔華平靜地觀察著高墻內女性的喜怒哀樂,將其訴諸于筆端,又讓自己置身于高墻之外。她冷靜客觀地將自己最為熟稔的家庭一角展示給眾人看,并不試圖去探討“娜拉”出走后的人生軌跡,只是如實地描摹出女性焦躁、無奈、壓抑、自我沉淪的內心世界。
凌叔華也喜歡用兒童視角來觀察成人復雜多變的生活。因為“兒童能夠揭示腐敗、不公和社會暴力,因為他在兒童的外衣之下,不像成人那樣要負社會責任。”凌叔華在《弟弟》中描繪了一個天真活潑、爛漫無邪的少年形象。他因自己不經意暴露二姐的心事而傷心不已,而打著“好朋友”的幌子,誘哄弟弟說出秘密的林先生搖身一變,成為弟弟的“二姐夫”,這一諷刺性的對比描寫,將成人的虛偽世故和兒童的正直善良全部披露在世人眼前。而以作者親身經歷為藍本的《古韻》一書,試圖以“我”和兄弟姐妹們組成的天真美好的童心世界,去反襯由父親、母親、姨太太、丫鬟們等組成的成人世界的虛偽殘酷,欲以至美至善的童真來拯救人性的缺失。凌叔華力圖以成人的世故凸顯孩子的天真、對生命的赤誠,以此來營造一個天真爛漫、情趣盎然的兒童世界。在凌叔華的眼里,兒童都是“心窩上的安琪兒”,他們天真稚嫩,寬容友愛,絲毫沒受世俗玷污。譬如《搬家》中枝兒對花母雞的不舍,《小哥兒倆》中大乖、二乖兩兄弟對八哥、野貓的喜愛,《鳳凰》中枝兒對人毫無成見的信賴,孩子身上的淳樸、憨厚、純潔、友愛的天性可見一斑。在這樣的天性面前,即使是抱著民族成見的日本少女千代子,也不忍心為難抱著幼兒前來沐浴的中國小腳婦女(《千代子》)。凌叔華試圖通過對兒童的質樸天性的發掘,來喚醒被禁錮、被異化的人性,這種寫作方式豐富了京派對人性的表現形態。
凌叔華以詩人的心境與自然相通,用畫家的眼光去捕捉山水之美,因此,凌叔華小說中的大自然還特別富有繪畫美、詩意美。舉《倪云林》中一段為例:“其實一樣是蔚藍天空,罩在郊外,便自不同。目前一片黃碧渲烘停勻的曠野,嵌上空明清澈的溪流,幾座疏林后有淡施青黛彎彎的遠山黏著。”視線高低起伏,層次遠近分明,色彩豐富和諧,意境恬淡悠遠,充分顯示了作者那小說家兼畫家、詩人的藝術氣質。
具體來說,在繪畫上“繼承元明諸大家”的凌叔華,在文學創作中運用畫家的審美眼光去捕捉日常生活之美,將繪畫的結構布局,寫意傳情運用到文學創作中,使文學創作與繪畫藝術相互通融,形成文畫合一、文中有畫的境界。她對繪畫取材角度、空間藝術、素描手法、斑斕色彩的借鑒,營造出不同于其他京派作家的小說意境。凌叔華的小說創作從繪畫中借鑒的第一個技巧便是從不同視角來選材取景,正如凌叔華自己所言:“我看每一事件都可以由多方面看去,像繪畫的人,繪一個花瓶,因各方光影的變化不同,繪出來便不得一樣,雖然花瓶就只那一個。”凌叔華的《女人》、《她們的她》是對同一內容的不同寫法;《說有這么一回事》是改寫了楊振聲的《她為什么發瘋了》,涉及“同性”題材,細致交代了主人公曼影因被戀人云羅背叛導致發瘋的事實;《一個故事》是作者聽幾個人口述同一起桃色糾紛,在誰對誰錯方面,有了“羅生門”的效果,性別、年齡、職業、價值觀的差異,使每個人在講述故事時都站在有利于自己的視角,“事實夾理論幫忙”,“加油加醋的講下去”,沒有統一的是非標準。凌叔華的小說在結構方面借鑒了繪畫中的空間藝術。她在創作中盡量地淡化故事情節,僅僅截取生活中的一兩幀畫面,再用細節的顯微鏡將其清晰描繪,突破了傳統小說中的線性敘事模式。凌叔華在創作中尤其喜歡將兩種前后對應的場景進行空間對比,《繡枕》時間跨越兩年,但作者僅僅通過“繡枕”與“看枕”的不同場景對比,就將女性被男性文化體制主宰的悲涼命運表現得淋漓盡致。《女兒身世太凄涼》在結構上也是兩段式,以一年的時間為分界點,通過婉蘭“待嫁”與“歸寧”的場面對比,揭示出舊式女子命不由己的悲慘事實。
凌叔華在創作時也非常注重人物的心理寫實,以此引發讀者共鳴。在凌叔華的筆下,男女主人公的心扉之門是牢牢緊閉的,只是偶爾趁著酒意微醺之時,才能回歸自我,直面內心大膽而隱秘的欲望(《酒后》)。在大部分時候,作者均是巧妙運用對話、獨語、寫信、自傳、意識流等方式,去揭露人物內心深處的真實情感。在凌叔華看來,只有女人才能真正了解女人,男子或耽于事業(《春天》),或逃避家庭(《太太》),對女性內心的需求不聞不問,女人只能從同性那里去尋找關愛,獲取同情,凌叔華的同性戀題材小說《說有這么一回事》展示的就是這么一種落寞孤寂之情。詩人兼畫家的凌叔華喜歡在敘事中插入景物描寫,借助中國傳統式的景物意象來隱喻人物的內心世界,以環境渲染來捕捉來人物的隱秘心理。在《瘋了的詩人》中,詩意的自然環境與人物的心理形成一種客觀關聯,小說主人公的心理意識隨景物而發生變化。文章開篇以連綿細雨來映襯覺生的愁緒萬千,待至后面云收雨散,雨后初霽,詩人最初的悵惘之情也煙消云散,心情趨暖。凌叔華在創作中極其看重作品的情節結構,旨在通過起伏不定的情節來表現人物思想情感的變化,以情節凸顯情緒。如《花之寺》中背著妻子出游的幽泉,隨著情節的一波三折而經歷了欣喜、驚奇、失望、焦灼、驚愕、羞愧等六種情緒的變化。在《他們的一日》中,隨著離別的腳步越來越近,筱和的心緒也愈加焦躁,回想起相聚時的甜蜜,幻想著別離后的孤寂,女主角的患得患失在離別的情節中彰顯無遺。
沈從文在評論凌叔華小說創作時說:“使習見的事,習見的人,無時無地不發生的糾紛,凝靜的觀察,平淡的寫去,顯示人物‘心靈的悲劇’或‘心靈的戰爭’,在中國女作家中,叔華寫出了另外一種創作。”在30年代的中國,作家們還在遵循著現實主義的寫作原則,很少有人去挖掘人物的心理狀態或人物之間復雜的關系。凌叔華以女性特有的細膩敏感,努力探索著自己筆下人物的內心世界,運用多種手法進行傳達,在意識深層的開掘方面為京派作出了獨特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