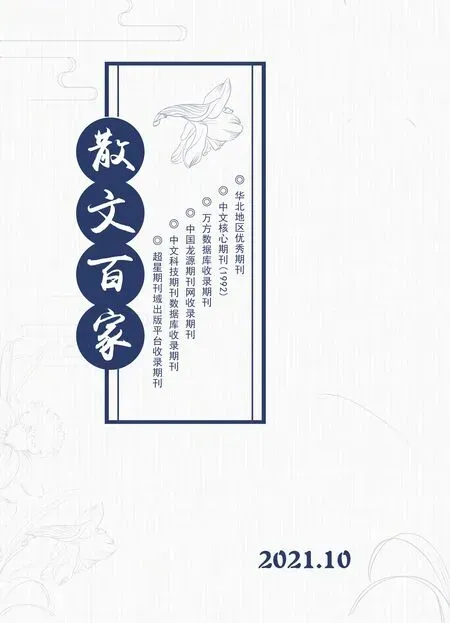重慶民間故事的美學意蘊及兒童美育功能研究
王雪佩
重慶幼兒師范高等專科學校
民間故事是人民創作并傳播、具有假想(或虛構)的內容和散文形式的口頭文學作品,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個地區的文化氣質。重慶因特殊的地理環境、生活方式等因素,造就了敘事多樣、情節曲折的重慶民間故事。這些故事承載著西南地區的風情,滲透著巴渝人民獨特的審美。“美是積淀了社會內容的自然形式”,對重慶民間故事進行美學的剖析,可以展現當地文化傳統和風俗習慣所隱含的美學意蘊。同時借民間故事的美學意蘊提高幼兒對美好事物的鑒賞感知能力,從而浸潤心靈,得到美的熏陶。
一、重慶民間故事的美學意蘊
“藝術美的要素可分為二,一種是內在的,即內容,一種是外在的,即形式。外在形式的價值就在指引向內容,顯現出意蘊”。重慶民間故事表現出重慶勞動人民內在的情感、信仰與精神價值,體現了內在意蘊美和外在形式美的統一。
1.內在意蘊美。
(1)和諧之美。“對和諧之美的追求是人類的本能”。重慶民間故事中的鳥木蟲魚、一餐一食的生活,都浸潤著這種“和諧美”。
重慶民間故事中有大量關于動物的情節設計,如《白龍過江》《白馬泉》《逐鹿得泉》等,故事中龍、馬、鹿等動物大多具有靈性且神通廣大,無論這些動物性善或性惡,都能與人類和諧共存。故事《銅梁舞龍》所描述的原始人類生存艱難,有妖魔鬼怪肆虐人間。于是女媧便造出兩條巨龍,保護人類繁衍生息。銅梁人民為了回報巨龍的恩德,每到年關都要扎龍祭祀,逐漸形成了民間早期的祭祀兼娛樂的舞龍活動。這個故事中的妖魔鬼怪暗指自然界的磨難和險阻,而巨龍的與之相抗衡,其實是民間勞動人民的希望與自然界和諧共存的審美心理。
重慶勞動人民最初看到高山峻嶺、奇異天象,以其有限的認知,認為是大自然某種神秘力量創造出來的,故賦予其生命,如神奇的“映月洞”,突冒甘泉的“女兒井”,險峻的“天生三橋”等。這些都反映了重慶勞動人民與自然界和諧共存的心理。
(2)崇高之美。渝地百姓在其成長過程中,敢于與社會不公抗爭,敢于和代表神秘力量的神仙、靈獸、自然災害做頑強的斗爭,形成了艱苦奮斗、頑強剛毅的性格,從而構成了重慶民間故事堅韌、奮進、宏大的崇高之美。如《火神廟》《鴨子龍傳說》《犀牛堡的故事》等均體現了勞動人民對抗自然神力、災難的不屈精神。
其中《縉云山的由來》的故事最具代表性。縉云山遠古時叫巴山,居住巴族和賨族鏈兩個勤勞的氏族。巴山有一條神奇的山泉,喝了它不長瘡,可以長命百歲。當時的皇帝想要霸占此山泉,便派殘暴的縉云氏和高新氏奪取山泉,巴氏和賨族奮起抵抗,最后只剩下九位勇士誓死抵抗,化為九座山峰擋住敵人的去路。自此,巴山的云彩早晚呈赤色,九勇士的英雄就義形象使我們肅然起敬。魯迅說:“悲劇是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故事中的矛盾沖突以及悲劇性的表現,使人產生深沉的情感共鳴和心靈震撼,引發人們深層次的審美心理體驗。
從生命意識角度來說,重慶民間故事里崇高美的深刻內涵在于勞動人民追求不朽和永恒的成長歷程,向無限的事業不斷奮進的狀態和境界。
2.外在形式美。
(1)語言之美。重慶民間故事中運用了大量的當地土詞俗語,如《涪陵大東門神仙口》中的“幺妹”(指家中最小的妹妹,又可指對小姑娘的稱呼),《破山和尚氣死趙財主》中的“夾森”(小氣、吝嗇),《白鶴梁的由來》中的“嘿個”(非常)等詞語。重慶民間故事也習慣用疊詞來抒發情感,如《金盆寺的故事》“叫花子女人在包包頭東摸一哈”,《涪江寺廟事件》“看到有黑(很)多人在涪江邊邊哭”,《魚復縣為何改名奉節縣的故事》出現“嚇得腳打閃閃”(形容渾身發抖),《熊嘎婆》反復出現“粑粑”(在重慶地區泛指餅類食物,如糯米粑粑等),《大佛寺》出現的“驚爪爪”(吃驚)等出現大量的疊詞。
土詞俗語和疊詞的出現,展現了原始人民的心理氣質,豐富了方言民間故事的語言表達,增添了民間故事的風情美。
(2)敘事之美。重慶民間故事集合了人、神、精靈、妖怪等群體,在敘事上打破時空的限制,現在和未來對話,人與其他族群相戀等,極具魔幻色彩,賦予重慶民間故事敘事之美。敘事模式有兩種最為突出:對比和是插入。
對比敘事來推動矛盾沖突。故事中同時出現真善美、假惡丑,并隨著情節的推動沖突加劇,結局是高尚戰勝卑劣,達到宣傳教育的目的。如《麻雀報恩》中對老大和老二形象的丑惡和善良,行為的高尚和卑劣做了對比,最終使善人善報,惡人惡報。這種二元對比更符合人們的道德要求,更能體現訓誡的意義。
插入敘事是指在大故事套小故事。在《江津米花糖的百年故事》中插入“陳氏二兄弟的故事”,《雙桂堂的由來》也加入了“嫦娥種桂樹”的故事。這種表達方式的出現“帶有民間故事口頭流傳向書面文學過渡的痕跡”,故事套故事的敘事方法,有追根溯源之意,增加了故事的真實性。
二、重慶民間故事的兒童美育功能
美育就是審美教育,即通過培養人們對美好事物的鑒賞、感知能力,從而浸潤心靈,得到美的熏陶。“兒童美育應該是根據兒童生理、心理特征,培養形成健全的、協調的審美心理結構,通過促進兒童的審美發展來促進兒童豐富完整的個性。”應站在兒童視角進行的審美教育,發展兒童的審美感知和情感體驗,達到輔德和益智的目的。
“一則神話,可以堅固全團體的協同心;一首歌謠,能喚起大部分人的美感;一句諺語,能阻止許多人的犯罪行為。在文化未開或半開化的民眾當中,民間文學所盡的社會教育的功能,說來是使人驚異的。”重慶民間故事是兒童美育的重要資源,在人們口頭傳誦中,能培養兒童的審美想象力,提高審美感受力、增進審美創造力。在美育過程中,兒童懂得何者為美,何者為丑,從小養成良好的品質。
1.培養兒童審美想象力。
想象力是兒童的天賦和本能,在聽、讀重慶民間故事過程中,兒童能得到審美想象力的培養。
精靈鬼怪、山川風物、等自然界的力量充滿了人的主觀意識,變成“人化的自然”。如重慶璧山地區廣為流傳的《茅萊仙女的故事》的故事,茅萊山有一個窮漢王丘,最大的夢想是有一雙鞋子,于是茅萊山仙女便托夢給王丘半夜一人去茅萊山洞口拿一雙鞋,并囑托要保密,但是拿到鞋后的王丘一時嘴快,泄露機密,惹得仙女生氣,從此王丘再也沒有新鞋穿。《小公雞》故事里,小公雞輕信花言巧語,給狐貍開了門。第一、二次幸好有個狗哥哥鄰居仗義出手,解救于危難之中,被救了的小公雞并沒有吃一塹長一智,第三次被抓丟掉了性命。整個故事情節緊湊,使用回環往復的敘述方式,重復的敘述中又顯示出細小的差別,教師和家長在講述過程中可以引導小朋友猜猜小公雞每次的遭遇如何,在故事中鍛煉小朋友的想象和思維能力。
重慶民間故事里以眾多的形象構成兒童審美的想象世界,如巨龍大戰惡魔的英勇勝利(《銅梁舞龍》);把錢和饅頭放進去可以再生的金盆(《金盆寺的故事》);龍王流落人間,被母女所救,為二人留下泉眼(《女兒井》)等,無不是以特定的想象方式,迎合兒童的心理發展特點,為其提供了想象的源泉。
2.培養兒童審美感受力。
重慶民間故事將生活中較粗糙、分散、處于自然形態的美的事物,形象地提煉為更強烈、更豐滿、更典型的藝術美,籍此影響兒童的感情,陶冶和培養兒童的生活情趣,發展他們的欣賞能力,加深他們對現實中美的感受和領悟。
故事《巴蔓子刎首留城》,據《華陽國志》記載:“周之季世,巴國有亂,將軍蔓子請師于楚,許以三城。楚王救巴,巴國既寧,楚使請城。蔓子曰:‘籍楚之靈,克弭禍難,誠許楚王城,將吾頭往謝之,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頭授楚使。楚王嘆曰:‘使吾得臣若蔓子,用城何為!’乃以上卿之禮葬其頭。巴國葬其身,亦以上卿禮。”巴蔓子以頭留城、忠信兩全的故事,成為了巴渝大地傳頌千古的英雄壯歌。
《巴蔓子刎首留城》因為成功塑造了巴蔓子這位巴渝經典形象而具有豐厚的審美意蘊。巴蔓子形象具有悲壯美的意味,他刎首留城行為所展現的非凡膽略和巨大氣魄,具有震撼人心的美感,進而引起審美者的贊嘆和歌頌。巴蔓子以其自身強大的人格魅力,成為家喻戶曉的典型,能引起兒童存于潛意識層次的英雄情感、感受到崇高的人格美,引起審美共鳴。
3.培養兒童審美創造力。
審美創造力是指兒童按照美的規律,綜合調動想象、情感、思維等因素,創造性地表現美和展示美。通過重慶民間故事的學習,兒童將所聽、所想呈現出來,表達自己對美的初步認識,審美創造力得到了提高。
重慶民間故事皆由民間勞動人民創作,故事的內容就地取材、與現實生活息息相關。就故事本身而言,對兒童來說更易理解,故事的簡易性和寫實性更容易激發兒童的創作熱情。再加上重慶民間故事中有大量動物形象、仙女想象、山怪精靈和擬人化的植物等,此類種種更容易激發兒童創作的欲望。兒童思維活躍,想法奇特,富有很強的創造力,因此,讓兒童積極參與其中,聽、讀更多的重慶民間故事,不僅可以拓展其思維能力,更能激發他們的審美創造力。
重慶民間故事是我國傳統文化中寶貴的資源,重慶民間故事又將藝術融入生活。不僅具有豐富的文化意蘊,而且語言通俗淺顯、幽默詼諧,具有濃厚的川渝區域特色,傳達出人民生活的追求與情趣。流傳過程中又向兒童傳遞了美的思想和教育,起到了潤物細無聲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