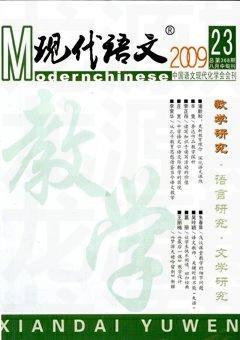先聲奪人譜華章
情境導入,恰如一曲交響樂的序曲,先聲奪人,華章溢彩。一部好作品,如果有一個美妙的情境導入,會將作品的魅力演繹得更加精彩。如若哪位教師,能營造一種情境,你也將在學生心中倩影永恒。展示你那美妙的導入,散發你的光彩,任文學作品飛翔,使讀者沉浸其中。
一、情境導入概述
常言說得好,響鼓還需槌來敲。倘若說一節課是響鼓,那導語則是重槌的第一響。它渾厚激越,聲聲擊到學生的心,碰撞出智慧的火花,消除其它學科的延續思維或心理雜念的干擾,使其注意力迅速集中,饒有興趣地投入到作品中。語文教師則應該花心思,使一堂課有一個充滿魅力的開場。那么,什么是情境導入呢?它是指教師借助一定的教學手段,創設出能夠激發學生的想象力或引發學生相應情感體驗的情境,使學生在欣賞或情緒感染中就勢轉入課文學習的一種導課方式。
二、情境導入的方法和手段
作品之情境導入,意在能夠使讀者迅即進入作品,感覺與領悟作品的內涵。一部文學作品,其語言華麗辭達,再輔以一個精妙絕倫的引入,將如虎添翼。情境導入法,是根據教學內容的需要,創設一定的情境,讓讀者在教師的引領下,悄悄地、不知不覺地進入主題。它直觀、形象,容易激發學生的興趣。它是一種極能引人入勝的方法,自然、恰當、精彩的導入情境,能立刻集中學生的注意,引發其興趣,給他們以一個富有啟發性的廣闊思維空間,使其產生強烈的好奇心與旺盛的求知欲,從而開展積極的思維,在最后的狀態中主動地進入作品學習。
1.懸念導入
蘇霍姆林斯基說:“如果教師不想辦法使學生產生情緒高昂和智力振奮的內心狀態,就急于傳授知識,不動情感的腦力勞動,就會帶來疲倦。”而懸念就是一種急切期待的心理狀態,它具有強烈的誘惑力,能激起探索、追求的濃厚興趣。因此,要巧用互聯網“信息容量大,查取資料快,圖文并茂”的優點,創設懸念導入新作品,引起學生的驚奇、疑惑和新鮮感,從而激發他們主動探索問題的動機,給課堂增添無窮的魅力。
在教學《論求知》時,導入設計是這樣的:鈴聲響了,筆者先把一只空口袋用手提起來,然后往講臺上連放幾次,口袋攤在桌面上。而后,給口袋裝滿了書,再一放,它便端正地立著。此時,問:見后有什么想法?請你用最簡潔的文字把自己的感想說出來。
有的學生說:空無一物的袋子是難以站得直的。
也有的說:一個人要自立,必須有豐富的知識。
在他們認為筆者接著要講道理時,筆者卻只是片刻停留,請他們自己思考。然后,話鋒一轉,提出又一問題:你想獲得知識嗎?獲得知識都有哪些方法?請你閱讀本文,看看作者是如何說的。
這樣,通過教師精心設計,學生的認知發生了沖突,進而導致期待和探索的產生。學生急于尋求答案,閱讀作品的積極性大為高漲,因而達到了創設懸念的效果。
2.歌曲導入
歌曲,具有較強的文學性、音樂性與易傳播之特點。好歌,極具審美價值,能愉悅性情、激發靈感與志趣,陶冶情操。
歌曲導入,能夠創設良好的情境。一堂新課,一部作品,恰到好處地引用它,興趣、情味別具一番。目的意在激發興趣,引導其打開思路,幫助其理解作品內容;而且它們大多具有美好的意境、優美的旋律和歌詞,極其適合青年學生播放、吟唱。引用歌詞導入,能夠創設良好的情境,調動他們的情感,激發學習的興趣,使他們快速地進入作品的氛圍之中。
在學習《愚公移山》時,播放MTV欣賞曲,使學生對愚公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從而激發其情。當教室里出現那優美、鏗鏘的旋律,“聽起來是奇聞,講起來是笑談,但憑那扁擔把脊梁壓彎”;當屏幕上出現一位古代老人“望望頭上天外天,面對著王屋與太行,憑著是一身肝膽”那神情堅毅的特寫畫面時,學生仿佛置身于遠古時代,真切地感受他的堅毅,很快進入學習狀態。
歌曲導入時,老師應該致力指導。先應定向,在播放樂曲前,給一個目標。如欣賞樂曲的旋律,體會其中的意境,使之有意識地進行審美活動。再則要啟發,及時啟發,使其深入理解樂曲的意蘊。老師輔以樂曲旁白,促進理解。再次,要銜接自然,事先要精心設計好過渡的環節,如注意設計好提問以及展開問題,使之自然而然地導入新課的教學。
3.古詩詞導入
我國古典文學博大精深、文采斐然。恰當地將古詩導入作品,極為“大氣”。它極具磁力,含蓄雋永,回味久遠。教師宜熟讀作品,采擷作品精華,回首古代文化,讓學生產生聯想。如由《黃河頌》聯想到李白《將進酒》,“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
4.對聯導入
對聯是我國的傳統文化之一。學生知之不多,然而都希望學習,并且能夠運用。倘若我們能夠抓住這一求知欲望,進行恰當地引導,效果非凡。如:苦不苦,想想父母田野苦;累不累,憶憶北大清華輩。
5.合樂朗讀導入
音樂有優美的旋律,更有美好的意境。配上樂曲來朗讀進行導入,可以營造情境,使學生很快進入角色,課堂活躍,心情愉悅,能夠提高注意力,有助于理解作品內容。
語文教學綜合性的特點,決定了課堂方法的多樣性。導入的設計不能刻板單一,宜花樣翻新,多姿多彩。在作品導語設計上,還有溫故導入、審題導入、圖示導入、提示問題導入、提煉觀點導入、介紹導入、針對語病導入、點出人物導入、敘述故事導入等等。
三、結語
我們呼喚的導語設計,應為作品的教學目的與重點服務,與作品的內容自然銜接。具體來說,好的導語,攫住了學生的心,是教師與學生互動的橋梁,它既能夠引起學生的興趣,又能激發學生的求知欲望,為一堂課創設一個良好的開頭,會使教學的雙邊活動生動、活潑、自然,切實提高教學的實效性。
參考文獻:
[1]尹祖琴.語文課堂教學有效性研究[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
[2]金玲.語文教學中的情境創設[J].內蒙古教育,2008,(24).
[3]李秀偉.喚醒情感——情境體驗教學研究[M].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7.
(胡耀文 河北省固安縣東灣中學065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