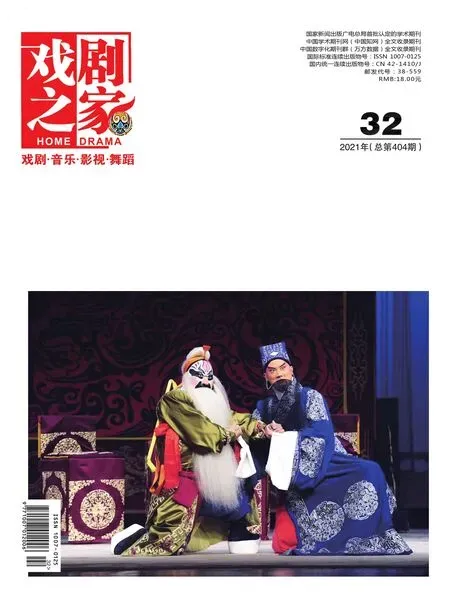淺析戲曲舞臺平臺的運用
周 鵬
(湖北省戲曲藝術劇院 湖北 武漢 430000)
中國戲曲最早生長于民間,它起源于原始歌舞,是一種歷史悠久的綜合舞臺藝術樣式。經過漢、唐到宋、金才形成比較完整的戲曲藝術。梨園名伶們化上濃墨重彩的妝容,穿上絢麗多彩的服飾,或激越高昂,或妙喉婉轉,在舞臺方寸之間載歌載舞地上演人間百態,按照學者王國維的話來說,即“謂以歌舞演故事也”。
由于受到演出環境以及技術手段的限制,傳統戲曲初時只有一個小小的被稱為“守舊”的刺繡帷幕作為背景,左名“出將”,右曰“入相”,作為戲曲演員上場和下場的通道。前方的表演區域,只采用“一桌二椅”作為傳統戲曲舞臺上的演出用具,視劇目情景的需要可多可少,可分可合。這“一桌二椅”在作為桌椅本體出現在宮廷府衙、中堂閨房之余,又可作為山水樓臺的代用物。通過演員的各種表演和不同的擺設方式,對劇情的地點和人物關系進行表現和暗示。傳統戲曲表現角色人物的活動場所和環境僅憑“一桌二椅”即可,利用極簡單的道具表示出形形色色的環境和場合。“一桌二椅”可以表示宮廷禁院,可以表示軍帳將臺,可以表示亭臺樓閣,可以表示土丘山岡,可以表示房門圍墻,大凡劇中角色所在客觀環境都可包括在“一桌二椅”之內。其擺設方式繁多,如大座、小座、八字桌、三堂桌、騎馬桌、門椅、站椅、倒椅、大高臺、小高臺、帥帳、樓帳、床帳等。這些擺設方式,因長期演出積累而成為基本程式,可根據不同劇目的表演靈活掌握。
上述表現方式主要是通過劇中人物的裝扮、唱腔和對白的內容,以及人物圍繞其造型所展現出來的動作來表現,觀眾再加以聯想和感悟,方能淋漓盡致地體現其豐富內涵:“外桌內椅”大多表示宮廷、衙署、軍帳等,用于上朝斷案、發號施令等具有上下級關系的人物場景;“內桌外椅”大多表示閨房、中堂、大廳等,用于訪友、對酌、拜壽等人物場景;將椅背對向觀眾也表示門,如《紅鬃烈馬》中“武家坡進窯”一折,而在其后再放一把椅子又可以變為織布機,如《三娘教子》中“教子”一折;一張桌子可以代表山岡,也可以表示床榻,斜放又可以表示圍墻如《狀元印》中“馬跳圍墻”一折;一張桌子在同一劇中時而表示床榻,時而表示桌子,如《三岔口》中“打店”一折;一把椅子放在并列的桌子上就可以看作點將臺,如《失街亭》的諸葛亮;兩椅相對支起一個帳子,代表臥室床榻,如《文昭關》的伍子胥;兩椅相對,中間或后面放桌子,人物站在上面就表示樓閣,如《望兒樓》中竇太真登樓盼子;兩桌兩椅相對表示宴會,如《鍘美案》中陳世美侯爺與相爺講宮;如果增至三桌多椅則表示盛大宴會或重要庭審,如《群英會》中群雄戲蔣干等。值得一提的是,“一桌二椅”有專門的桌幃椅披,不同的顏色、花紋、圖案,代表著不同的人物身份和場景環境,黃色的桌幃椅披代表著皇家威嚴,粉色繡花的表示待字閨中,藍色無花的指向一貧如洗……這大概可以看作戲曲對于布景平臺最原始的意象化使用方式,它的這種使用方式脫胎于中國傳統藝術寫意的藝術理念,彰顯前人高雅的格調和不羈的浪漫。
隨著演出技術的進步,三面圍觀的伸出式傳統戲臺逐步過渡到更為縱深,舞臺畫面造型更完整的鏡框式舞臺,這一轉變凈化了舞臺畫面,促進了舞臺布景技術的發展。在步入更高級的演出殿堂之后,單純的底幕布景已經無法滿足更寬闊的演出空間的需求,藝術創作上要求能夠提供更多的實物支點來促進舞臺動作的展開,因而立體布景更多地被采用。而當代舞臺設計對于國外戲劇思想的反思和借鑒,讓不同劇種間產生橫向借鑒,同時使布景的樣式呈現出多樣化的傾向,傳統戲曲中出現話劇的表現手法,而話劇中也融入了歌舞以及戲曲的成分。于是最早出現在話劇、歌劇舞臺中帶有寫實主義的平臺裝置以及設計被帶入戲曲舞臺。
現今國內戲曲舞臺創作按照題材大略分為兩類,即秉承傳統的古裝戲和推陳出新的現代戲,二者在表達內涵、劇本結構和導演構思上都不盡相同,對不同題材的理解引發了舞美設計師對戲劇空間結構的不同分析,而這種分析讓設計師重新解構了戲劇空間的各種要素,從而明確舞臺上平臺在創造不同空間時所具有的不同功能。
傳統戲曲是在傳統文化氛圍之中創造出來的,符合古典審美觀,猶如中國畫之寫意,運用了“取其意而棄其形”的方式。在具體的表現形式上,采用“以動代靜,以聲傳形”的虛擬性動作,進行象征性的虛處理。基于傳統戲曲的這一特點,平臺的介入導致傳統戲演員很多程式化的動作無法施展,身著傳統戲曲中的高底靴在起伏的平臺上無法自如行走;平臺帶有傾斜的坡度使得演員在表演身段時需要額外注意平衡性等。由于上述諸多問題,因此我個人在傳統戲曲的舞美設計中,盡量保持舞臺的原始平整度,以盡量不影響到演員的表演為原則,慎用平臺,點到為止。
例如我有幸參與設計的花鼓戲《秦香蓮》就是一部典型的傳統戲曲。該劇由傳統劇目《鍘美案》改編而成,由于編劇和導演把原來的主角陳世美和包公之間的矛盾沖突重心轉移到了秦香蓮這個角色身上,所以戲名改為《秦香蓮》。劇中我利用幾塊小型幾何平臺的移動,在后區組織幻化為客棧門、廟壇、公堂,在不影響演員在主要表演區的圓場、身段表演的同時,與傳統戲曲“一桌二椅”的寫意擺場手法呈現出了異曲同工之妙。特別在“講宮”一場,我重新解構了舞臺布局。秦香蓮由偏下場門邊的斜座位置調整到中場。為了突出主角,我使用兩塊活動平臺在中后區搭建了一個區域,兩側飾以欄桿,模擬駙馬府后院小戲臺的氛圍,秦香蓮就穩穩地端坐在這個平臺上,完成一段核心經典唱段的演唱。這一做法在舞臺構圖上強化主角的視覺信息,把重要的支點形象放到了顯著的位置,輔以局部光區的提亮,突出了秦香蓮的主體形象和扮演者的主要演區。這一處理得到了創作組的認可,讓導演可以給予主角一個在正中間最優勢的位置演唱核心唱段的支點。同時,這個平臺的設置在第三道邊沿幕偏后的位置,前面預留6-7 米表演區,不影響相爺、王爺來訪以及與陳世美之間相互的走位。而我又在第三道邊沿幕后掛起蝴蝶幕,飾以屏風,讓這組平臺融入舞臺的整體,使得舞臺形象得以合理組織,設計元素呈現出統一的秩序,并與表演達到一種協調,使整臺戲的視覺因素形成一個統一的結構體。
而近幾年的現代戲戲曲創作,大多都是響應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號召,著眼平民視角,圍繞農村題材,反映諸如新農村建設、精準扶貧、平凡好人等主題,題材決定了表演場景大多為村屋鄉所、田間地頭等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區域,如果沿用傳統美學意象性的表達,未免不接地氣;同時,現代戲題材由于貼近生活,貼近老百姓,所以程式化的表演大大減少,因此對于平臺可以合理、適當地調整使用面積和使用方式。
我參與設計的現代題材楚劇《澴河村的故事》,描繪的是年輕的扶貧干部深入基層,利用自己的智慧和熱情改變鄉村落后面貌的故事。基于劇本設定,我設計了一組多向斜坡平臺,利用參差不齊、崎嶇難行的斜坡模擬落后的舊農村鄉間起伏的小道,再以少量的植物、破舊的墻片、簡陋的房片等裝飾其間,模擬了急需我黨扶貧干部去改變的舊農村的原始面貌。這組平臺雖然體量相對較大,但是由于劇情的需要,演員程式化的表演被生活化的動作取代,起伏的平臺對表演沒有造成太大的影響,反而讓演員的動作更貼近生活。同時,平臺很好地承載了燈光的效果,側橋和反打的電腦燈光在起伏的斜坡上產生了奇妙的組合效果,極大地豐富了舞臺效果,立體的平臺增強了表演的動作性及雕塑感,生動地創造了角色動作空間,對于演員們飾演的角色起到了很好的烘托作用。劇中的老酒鬼趁著夜色偷了鄰居的雞,跑到荒郊野外,用散落的石塊架起一個火堆烤雞吃,設計制作的石塊在起伏的平臺上毫不突兀,角色人物周圍放置幾棵小樹和一個破草棚,燈光模擬的月光將樹影投射在平臺上,映襯著背景的夏夜星空,形成統一的畫面,環境氛圍感十足。在這樣的環境下,角色人物與劇本的內在精神高度融合,演員的角色完成度極高。這個戲還有個小插曲,由于劇場條件限制,沒有吊桿可供搶景換場,我在前區正面斜坡平臺和后區通欄斜坡平臺間預留了十公分的間隙,搶景時將所需的房片嵌入其中,在不影響美觀的同時解決了沒有吊桿的困擾,提升了搶景效率,保證了劇目的完美呈現。
戲曲舞臺設計是一種包含多種因素的綜合概念,它提供的是圍繞著演員讓其展開動作的一切物的造型,其任務就是根據演出文本的情感、情緒、情景需要,創造一個特定的戲劇空間。由于戲劇演出是由活動的演員扮演著虛構世界的角色在立體的空間中進行,所以演員活動的位置隨著角色所處環境的更替而變化無窮。而平臺在戲劇演出中總是以某種形式呈現于舞臺空間,它可以引導觀眾的眼睛追逐著戲劇動作的展開。因而當我們在研究戲劇舞臺的結構元素時,總能發現這些所謂的結構充斥在舞臺的每一個角落。
戲曲舞臺設計是需要感性思維和邏輯判斷高度集中和統一的系統工程,構思時需要豐富的想象力,實施時又需要注意繁復細節。而平臺作為創作中的一種技術手段,首先它不能是一個獨立存在的個體,即為了存在而存在,它應該參與到劇情中來,和劇中人物產生互動,這一點是裝置存在的基點。然后就是要運用得協調、舒服、適當、得體,這一點是不容易的,如何運用需要從劇本內容出發,從導演構思出發,從劇種的特色出發去量體裁衣。用到實處,它就是真實生活的寫照,用到虛處,它能代表大千世界,寫實與寫意的關鍵在于“分寸”的掌握,“實到何處?虛有幾分?”,如何使其“簡而不陋,少而豐滿,延長有機,連續呼應”是難度所在。在這些方面,我也只是一個正在戲曲舞臺設計道路上默默探索的學習者,還需要不斷地學習和摸索,才能取得更多的收獲。限于學識和視野,上述有不到之處,懇請各位師長同行予以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