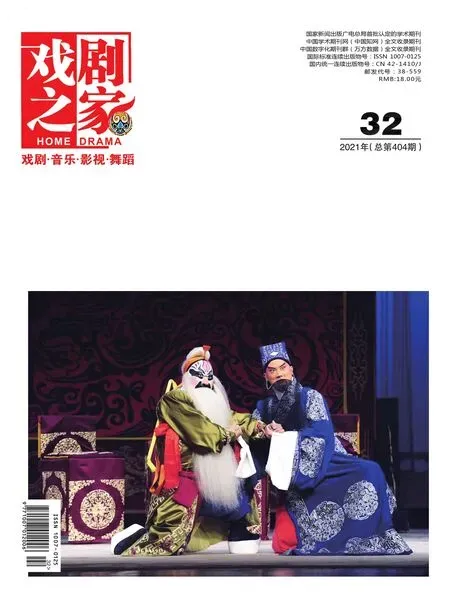超現實主義電影《一條安達魯狗》的符號學分析
陸 方,高元祺
(大連大學 美術學院,遼寧 大連 116622)
1928 年,路易斯·布努埃爾曾與西班牙畫家薩爾瓦多·達利共同創作了他的第一部短片《一條安達魯狗》。針對這部作品的名稱,達利曾在自己的書中寫道,“安達盧西亞的狗”含有“媽媽的寶貝”這一含義。這一解釋結合影片所包含的俄狄浦斯式的內容便不難理解。但布努埃爾也曾對此解釋,自己只是為了給電影取一個怪名字。此外,兩位作者還曾宣稱這部影片的靈感來源于兩個夢境,并且在拍攝時遵循著“不要可能得出任何理性的、心理的和文化的解釋的任何思想,以及任何形象,除了令人震驚的畫面,別的都不要。”顯然這只是作者一種“偏激”的回應,并不代表作品本身僅僅是夢境的純粹再現。影片作為布努埃爾的處女作以及達利跨界參與完成的一部作品,在當時就引起了巨大的轟動,并且對電影美學的審美傾向、剪輯手法等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甚至可以說,影片本身已成為了一個“符號”。因此,對這部影片中的視覺元素以及聽覺元素進行符號學分析是非常有意義的。
影片的開場,伴隨著節奏歡快的音樂,一個男子正在磨著剃刀,神情似乎有些焦急。他抬頭望向天空,烏云和月亮交錯,走進屋內割開了女子的眼球,音樂的節奏也急轉直下,變為重重敲在鋼琴上的低音音效。這里使用剪輯手法,在準備割開的動作和下一個割開牛的眼球的畫面中插入了一個畫面:一道狹長的烏云劃過潔白的滿月。這一幕堪稱心理和視覺上同步的極大震撼。刀割開眼球,云劃破月亮的畫面實際上也在隱喻初次性行為。使用這樣一種帶給人心理不適感的視覺語言去象征“性”,實際上也代表了作者的一種傾向——即表達“性”這一原始的本能沖動所帶來的破壞性。這也是《一條安達魯狗》表達的一個重要主題思想。
繼影片開場結束后,在下一幕之前,“八年后”的字樣出現在銀幕上。但實際上影片并沒有真的按照這樣的時間進行邏輯性排列。作為一部反敘事電影,布努埃爾用一種夢境式的跳躍轉折來構成這部作品,與布努埃爾幾乎同時誕生的弗洛伊德的《夢的解析》也被當作影片的理論依據。事實上,電影和夢境的關系十分復雜,德國學者本雅明曾指出“電影這種空間是一個人造的夢境。”但夢境的碎片性與模糊性使其與文學又有著本質上的區別。布努埃爾此舉試圖打破這一差異性,使用夢境的方式進行創作,但其內在本質上依然是一種自我意識的表達,并不完全如夢境般無邏輯。
下一幕,騎自行車的男人與坐在房間內的女人正式出場。男人和女人在這部影片中占據著90%的時長,他們的外表和互動情節也隨著扮演的身份不同而隨時轉換。在這十七分鐘內他們分別扮演了兒子與母親、丈夫與妻子、強奸者與被強奸者、情侶等多重身份。二人實際上象征著所有的男女關系,而并沒有傳統意義上故事中的人物身份。另外,影片中的男人還有另一個身份,作為同一演員的不同身份,他在影片中手持圣經,似乎與前面的男人是父子關系。但實際上影片中所有角色都可以視為同一男性或女性。他們主要作為弗洛伊德的本我與自我出現在畫面中,時而壓抑自我的非理性沖動,時而被社會秩序所束縛。
羅蘭·巴爾特被認為是符號學真正意義上的開創者,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在于他開拓性地把符號學運用于視覺文化的研究,這也引起了電影界的關注。盡管《一條安達魯狗》是一部反敘事的作品,但仍然可以看出一條較明確推動故事發展的線。因此,我們可以借用巴爾特的理論分析這部作品。巴爾特在對敘事作品中人物角色進行功能單位分析時將人物分為主體/客體、傳播者/接受者、助者/敵者。將這一模型套用在《一條安達魯狗》中,我們會發現,無論將男人作為主體,還是將女人作為主體都完全說得通。是將男人視為正義的一方,還是將女人視作正義的一方,布努埃爾并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答案。比如,在影片中,男人看似在追逐著女人,但在影片的最后女人卻也走出象征著婚姻的房間和門外另一個更符合自己理想的“穿條紋坎肩的”男子親熱起來,最后被埋沒在春天里。影片中男人和女人都沒有達成自己的追求。
“手”作為重要的象征符號,在影片中著重表現了三次。手作為男性生殖器的象征與作為性沖動象征的螞蟻同時出現,第一次是剛剛脫下嬰兒服的男子望著自己的手,螞蟻從手上的一個黑洞中爬出,象征著男人性成熟過程的開始。而后黑色螞蟻與海膽和女人的腋毛疊加剪輯在一起,象征著女性的性吸引力和危險伴隨出現。第二次是手單獨出現在馬路中央,一個上身男裝下身女裝的中性人在用棍子撥弄著那只手。警察驅散了圍觀群眾,將手裝進了帶條紋的盒子里。這里的手象征著欲望,秩序禁止欲望暴露于大眾之間。無處可歸的中性人最終被汽車撞死,而樓上的男子在看到這一幕后興奮地覺醒了自身的欲望,對女人步步緊逼。第三次是在男人追逐女人的過程中,女人逃到另一間房子,用門夾住男人的手,更多的螞蟻從手上爬了出來,象征著性到達頂峰。螞蟻也是達利繪畫作品中經常出現的元素,在他的繪畫作品中常常象征著死亡與腐爛。結合這一點也可以看出作者對性沖動所帶來的破壞性的暗喻。
條紋也是影片的重要組成部分。房間的條紋墻紙,反復出現的帶條紋的盒子,條紋領帶,以及最后出現的身穿條紋坎肩的男人,這些條紋都象征著“社會秩序”,或者說人類的文明對性的束縛。另外,在男人追逐女人的橋段中,男人突然背上麻繩,拖著象征宗教的兩個天主教徒,象征腐朽的文明禮儀制度的兩架載著動物尸體的鋼琴去接近女人,女人被迫逃到了另一個房間,即婚姻。手與條紋的能指可以有不同的所指,不同的受眾可以有不同的解讀。但這種解讀必須建立在男人和女人在本部影片中的關系的基礎上。
在整部影片中,男性和女性大多數時間處于相互對立的狀態。男人被欲望所驅使,而女人則希望借助文明,借助道德去束縛性。而身穿格子西裝的男人,即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自我的一面在臨死前也暴露出本我的一面,撲向了幻想中的裸露女子的背影。蛾子背后不祥的圖案和女性在跨入最后一間房間后消失的腋毛都傳達出作者對婚姻的消極態度。女人試圖借婚姻去完成自己理想中的男女關系,而男人則拖著婚姻的束縛去完成自己的欲望追求。影片最后一段,在男性伴侶的引導下,女性也最終拋去了象征倫理道德與秩序的盒子與領帶,卻在下一幕中和男人一起半截埋在土里,被蟲子啃噬著尸體。
在影片上映的1928 年,資本主義國家第二次工業革命基本完成,進入高速發展階段。一方面,影片用人的原始欲望與工業文明下的社會秩序發生碰撞,從而表達作者的觀點;另一方面,影片對于婚姻和男女關系的探討也重點強調了秩序的壓迫和婚姻的不合理性。根據上文提到的男人和女人在影片中對立的狀態,在互聯網快速發展的今天,這種對于男女關系的對立性的探討更加值得關注。男女關系在不同的階段,乃至在文明高度發達的今天,其矛盾不僅沒有被調和反而愈發暴露出來。
這里便拋出了一個問題:性別對立與社會文明的發展之間有何關系?《一條安達魯狗》對此給出的答案更傾向于文明的發展激化了這種矛盾。布努埃爾對于這樣一種兩性關系的矛盾化解也持一種消極態度。倘若回到原始社會,這種矛盾并不會隨之消除,只是在母系社會或父系社會中一種性別的絕對權力下被遮蓋住了。因此,文明并不只是對人性的壓迫,更多的是對人性的解放。今天性別對立矛盾產生的原因十分復雜,無法用一種觀點概括。但這種矛盾的激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平權的發展,雖然許多傾向難免有偏激之嫌,但宏觀上來說也可以算是一種意識形成的必要過程。
《一條安達魯狗》強調了文明與道德等固有秩序對人原始欲望的壓迫,也表達了男女關系的種種對立性,這些觀念在今天看來有待商榷,但在當時對于沖擊資本主義工業化車輪碾壓下的人性有著重要的意義。今天對于超現實主義影視作品乃至繪畫作品的認識,不應該舍本逐末地研究他們是如何對夢境幻覺或潛意識進行再現的。這僅僅是一種創作方法,涉及藝術的假定性和藝術作品本身的內容問題。藝術是人創造的,我們應該去追尋藝術家在其作品中表現的理性追求與感性認識。因此,對作品進行解讀乃至“過度解讀”都是十分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