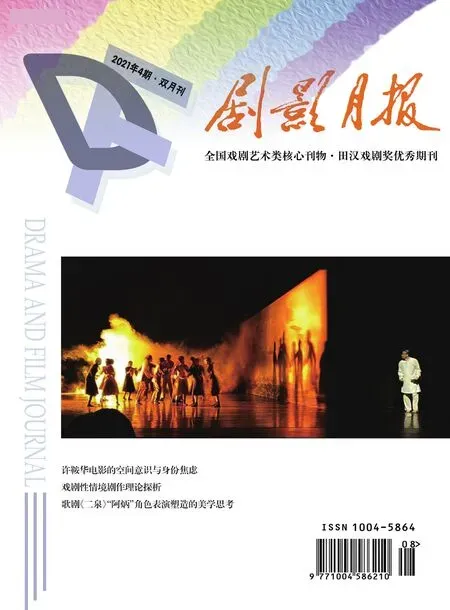戲劇性情境劇作理論探析
■賈兵
戲劇性是戲劇學的重要概念,自提出以來無數的劇作家或戲劇理論家對其內涵提出過多種不同角度的界定:“有的將情境說成是作品的基礎;有的認為是一個不可缺少的環節;有的看做是戲劇的本質;有的則把它看做是對象。在具體的范疇,有的認為應推廣到劇場,有的則局限在舞臺演出;在劇本創作上,有的提出在設置情境時要設身處地地想問題;有的提出要從社會的角度給予考慮。”
在諸多說法中,戲劇性的概念主要有:被用來概括戲劇藝術的本質,以區別戲劇與非戲劇和被用來解釋戲劇藝術能“引起觀眾興趣,抓住觀眾有興趣地看下去”的原因兩種主要說法,每種說法又各存在偏重外在形式和內在情節的兩個方向。因此,戲劇性理論大致有四種概念:體現戲劇外在形式上的本質,描述戲劇外在形式上的吸引力,反應戲劇內在情節的本質,對具有吸引力的情節共性的概括。
一、從“模仿說”到“情境說”:戲劇性情境的理論基礎
(一)“模仿說”與戲劇的外在吸引力
從外在形式上看,戲劇性必須體現戲劇藝術所獨有的本質特點,較早討論這一問題的亞里士多德提出戲劇的本質在于“模仿”。而這種“模仿”區別于繪畫等其他“模仿”藝術的特點在于戲劇模仿的對象是動態的“行動”。因此戲劇外在形式上的吸引力一定程度上體現于其“劇場性”及“可演性”等對外在的行動、場面上的效果要求。
但是,只具有場面和行動的“模仿”顯然不能完全體現戲劇藝術的特點。大量的學者認為戲劇性應存在于戲劇的內部,也就是戲劇情節之中。在這一理論框架中,主要說法有布倫退爾的“矛盾說”、阿契爾的“激變說”等等,他們試圖概括出所有的戲劇情節的共同點以反映戲劇的本質。
(二)“矛盾說”、“激變說”與戲劇的內在吸引力
布倫退爾認為矛盾沖突才是“戲劇的本質”,戲劇表現的就是人物產生自覺意志后在為實現自覺意志而采取的行動中與遇到的阻力之間的沖突和對抗。這一戲劇性理論明顯能夠涵蓋大量劇作的情節模式,甚至直到今天仍被以好萊塢為代表的現代商業電影所采用,但在可見的劇作中顯然存在大量的“矛盾說”無法涵蓋的劇作——如經常被拿來攻擊布倫退爾觀點的莎士比亞劇作《羅密歐與朱麗葉》的果園相會一段:這場戲的主要情節是一對戀人在互訴衷腸后確立了愛情關系,是故事向前發展的重要情節點,但兩人之間卻并不存在任何矛盾沖突。
相比之下,阿契爾“通過——或者可以設法使它很自然地通過一連串較小的激變而發展,并且在發展過程中或多或少地含有能激動人的情緒的東西,如果可能的話,還含有生動的性格表現在內”的“激變說”所涵蓋的情節范圍還要窄于“矛盾說”。
“激變”(又作“危機”)僅是矛盾沖突的類型之一——矛盾沖突既可以產生于追逐未擁有的事物或人的過程,也可以為保護已擁有的事物或人,而后者就是所謂的“危機”。因此,無論是“矛盾”還是“激變”都無法涵蓋所有的戲劇情節,而相比之下“激變說”的范圍更窄,更接近情節對觀眾的吸引力問題。
與“漸變”相比“激變”明顯更能夠吸引觀眾的注意力。在符合邏輯和人物性格的情況下,越突然、越激烈的情節變化越能引起觀眾的興趣。因此,柯爾在《西歐戲劇理論》中又提出了用“可以導致情緒上和心理上會發生震驚的意外成分。”來概括吸引力情節層面上的戲劇性,雖然其涵蓋范圍比“激變”有所擴大,而且將“戲劇性”概念中情節的吸引力問題與觀眾聯系的更為緊密,但顯然仍具有局限性:某些“懸念”可以造成吸引觀眾的“緊張”感,但最后的結果帶來的卻很可能是放松而非震驚。
我們之所以無法確定戲劇情節對觀眾的吸引力所在,僅能以“懸念、誤會和巧合等因素”作為劇作技巧零散地觸及這一問題是因為我們很難找到一種既能如“模仿說”理論一樣概括戲劇外在本質,也能夠像“矛盾說”、“激變說”和“震驚說”一樣體現戲劇內在本質并具有更廣闊的涵蓋性的概念。而由我國戲劇理論家譚霈生先生在黑格爾和薩特等人的戲劇情境理論之上提出的“情境說”戲劇性理論似乎能夠解決這一問題。
(三)“情境說”與劇作理論的建構
譚先生認為,戲劇情境需要包含“特定的情況,環境和特定的人物關系”。戲劇的本質在于情境中的人物根據當前情境下的利害關系以及自身的性格產生自覺意志并付諸行動,進而收獲一個結果,或造成當前情境的改變,或未改變情境——情境可能因其他外在原因而改變。之后,新情境下的人物再產生新的自覺意志并行動,舊情境下的人物則為未實現的自覺意志再次發起行動……
譚先生的戲劇性理論無疑是對戲劇藝術本質的探索,這一理論提供的情節模式幾乎可以包容古今中外的全部戲劇情節。因此其在對戲劇本質——尤其對戲劇內在本質的理論認知方面具有重大的意義。
如前文所說,正是由于缺乏對戲劇內在本質的足夠認識,劇作問題長期停留在零散的技巧層面,編劇理論遠未得到足夠的發展。正如我們無法在認清研究對象是什么之前,不可能總結出其優秀部分之共性,劇作理論一定要建立在對戲劇本質認識的基礎上,即某種戲劇性理論之上。只有產生了能夠反映戲劇本質,涵蓋所有情節的戲劇性理論,才可能產生對具有吸引力情節的本質認識,進而產生創作這類情節的劇作理論。因此戲劇性的“情境”理論對劇作理論的建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中央戲劇學院的楊健先生就曾提出根據譚先生的戲劇性情境理論,建立編劇學理論體系的設想。
雖然“情境”理論在劇作方面的應用還有待進一步研究,但在特定的情境之下,性格不同的人物必然產生不同的情節,因此“情境”理論可以為劇作構思帶來一種情境、人物、情節的多重組合之可能性。而在三者之中,一個具有戲劇性的“情境”至關重要。
所謂戲劇性情境與一般“環境”的區別不僅在于情境中的人物之間已經具有了某種關系或發生過某些前事,筆者認為其最核心的設計應該在于通過前事、環境和人物關系的設定,保證此時情境中的各個人物處于對情境了解的不同程度之中。一旦劇中的各個人物對情境的了解程度存在差異,便能有效為故事的發展提供基礎和動力,為后續情節的產生創作充足的條件。
這種基于戲劇性情境理論的戲劇性情境設定體現了戲劇藝術的本質特點,且能夠容納并解釋目前可見的所有產生吸引力情節的劇作技巧,從理論上說具備構建劇作理論的可能性。
二、從存在形式到表演行為:戲劇性情境對戲劇本質的表現
戲劇性情境由于基于戲劇性“情境”理論,因此對戲劇內在情節本質上的意義無需過多解釋,而其對戲劇外在本質——“對行動的摹仿”的體現還有待進一步說明。
(一)對戲劇存在形式的“模仿”
如前文所說,作為模仿對象的“行動”能為戲劇作品帶來外在的場面性和觀賞性,在一定程度上為戲劇提供“可演性”或“劇場性”。而如果從更的深層次對該問題進行討論的話,戲劇藝術的這種“模仿”以其在人類所處的現實中“模仿”出一個虛擬時空為存在形式。戲劇的這種“依靠模擬人物進行的敘事作品本質上就是一種嵌套結構的文本”,其存在層次要低于我們的現實世界,并與之構成一種嵌套關系。
而戲劇性情境中的人物,因為對情境的了解程度不同,彼此間也必然形成一種類似的“嵌套關系”:對情境了解程度較低的角色在語境上是低于對情境了解程度較高的角色的,或者說前者一定意義上存在于后者的層次之下。后者可以隨時通過把真實的情境告訴前者使其脫離原來所處的較低的存在層次。如果再考慮觀眾的因素,那么這種本質會被體現的更加直接:至晚在劇作的高潮到來之后,觀眾們都會處于對情境全面了解的狀態之下,進而會對劇中不完全了解情境的角色形成一種優勢。與電影《楚門的世界》類似:銀幕前現實世界的觀眾與影片故事體世界中除楚門之外的所有人物及楚門三者之間就形成了這樣一種存在層次上的嵌套關系。
這種嵌套關系造成的優勢既體現了某些角色或觀眾高于劇中其他角色的存在層次,也體現了現實世界高于戲劇虛擬時空的存在層次上的優勢。所以我們可以說“戲劇性情境”以類比的形式體現了戲劇藝術“模仿”的外在本質及其存在方式。
(二)對戲劇“表演”行為的“模仿”
在“戲劇性情境”之中,作為模仿對象載體的“人物”,因為對情境的了解程度不同,有很大的可能會出現一方對情境的了解程度高于另一方,而又無法把真實的情境立刻告訴后者的情況——否則這種差異在情節設定上就毫無意義。這又使得前者往往需要通過“表演”來假裝自己和后者處于對情境了解的同一層次中。
在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中,娜拉完全清楚自己的處境:如果不能幫助柯洛克斯泰向自己的丈夫海爾茂要回他的工作崗位自己就會面臨牢獄之災。海爾茂對娜拉所處的情境完全沒有了解,而他對柯洛克斯泰的鄙視態度又讓娜拉無法開口替后者要回工作,所以娜拉只能假裝自己被柯洛克斯泰要挾的情況并不存在,而以“表演”的方式來“模仿”自己和丈夫正處于同樣一個未受到任何威脅的情境之下之狀態,以度過最后的“快樂”時光。
類似的例子在戲劇、影視作品中屢見不鮮。這種劇中人因他人對情境缺乏了解,而自己不得不假裝處于對方所認識程度的情境之中的行動,從另一個層次體現了戲劇藝術“模仿”的本質特點。
可見,角色的這種“模仿”行為不僅為表演提供了更多的層次,也同時體現了戲劇藝術外在的“模仿”本質。因此,基于戲劇性情境理論的對戲劇性情境的設定,從內在的情節模式和和外在的存在形式上都體現了戲劇藝術的本質。
三、從戲劇反諷到誤會、巧合:戲劇性情境是劇作技巧的前提
從創造吸引力情節的劇作角度來看,戲劇性情境理論幾乎可以解釋目前可用的所有劇作技巧,具備了使這些在劇作實踐中被總結出來的、零散的、互不統屬的劇作手法統一于一套劇作理論的可能性。
(一)戲劇反諷
能夠最直接的反應戲劇性情境劇作意義的技巧就是戲劇反諷。戲劇反諷是一種通過引導了解實際情境與相應臺詞之間的反差,并且讓戲劇中的角色對這種反差一無所知,從而達到一種戲劇效果的劇作技巧。也就是在角色之間,同時也在角色和觀眾之間形成一種對情境了解程度上的差別,而對情境了解程度優于劇中人物的觀眾眼睜睜的看著某個劇中人因為缺乏對情境的了解而將要犯下錯誤或面臨危險時,無疑在角色和觀眾之間——同時也在角色所了解的情境和真實情境之間——形成一種戲劇張力,進而牢牢地吸引住觀眾。
如前文提到的“矛盾說”無法解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的果園相會一場戲:兩位主人公都處于愛著對方,想和對方在一起,但又不確定對方是否能戰勝家族仇恨接受自己的復雜情境中。隨著羅密歐來到朱麗葉的窗下,偷聽到朱麗葉對自己的愛意,羅密歐所處的情境便發生了變化,使自己獲得了比于朱麗葉對劇作情境更高的對情境的了解:知道了朱麗葉是喜歡自己、希望和自己在一起的。于是站出來對朱麗葉表達了愛意,也讓朱麗葉知道了自己的心意,提高了朱麗葉所處的對情境的了解程度。所以這場戲的吸引力不在于矛盾沖突,而在于完全了解情境的觀眾對不夠了解情境的人物是否行動、如何行動的期待。
但戲劇反諷必須以觀眾已知為前提才能把矛盾指向觀眾所知和角色所不知之間才能形成一種戲劇張力,且其情節發展的方向比較單一,不能反映戲劇性情境所包含的無限的變化發展方向。
比如在遼寧人民藝術劇院復排的話劇《父親》中,沉浸在大兒子大強成為副廠長的喜悅之中的父親楊百萬,被小兒子二強一句“大哥已經辭職了”震驚得目瞪口呆。而對大強辭職一事觀眾此前一無所知,因此該情節并不屬于對戲劇反諷技巧的使用。但其明顯基于楊百萬、觀眾和二強對所處情境的不同了解程度之上,并具有“反轉”所帶來的強烈的吸引力效果,因此戲劇反諷僅僅是戲劇性情境應用方式的一種。
(二)發現與突轉
剛剛提到的來自亞里士多德的“發現”和“突轉”理論的“反轉”技巧,同樣是由劇中人物對所處情境的不同了解程度造成的,在經歷了對情境由“未知”到“已知”的變化過程后,人物的命運發生的改變。
比如在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中,已經經歷了“殺父娶母”的俄狄浦斯,由于在故事的開始時對所處情境中的這段“前事”一無所知而逐漸將自己帶入了悲劇的深淵。而俄狄浦斯對所處情境的“發現”又是基于報信人、牧羊人等對情境不同程度的了解和對他們帶來的零散信息的拼湊基礎上的,同時劇中還存在著對情境完全了解的盲人先知特瑞西阿斯。可以說,先知特瑞西阿斯、報信人和牧羊人以及俄狄浦斯正好處于于對情境了解的三個不同次,構成了戲劇性的情境,促成了俄狄浦斯對情境的“發現”和隨之帶來的命運的反轉。
(三)懸念與驚奇
被廣泛使用于現代影視劇作品的“懸念”與“驚奇”技巧也是如此。“懸念”通常包括兩種情況,一是對主人公未來命運的期待。二是對之前發生的未經表現的故事內容的好奇;而“驚奇”通常指不經鋪墊的對觀眾的驚嚇。
而無論是懸念還是驚奇,均基于故事主人公缺乏某些關于情境的重要信息的戲劇性情境的設定。二者的區別在于:使用“懸念”的情節中,觀眾知道的有時會比主人公多一些,為主人公能是否夠躲避即將到來的危險而感到緊張,而有時則跟主人公知道的一樣多,期待主人公解開事件的真相而徹底了解情境;而在“驚奇”技巧的使用時,觀眾和主人公對情境的了解程度完全相同,震驚于突然被表現出來的真實情境。
(四)誤會與巧合
喜劇里常見的“誤會”與“巧合”技巧也正因為人物對情境不夠了解,才會因為自己的有限信息而產生“巧合”基礎上的“誤會”。而對情境了解程度較高的角色往往無法直接參與到故事中,以保證“誤會”被持續。直到劇中各人物完全了解情境時,誤會才會被解除,故事也迎來大結局。觀眾作為對情境完全了解的存在一直處于由這種優越性造成的可笑性之中。
可見,無論是“戲劇反諷”還是“發現與突轉”、“懸念與驚奇”還是由“誤會”造成的“巧合”,這些被廣泛使用的劇作技巧均來自人物對情境了解程度上的差異,也就是戲劇性情境的存在。正如大衛·波德維爾在《電影詩學》中所說:“我們的好奇、懸念以及驚訝都是通過對我們知道什么和何時知道進行操縱而產生的”。
結語
綜上所述,制造一個使劇中人物處于對情境了解不同程度的情境不僅能給作品帶來情節的多種發展的方向,更是產生對觀眾具有吸引力情節的前提。這種戲劇性情境的設定基于對戲劇本質認識的戲劇性“情境”理論,具備形成一套劇作理論的可能性:根據情境中主要人物的性格、情境的復雜程度以及觀眾是否了解情境等元素對故事進行逐步的分類推演、排列組合就可以規劃出所有情節發展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