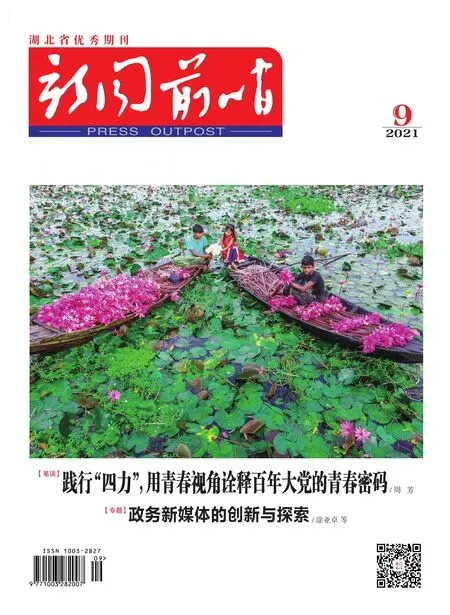文化類節目的媒介記憶建構
——以央視《故事里的中國》為例
◎馮路欣
《故事里的中國》于2019年10月播出第一季第一期,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中國共產黨建黨98周年之際應時而生的文化類節目。從現實意義上講,《故事里的中國》作為中央廣播電臺紀念新中國成立70周年推出的大型綜藝類節目,節目通過梳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典型人物、典型題材的經典人物及故事、榜樣人物,極大地滿足處在信息爆炸與信息匱乏的受眾精神需要,這種故事分享的方法顛覆了以往人們接受信息的模式,《故事里的中國》憑借其獨特的敘事性、綜藝性吸引人們的關注。本文主要討論《故事里的中國》節目媒介記憶呈現、建構策略以及建構價值。
一、央視《故事里的中國》時代“文化封面”媒介記憶建構策略
《故事里的中國》以小見大,以“生于平凡、卻敢于追求不平凡”的立場高度還原眾多領域典型人物的真實故事,聚焦現實主義經典,凝聚時代精神。
(一)媒介記憶作用下的受眾互動與認同
媒介記憶的建構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加深社群對自己的身份的認同,社會成員在“自己人”效應的作用下對具有權威性的媒體生產的內容產生了順向的心理活動傾向,節目正是利用受眾的歸屬心理拉近了傳播者與受眾之間的溝通。編劇劉靜創作的《父母愛情》是以自己父母為原型,其姐姐劉軍被邀請至節目現場,向觀眾親身解讀自己體會到的父母愛情,受眾接收到了劉軍傳達的信息與情感,加之聲音、畫面的渲染,鏡像神經元在頭腦中被激活,節目中影像記錄與對話交流輸出的信息使大腦中相對應的神經元被激活,進而提取或想象這部分的感官記憶,并自動將這些記憶與自己的感情相匹配,這一系列的處理使得媒介記憶與個人記憶形成了潛在的聯結。大眾傳播時代下,信息的受眾是大眾,在信息的刺激下,受眾深受媒介記憶的影響,與傳播者在情感上達到了共鳴,這也使受眾的個人記憶與集體記憶在精神層面達到了一致。
與此同時,社交媒體利用平臺的轉發、點贊、評論等功能為媒介記憶的傳播提供了新的環境,相關操作既可達到及時的信息交流與直接反饋,也可以增強受眾粘性與互動性。以抖音為例,截至2021年一月,《故事里的中國》抖音官方賬號共擁有粉絲53萬(其中抖音擁有49.3萬粉絲,今日頭條擁有3.6萬粉絲),發布了68條作品,轉發總量高達43257次,受眾累計評論88025條,獲贊1056.9萬。獲贊最多的視頻是“周總理親手送的演出服,這位日本老人穿了四十多年”:松山芭蕾舞團森下洋子從1971年至今,每次《白毛女》的演出都會身著1971年周總理接見時贈送的演出服,這一段視頻時長僅36秒,獲贊高達238.4萬次,網友與作者積極互動,共19340條評論,轉發6215次,有些網友真誠的評論也收到了作者的點贊,媒介為受眾提供了表達對媒介記憶的認同和贊揚的平臺,同時也使傳播者獲得受眾的信息反饋,以便制作更貼合受眾需求的節目,這樣的雙向交流形成了良性循環。《故事里的中國》一節目以共同的集體記憶為基礎,擴大了節目覆蓋面,吸引不同年齡、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受眾觀看,并且其傳播的信息在時間上的跨度極大,對于不同的受眾意義不同。根據酷云大數據調查顯示,該節目突破了青年群體對教育文化類影視的刻板印象,節目以18-44歲年輕用戶為主,占比高達77.55%,未成年人TGL指數高達152,用更高質量、更具藝術氣息、更符合當代潮流的方式傳播媒介記憶,帶動年輕人了解歷史、了解中國故事的熱情,為中國故事注入年輕活力提供了新的思路。
(二)媒介記憶的選擇
身處信息量爆炸但信息質量匱乏的時代,阿斯曼夫婦在研究“文化記憶”與媒體之間的聯系時意識到:“當前的大眾媒體制度割斷與過去的聯系,從而把今天絕對化了。大眾媒體使人們的記憶悄然變成了不斷生產消費品和不斷消費人為編造的‘歷史’”在現如今越來越多的人依靠媒體形成并完善自己對社會的記憶的時代,不同于歷史記憶,社會對集體事件的定義會影響傳播者選擇性記憶與選擇性傳播,受眾對媒介記憶的需求與反饋也會影響媒介對記憶的選擇,傳播者站在中國語境下思考“民族”與“國家”、“集體”與“個人”之間的聯系,積極主動思考媒介記憶標準,選擇極具代表性、重要性、顯著性的歷史記憶,營造良好的社會事件與歷史記憶傳承環境,貼近新時代觀眾的喜好,采用主持人與訪談對象問答和影像記錄播放相疊加的方式講述故事情節,其中不乏幽默與玩笑,但在細節中又能體現英雄人物形象的豐滿與立體,突破傳統意義上精神文明傳播的限制,生動地講述故事里的中國。
媒介記憶既是記憶載體,也是記憶的傳播者,《故事里-的中國》第一季改編耳熟能詳的作品,再現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國家當代建設發展過程中英雄人物的故事,緊扣時代主旋律,著力解讀故事背后的精神力量。《故事里的中國》第二季主要側重于向當代楷模致敬,影視與話劇大部分為原創,這不僅要求節目組在戲劇故事方面展現創意,用虛構的故事展現并非虛構的生活,吸引新時代青年重視時代歷程,對歷史懷揣敬意。節目組積極承擔采集中國記憶的責任和義務,深度挖掘媒介記憶中的信息資源,利用自身特點和優勢,傳承社會記憶,滿足受眾精神需求,營造積極健康的媒介環境,是每個媒體人、媒介組織應該思考并付諸實踐的。
(三)影視符號的設計
在舞臺設計方面,節目對于戲劇表演的舞臺設計作出了創新,在主舞臺的兩側分設兩個個小舞臺,擴展了表演的空間,增加了敘事內容,敘事更加立體,多線并立,使得故事更加完整。多場景的切換增強了觀感,長時間的觀看也不感覺乏味。以鐘南山的故事為例,舞臺一比一完整的還原了鐘南山家、乘坐高鐵、醫院開會、病房安慰患者等場景,使觀眾從各個不同的角度感受鐘南山完整的人物形象,同樣拉近了演員與觀眾的距離,讓表演更加貼近觀眾認為的現實世界,使演員的情緒變化得到觀眾更多更深刻的理解和反饋,增強了戲劇表演的節目效果。
聲音符號是組建影視語言的重要部分,聲音符號的準確運用對于成功的戲劇是至關重要的,聲音這一符號逐漸成為了研究者研究的重要課題,節目中的聲音符號更引起我們的關注。以《鐘南山》為例,戲劇表演的聲音配置可圈可點,貫穿整個戲劇的鋼琴曲完美的貼合了故事的走向和情緒的變化:救護車的音響配合演員的動作彰顯了他以治病救人為首要的高尚職業道德;在醫院查房的片段中微弱呼吸的聲音和擔架車車輪極速摩擦地面的聲音,讓觀眾直觀的了解到當時情況的緊急與嚴重被鐘南山的無畏精神所打動;在演出的結尾,青年時期和老年時期的鐘南山相遇,在這記憶相逢處選用的音樂給人的聽覺感受是淡然但不失廣闊的,這象征著鐘南山在平凡崗位的忠誠堅守以及對事業作出的巨大貢獻。聲音符號是對傳播者站在第三方角度對記憶的渲染、表達,化抽象的精神記憶為具體的現實情感,能夠幫助受眾更好的體會當事人的情緒。
二、央視《故事里的中國》時代“文化封面”媒介記憶建構價值
(一)公共領域建構文化認同
媒介記憶拓寬了記憶傳播方式并且擴大了受眾的覆蓋范圍,時代“文化封面”媒介記憶建構服務在議程設置及模仿典型對象的選擇方面符合精神文明建設,節目涉及文學、歌劇、扶貧、影視、軍事等各個行業、各個領域,節目用受眾喜聞樂見的方式講述了20世紀革命者的艱辛、扎根基層的工作者的奉獻與堅守,也提及21世紀懷著時代使命的年輕一代的精神面貌,這些記憶具有巨大的教育力量,能夠開闊受眾的視野,激發受眾的個人記憶和創造力,影響個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及對國家的利益的關注程度。節目除了通過影像記錄等媒介記憶重溫時代印記,還利用與故事相關的人物的個人記憶進行代際傳播,影像記錄與同時代親歷者或見證者的回憶交替敘述,將集體記憶、媒介記憶與民族主義聯系在一起,強調民族認同感和國家歸屬感的英雄敘事形成了不同時空的強烈對比,實現媒介記憶的情感價值;鼓勵受眾從中學習,努力奮進,使受眾精神備受鼓舞,加入到譜寫中國新故事的行列中去,為國家再創新的記憶。
(二)為新時代中國青年領航定向
伴隨著全球化、傳播平臺的拓展、傳播技術的升級,青年群體伴隨著媒介同步發展,青年受眾在媒介上投入的時間和資金也越來越多,近些年來,在青年群體中存在著泛娛樂化、負能量情緒、無思考行為的現象。馬爾庫塞在《單向度的人》一書中指出青年學生等最少受到社會一體化趨勢的影響的群體存在一定的批判性、否定性的向度,青年受眾會以自己對媒介記憶的解讀構建屬于個人的記憶,傳媒企業應自我管理提高傳媒素養,與當代青年進行坦誠對話,站在年輕化的視角創新傳播中國故事的方式,用青年受眾喜聞樂見的方式講述媒介記憶。節目利用正能量偶像、演員作為話劇演員,通過媒介記憶敘事角度的故事講述和偶像榜樣再演繹的方式,鼓勵青年樹立正確的歷史觀、價值觀,樹立典型人物為時代新青年領航定向。
(三)講好中國故事,展現國家活力
簡單的同化或者純粹的寬容并不足以支撐身份認同的形成,反之,身份認同的基礎應當是根植于制度層面的多元文化實踐。節目基于第三視角講述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中國故事,結合歷史脈絡與社會文化進程,對新中國做了一次全景式的回顧,以浪漫溫馨、生動感人的筆觸,向中國社會及國際社會展示中華民族的獨特魅力。在故事中讀懂中國社會的變遷,領悟中華民族精神,體會中華歷史文化的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在故事中發現民族與國家的創新精神,通過媒介記憶傳達了作為中華民族歷久彌新的核心的價值觀念及行動典范。節目將多元的公民身份在民族身份層面彰顯出一體化,還拉近了中華各民族之間的族際關系,在國家層面反映出中華民族的多元與一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