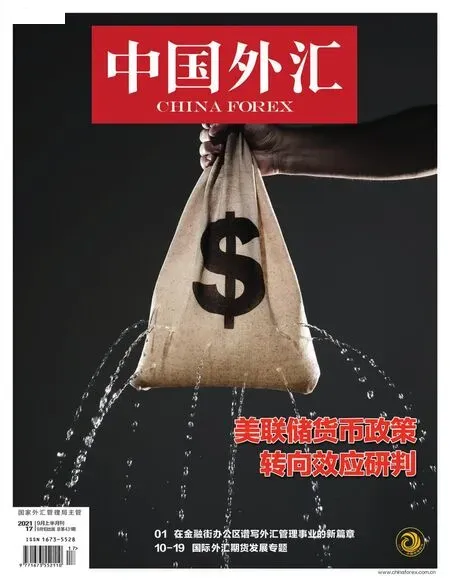離岸人民幣外匯期貨市場蓬勃發展
文/鮑思晨 田園 編輯/孫艷芳
外匯市場大致有兩種分類維度:一種是將外匯市場劃分為在岸和離岸市場,另一種是將外匯市場劃分為場內和場外市場(見附圖)。在岸和離岸市場比較容易理解,即以外匯交易發生地劃分。而場內和場外市場的區分以及定義則稍顯復雜:場內市場是指在交易所開展的、以連續競價方式為主進行的標準化外匯期貨和外匯期權交易的市場;場外市場主要是指在銀行間市場開展的、雙方以簽訂個性化協議方式為主進行的外匯即期、外匯遠期、外匯和貨幣掉期以及外匯期權交易的市場。從日均交易額來看,離岸人民幣外匯市場的規模較大,產品體系豐富。這其中,即期、遠期等場外市場的占比較大,而以外匯期貨為代表的場內市場占比較小。這與外匯期貨在全球外匯市場中占比較小的現狀相吻合。根據國際清算銀行2019年的調查數據,全球外匯交易中,外匯期貨市場交易額占比為1.89%,人民幣外匯期貨交易額占人民幣外匯市場的1.09%,且全部發生在離岸市場。

注:不同機構對外匯市場的統計規則不同。國際清算銀行每三年進行一次央行調查,統計方式為日均交易額。最新的調查數據時間為2019年4月的日均交易額。全球期貨業協會的統計方式為交易手數,未給出產品交易金額,因此二者數據無法建立聯系和相互印證。國際清算銀行提供了一個可供對比的數據口徑,可大致展示人民幣外匯市場在岸、離岸和場內、場外的情況。根據數據統計規則,場外數據為凈總交易額,即僅調整當地交易商之間的重復計算,未調整跨境交易商之間的重復計算;場內數據為交易所集中清算,可理解為凈凈交易額,即對當地和跨境交易商的重復計算均進行了調整。因此,相比場內數據,場外數據可能略有虛高。根據外匯局的同期數據,2019年4月,我國場外市場的日均交易額為943億美元(此數據也為凈總交易額),略小于國際清算銀行統計的1012億美元。2019年4月人民幣外匯市場日均交易額分布圖(單位:億美元)數據來源:國際清算銀行
離岸人民幣外匯期貨市場發展已有15年
據不完全統計,全球共有12家交易所可以交易人民幣外匯期貨和期權產品(見表1)。由于市場主體存在規避匯率風險的需要,2002年之后,人民幣無本金交割遠期外匯交易(NDF)市場在中國香港、新加坡等多個地方迅速發展;2005年“7·21”匯改則使得市場對匯率避險工具的需求又進一步增加。在此背景下,為搶占先機,美國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于2006年8月28日率先推出了在岸人民幣對美元、歐元、日元期貨和期權6個品種。此后,境外交易所紛紛效仿:中國香港交易所推出了美元、歐元、日元、澳元對離岸人民幣的多種期貨產品;新加坡的三個交易所先后推出了美元對離岸人民幣、在岸人民幣對美元等期貨品種;中國臺灣期貨交易所推出了美元對離岸人民幣等期貨和期權產品;巴西、南非、韓國、土耳其、俄羅斯和迪拜等交易所推出了離岸人民幣對其本幣的外匯期貨產品。目前,交易人民幣外匯期貨產品的交易所可以大致分為兩類:一類來自與我國經貿往來密切的新興市場國家,包括南非、巴西、俄羅斯、韓國和土耳其,推出的場內人民幣外匯衍生品以離岸人民幣對本國貨幣的外匯期貨產品為主;另一類則來自國際金融中心,包括美國、中國香港、新加坡、中國臺灣和迪拜,推出的場內人民幣外匯衍生品以美元兌離岸人民幣的匯率期貨和期權產品為主。

表1 離岸交易所推出人民幣外匯期貨和期權產品概覽
近年來離岸交易所愈加重視人民幣外匯期貨市場
隨著市場規模的不斷擴大,各家交易所愈加重視人民幣外匯期貨,通過政策優惠、規則和機制的優化,來提高交易活躍度。隨之而來的,各家交易所的人民幣外匯期貨市場份額也幾經變動。例如,2015年中國臺灣期貨交易所上市了標準與小型美元兌人民幣期貨,上市之初通過做市等方式吸引流動性,使其在當年占據了人民幣場內外匯衍生品交投份額的頭把交椅。中國香港交易所和新加坡交易所緊隨其后。再如,2018年亞太交易所(新加坡)上市美元對離岸人民幣外匯期貨,通過手續費減免等方式鼓勵客戶參與市場,使得亞太交易所在2018年至2019年間的成交量激增,市場份額一度超過中國香港交易所;但激勵機制退出后,市場成交量逐步清淡。此外,得益于滿足不同投資者需求的多樣化人民幣外匯衍生品的發展策略,新加坡交易所的人民幣外匯期貨交易發展迅速,自2017年起成為全球最大的場內人民幣外匯衍生品市場。據全球期貨業協會的統計,2021年上半年,新加坡交易所占據76%的人民幣外匯期貨市場份額,中國香港交易所排名第二,占比16%,兩者合計占比超過90%。而長期以來,新加坡交易所和中國香港交易所能夠成為離岸人民幣外匯期貨交易最活躍的市場,一方面是因為兩地是亞太地區重要的金融中心,同時也是重要的人民幣離岸市場,因此人民幣的流動性較好;另一方面,因為不存在時差,交易時間也便于投資者參與。
離岸人民幣外匯期貨市場主要發揮避險功能
與大宗商品等傳統期貨市場的價格發現功能不同,外匯市場的價格發現功能主要由龐大的包括遠期市場在內的場外市場承擔。相關學術研究文獻,也大多聚焦遠期市場對即期市場的價格發現功能。而外匯期貨市場是零售市場,其主要功能是為市場主體提供套期保值和風險規避工具。在2015年“8·11”匯改、2018年下半年中美貿易摩擦升溫、2019年上半年人民幣面臨“破7”的重要關口,離岸交易所的人民幣外匯期貨成交量均出現明顯躍升,反映出市場主體對人民幣匯率避險需求的增長(見表2)。據全球期貨業協會的統計,2015年上半年,場內人民幣外匯衍生品成交16.81萬手;2021年上半年,這一數據提高至698.74萬手,增長超過40倍。

表2 重要事件推動離岸人民幣外匯期貨市場成交量躍升
離岸人民幣匯率期貨產品在離岸人民幣外匯期貨市場中占比較大
以離岸人民幣(CNH)為標的物的期貨成交規模遠遠大于以在岸人民幣(CNY)為標的物的期貨交易。據全球期貨業協會的統計,2021年上半年,離岸人民幣外匯期貨交易中,以CNH為標的物的期貨成交量超過690萬手,而以CNY為標的物的期貨僅成交1654手,前者是后者的4100多倍。究其原因:一是我國內地資本項目開放程度與我國香港等離岸市場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境外投資者持有CNH計價資產的便利程度更高;二是CNH的形成機制的市場化程度高,波幅更大;三是CNY/USD期貨采用1單位人民幣兌美元的報價方式,與傳統的人民幣美元貨幣對使用1單位美元兌人民幣的報價方式相反,不便于投資者開展交易。
人民幣外匯期貨市場仍有較大增長空間
綜上所述,市場占比不大的人民幣外匯期貨在離岸市場上豐富了全球投資者的匯率風險管理工具。筆者認為,與金磚國家中的巴西、俄羅斯、南非和印度四國相比,未來人民幣外匯期貨市場仍有較大的增長空間。這四國分別于1988年、1992年、2007年和2008年推出了外匯期貨產品,且發展十分迅速。據全球期貨業協會的統計,2021年上半年,印度、俄羅斯、巴西是全球前三大場內外匯衍生品市場,成交量分別為13.6億手、4.8億手、4.6億手,占比分別為51.9%、18.2%、17.5%,而美國作為金融期貨的發源地以及發達國家的代表,僅位居第四,成交1.1億手,占比4.3%。從成交量的合約分布來看,全球前六大場內外匯衍生品合約均是金磚國家境內交易所推出的美元兌本幣合約,而美國成交量最大的合約——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歐元兌美元期貨,僅排名第十二位。不過,金磚國家外匯期貨市場的成交量偏大也有一定的特殊性:一是金磚國家的銀行間市場發展相對滯后,特別是流動性較差,場內的外匯期貨市場成為實體企業和金融機構規避匯率風險的重要場所;二是為了提高交易活躍度和流動性,金磚國家貨幣期貨的合約價值普遍小于發達國家,因此成交量較大。
繼續發展人民幣外匯期貨市場具有重要意義。一方面,人民幣外匯期貨市場可以豐富市場主體管理匯率風險的工具箱。隨著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建立和金融對外開放水平的提高,境外投資者會更加深入地參與我國的資本市場,因而需要更加靈活、便捷的匯率風險管理工具。另一方面,人民幣外匯期貨市場可以改變過去由銀行單一提供匯率風險管理工具的現狀,降低市場主體管理匯率風險的成本,促進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