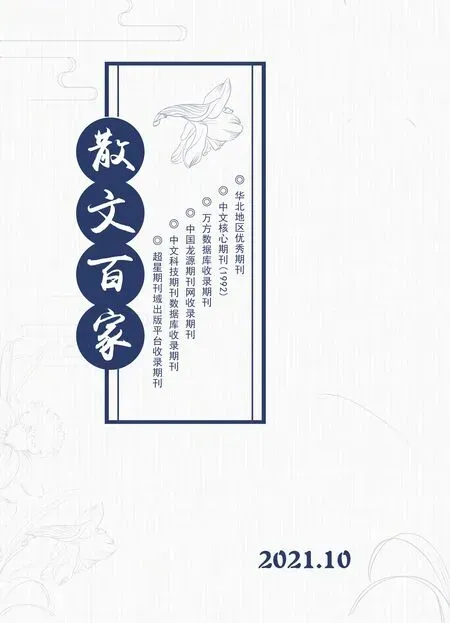少數民族地區教育現狀研究
——以青龍滿族自治縣花廠峪村為例
鄭雅琳
中南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
教育是國家未來國力的主要基礎,少數民族地區的教育問題直接關系到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是當今教育發展的重要課題,也是幫助解決少數民族脫貧攻堅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正如習總書記所講,治貧先治愚,扶貧必扶智。2018年青龍滿族自治縣成功脫貧摘帽,多年來,青龍始終堅持“以智扶貧、以教興縣”,最終成功探索出一條與自身實際相適應的教育扶貧路徑。
一、花廠峪村基本情況
本次少數民族地區教育現狀調查選取的調研地點為青龍滿族自治縣下轄的祖山鎮花廠峪村。清代光緒五年《永平府志》中有記載:花廠峪,在臨榆縣西北六十里,明時移細夯口關家莊,仍舊名,即此。由于該村溝深林密,故稱其“九溝十八岔,岔岔有人家。多則八九戶,少則三兩家”。花廠峪村景色秀美,生態環境極佳,近年來發展迅速,為更多人所熟知。
據統計,2020年花廠峪共有415戶,人口1341人,散居在十幾個自然村落。其中滿族約占40%,漢族約占60%。其中18歲以下233人,18-44歲437人,45-65歲436人,65歲以上235人。其中約25人為本科及以上學歷,約30人為大專學歷,約25人為技校畢業,其余均接受了九年義務教育。
二、花廠峪村教育的現狀
1.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作為現代國民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的前提與基礎。家庭教育在我國一直都占據著重要地位,古有出自各大家族的家訓流傳至今,不僅對個人的教養、原則起到了潛移默化的約束作用,而且對家庭乃至全體國人的立身處世、持家治業都有著重要影響。今有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給孩子講好‘人生第一課’,幫助其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在環境相對閉塞的少數民族地區,則更要注重家庭教育的實施。無論時代如何變化,無論經濟社會如何發展,對一個社會來說,家庭的文明作用都不可替代。
(1)家庭教育目標明確。花廠峪村的村民十分重視教育,家長將孩子的教育問題看作家庭的頭等大事,想盡辦法的讓孩子多讀書從而走出山區;普遍“認同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學校,家長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的觀點,對孩子的品德教育十分看重,良好的品格在他們看來是做人的根本。
訪談a:女,滿族,69歲,退休
我兩個孩子都上大學了,一定要上大學,上學才能走出去這大山溝啊。現在兒子在北京呢,留下買房了,閨女在市里呢。青龍人就是肯吃苦,肯掙錢,為了孩子一代一代的都往上爬。
訪談b:男,漢族,70歲,退休
八幾年我在雙山子(地名)上班,有一天賣牛的經過,從橋上掉下來兩頭牛,正好讓我看見了,我就聯系了牛頭崖鎮,問有沒有丟牛的,結果還真找著了,給人家還回去了。后來我給孩子們講過這件事,告訴他們做人一定要誠信本分,不能貪圖小便宜。我家孩子都出去上學了,我一直告訴他們要努力工作,不能懶惰,得自食其力才行。現在的孩子們條件好了,吃得穿得都好,是最幸福的時候,可不能沒良心,現在的孩子應該學會感恩。傳統的文化教育不能丟啊,那都是流傳下來的有價值的東西。
(2)父母親陪伴孩子的時間過少。花廠峪村因人口外流而使得家庭教育難以趕上社會平均水平。現今的花廠峪村常駐人口僅有370人,多為老人和小孩,青年人外出務工是導致留守在家的兒童在家庭教育方面有所欠缺的最根本原因。留守兒童的監護人多為其父母的上輩,在山區生活的老年人對外界事物了解有限,很難承擔起全部家庭教育的職責。
訪談c:男,漢族, 65歲,農民
兒子和兒媳都在外面打工,只有過年才回來,一年才能見上一次面。孫子留在家里和我們一起住,今年剛上三年級。之前在村里上了一二年級,現在村里沒有高年級了,就去祖山小學住校,一周回來一次。剛9歲就住校,沒辦法,我跟老伴文化淺,輔導不了他。眼睛也花,用不好手機。他如果在家里的話只能管他生活,其余什么也教不了。還是得讓他多跟同齡人在一起,在學校多學點知識。
2.學校教育。
學校教育是個人在一生中所受教育的最重要組成部分,學校教育對人的發展作用是全面的:不僅關心教育對象心智的增長,也關心其道德品質的形成,還照顧其身心健康。相較于具有片段性的社會教育和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的內容更加注重其內在的連續性與系統性。
花廠峪村實施教育有一些年限,不同階段教育呈現的模式不同。新中國成立前,花廠峪村就已經進行教育發展,由于受政治、經濟及客觀環境影響,教育并沒有成規,主要是以私塾的形式開展,只有富裕家庭的孩子才能進入私塾讀書,所以受教育的人只是占極少部分,大部分人沒有機會學習。新中國成立后,國家高度重視教育的發展,花廠峪小學始建于1954年,早些年的學生數量要遠遠大于現在。那時的花廠峪小學開設一到六年級,每屆有3-6個班,平均一個班30個學生。原因為那時計劃生育還未開展,每家每戶的小孩很多,也由于花廠峪村處于山區,整個村的面積很大,村民居住的十分分散,全村的小孩都來這里上學。花廠峪村現在僅有一個非完全小學,屬于基層教學點,共有兩名教師以及15名學生,隨著學生人數減少只留下了幼兒園以及一二年級,混合在一起上課,并沒有進行嚴格的分班,三年級后就要去鎮上的小學寄宿讀書。
訪談d:男,49歲,教學點任教老師
這個學校是五幾年建的,建的時候還是瓦房呢。八幾年的時候我在這上的小學,九五年開始在這里當老師,一晃35年了。我上小學那會學制還是五四的。九五年之前能上完小學,后來逐漸開始縮減,先是到三四年級,然后是一二年級,現在就只有一二年級和幼兒園了。上完二年級就去祖山中學住校了。
(1)學校配套設施落后。如今的花廠峪小學就是建在村民中心旁的二層小樓,僅有幾間教室,配套設施極其不完善,沒有操場以及其他運動場,學生的課余活動很難規范開展,課余生活單調。
(2)教學體系不夠規范。花廠峪小學為非完全小學,開設的課程有數學、語文、道德與法制以及培養學生動手能力的綜合實踐。與其他學校相同,公共衛生事件期間采取學生在家上網課的辦法。但由于學校師生人數太少,在一些方面還是存在著很多問題,例如幼兒園階段無法正常分為大中小班,混合教學使得學生沒有在合適的年齡熟練掌握應有的技能;小學一二年級階段由于教師和同學都沒有改變,教學體系不夠規范和系統,導致學生心理狀態較為松散,沒有身心投入到學校學習中去。
訪談e:男,49歲,教學點任教老師
問:現在小學里都有什么課程?
答:語文、數學、道德與法制、綜合實踐。
問:綜合實踐做什么?
答:干農活,還有培養各種技能。
問:這里小孩上完幼兒園直接上一年級了?
答:對,國家規定幼兒園要大中小班,我們這兒人少,就混一塊兒上。
(3)師資力量薄弱。教師花廠峪小學僅有兩位老師,從事鄉村教育工作多年,這些年一直扎根山區,堅守崗位;四處奔走,改善辦學條件,為學生搭建快樂學習、立德樹人的平臺。兩個人分工合作,承擔起年齡從幼兒園到一二年級不等的15個孩子所有的教學活動。但僅以兩名教師的力量對于所有的教學活動來說還是存在困難的。
訪談f:男,49歲,教學點任教老師
問:您兩個老師有什么分工嗎?
答:她教一個年級,我教兩個年級。一個人教所有科目,學生少。一共15個學生,一年級4個,二年級3個,幼兒園8個。
問:您和胡老師是怎么來這當老師的?
答:我就是本地人,小時候在這上的小學,開始山上有個教學點,在那兒教了一年書,然后考了編制。胡老師這些年一直在農村任教,支教好幾年了。她來上班挺不容易的,她家在另一個村子,離得遠有時候回不去就住在學校里,以校為家。
問:沒有想過去市里嗎?
答:也想過,但對家鄉還是很有感情。現在村里的年輕人是都出去了,但還有一些孩子留在家里,老人又沒法教這些東西,去祖山(小學)上的話一二年級的孩子還太小也沒法住宿,來回的路程太遠,沒大人接送又不安全。到什么時候村里還是得有個小學。
問:這兩年有志愿的年輕老師嗎?
答:有過,但年輕人待不住,這地方欠發達,來一兩年都走了。原來有定崗的,現在就我們倆人了。
3.紅色教育。
紅色教育以紅色作為時代精神內涵的象征、務實的落點在于教育。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講好黨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據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要加強革命傳統教育、愛國主義教育,把黨的紅色基因傳承好,確保紅色江山永不變色。”
花廠峪村是有著“銅墻鐵壁花廠峪,固若金湯靴腳溝”之稱的抗日革命老區。這里曾是八路軍挺進東北的前沿和冀熱遼邊區抗日中心,也是抗日時期長城外東北第一個鄉村黨支部誕生地,中國共產黨曾在這里組建“臨撫凌青綏”聯合縣工委辦事處,帶領群眾同日偽斗爭。2004年,秦皇島市將花廠峪村列為首批愛義國主教育基地;2010年,青龍滿族自治縣紅色文化開發重點項目的花廠峪抗日紀念館落成開放,革命烈士陵園奠基儀式也同時舉行。多個單位和學校曾在此組織參觀學習,全國共有22個單位在此設置培訓點。
花廠峪抗日紀念館座落于該村的中心地段,館內以冀熱遼邊區臨撫凌青綏五縣黨、政、軍、民抗戰歷程為主線,生動直觀地再現了當年堅苦卓絕的斗爭歷史。花廠峪烈士陵園位于花廠峪村祖源河北岸坐西朝東環形山坡上,與紀念館隔河相望。
訪談g:男,60歲,紀念館館長
我的父親周子豐194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過大小戰役近百場,但花廠峪口阻擊戰是讓他覺得打得最慘烈的一仗:靴腳溝突圍,敵人兵力六千多,我們只有二百多,敵我兵力相差實在懸殊,后來敵人又調集六千多名日偽軍來圍剿,當地群眾為保護受傷的戰士、掩護部隊轉移和躲避日寇屠殺,藏在峪中的山洞里。因為害怕小孩兒的哭聲暴露目標,孩子母親就用乳頭堵住孩子的嘴,日寇走了,孩子卻被活活憋死了。當時即便就是這么殘酷的情況,全村也沒有一個投降和泄密的。父親一直覺得虧欠花廠峪人民,他從沒有忘記鄉親們付出的重大犧牲,一再囑托我:“鄉親們的恩情不能忘,要替我們償還欠他們的感情債,一定要想辦法為他們辦點事。”
我在花廠峪住了12年了,從籌建抗日紀念館開始一直到現在,花廠峪的抗日歷史壯歌被更多人所熟知,我們不能忘記前輩們的不畏艱險,誓死保家衛國的英勇斗爭歷史。正是這些先烈們拋頭顱灑熱血,我們今天才能如此幸福地享受著青山綠水和太平盛世。
紅色教育影響深遠。自建館以來,來此舉辦紅色教育活動的單位與學校絡繹不絕,抗日時期花廠峪人民大無畏的精神、寧死不屈的意志感動、影響和教育著前來學習考察的每一個人。
三、結論及建議
家庭教育方面,父母親陪伴孩子機會過少,孩子與祖輩生活在一起,由于祖輩群體年紀較大從而導致教育孩子精力不足。老年群體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在學業與生活上都難以全面關注到孩子的變化,導致留守兒童的心理問題得不到及時的慰藉與疏導。盡管花廠峪村村民思想較為開明,比較注重孩子的教育問題,但如今由于各種外界因素影響,家庭教育的缺失還是較為嚴重的。今后應盡量使需外出打工但有條件的家庭留下父母一方,認真開展對兒童的家庭教育;條件不允許的家庭則要謹慎選擇托管對象,監護人則要學會運用正確的教育方式對留守兒童開展家庭教育。
學校教育方面,花廠峪小學的硬件配套設施不夠完善,整個學校只是一座二層小樓,沒有操場等供學生運動和課外活動的場地。政府應加大教育經費投入,加強配套設施建設,全面提升辦學條件,改善教學環境,促進學生德智體美全面發展。此外,全校只有兩名教師,教師人數不足,副科專業教師以及年輕教師的缺乏導致很多課程無法開設,故其小學的課程體系并不完備。在花廠峪小學,兩名教師分別負責一個年級所有課程的教學,雖然學生數量較少,但依然難以滿足每門課程的專業性。在今后應盡可能提高師資隊伍素質,引進人才,從而豐富課程體系,不斷提升教學質量。
紅色教育方面,就目前形式來看發展較好。花廠峪村紅色文化濃厚,其紅色歷史記憶使得滿漢兩族人民更加緊密團結的聯系在一起,且將這種精神延續至今。紅色教育是民族教育的紐帶,在今后應繼續深度挖掘紅色資源,加大其紅色旅游的宣傳力度,提升服務行業質量,打造紅色旅游精品,持續講好感人至深的紅色故事,使光輝奪目的紅色歷史被永遠銘記、讓紅色精神歷久彌新。
無論是從每個家庭來看,還是從民族、城市乃至于整個國家的發展來看,教育問題是刻不容緩的。知識改變命運,在知識經濟時代尤其如此,只有教育才是實現高質量發展、可持續發展的關鍵。由于貧乏的知識與落后的觀念使得我們在當前的工作與發展中遇到各種難題與重重阻力,究其根源則在于教育的不足甚至缺失。所以,重視教育、發展教育,對花廠峪村乃至青龍滿族自治縣來說具有特殊意義,想要徹底“挖斷窮根”,最為關鍵的一步就是依靠教育。教育興則國家興,教育強則國家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不可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