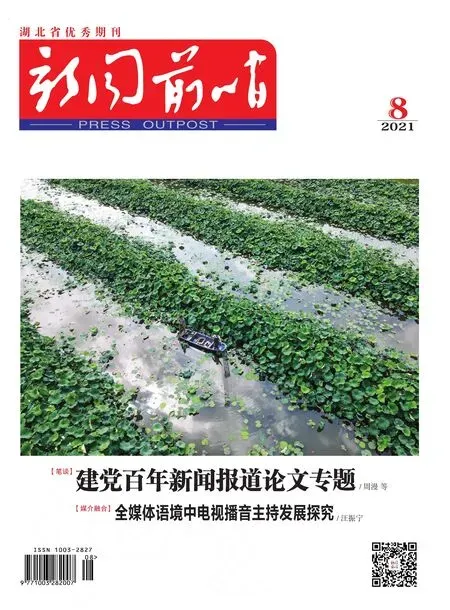融媒視域下微紀錄片創新探析
——以《早餐中國》為例
◎張 霞
伴隨社會經濟高速發展,食物不僅是人們的飽腹之物,更象征一種情感記憶,對于美食的喜愛由此引發了電視節目的“美食潮”,即便在電視節目多元發展的時代,美食紀錄片也能在其中獨樹一幟,而本文探討的美食紀錄片《早餐中國》定位于一天中的第一餐,從普通的早餐喚醒清晨的味蕾,是一部在上班通勤時間便能獲得情感愉悅的紀錄片,從2019年第一季播出到至今的第三季,豆瓣評分也從第一季的8.1分飆升至第三季的9.1分,獲得口碑和收視的雙豐收。《早餐中國》在鴻篇巨制的美食紀錄片洪流中以微觀細節啟程,搭乘媒體融合的快車,真正做到節目廣泛傳播的同時又深入人心。
一、《早餐中國》文本內容的“微”表達
媒介化社會語境下,傳者與受者在傳播過程中形成了多元互動、自由碎片式的媒介景觀,受眾審美趣味逐漸發生了“微”變化,微紀錄片便是契合新媒體的傳播特性和受眾接收方式的新興藝術形式。《早餐中國》從一開始就致力于做有溫度的美食紀錄片,不僅選擇展現日常生活中的美食,更采用契合觀眾接受習慣的短視頻形式,使其成了同類節目中的佼佼者。
1.微視角:主題的細膩化表現
食物對于人們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它在日常生活中既是維持生命能量源泉,也是追求美好生活的表征,具有重復性和普遍性的特點。《早餐中國》展現的早餐種類,可能是普通受眾日常化接受、或是有著深刻味覺記憶的早餐,甚至該節目被稱為“家門口的美食節目”。例如第一季第一集中“湖南長沙肉絲粉”,便是長沙人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能吃到的早餐,街上大大小小的粉面店也是數不勝數。雖然都是粉,各地對于粉面選擇種類也會不一樣,在第二集中就選擇貴州凱里《酸湯粉》,真正滿足了觀眾對于早餐接地氣的簡單感。另外,節目彈幕中不時出現“本地人在線打卡”“什么時候能夠去我的家鄉拍攝”、“明天就去吃這家早餐”等等,不論是長沙的肉絲粉還是貴州凱里的酸湯粉,都印證了節目選取簡單的美食最直接喚起了觀眾對于家鄉的思念,對于觀看受眾來說有著一種“人在異鄉,胃在家鄉”的情懷,這些早餐都是人們記憶中的食物,對于觀眾從日常生活來說,加強了節目實用性和貼近性。
2.微結構:視頻的精簡化呈現
麥克·盧漢曾經指出“媒介即訊息”,媒介作為不斷變化發展著的產物,當前受眾習慣觀看短視頻的形式對紀錄片的發展產生著重要影響。《早餐中國》每期以5-8分鐘的“微結構”影像,講述了現代城市中街頭巷尾早餐店中“接地氣”的早餐,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微紀錄片的呈現使得節目內容更加廣泛、主題更加凝練,是迎合現代人快節奏生活下碎片化獲取信息習慣的產物。第一季播出至今共105期節目,講述全國各地各具特色的早餐,不再對食物進行事無巨細呈現,而是簡短介紹伴以老板的話語、經典歌曲以此強調引導、抓住觀眾注意力,讓每位觀眾在上班通勤途中都能尋找熟悉味道、得到心靈愉悅。其次,《早餐中國》由騰訊視頻和福建海峽衛視聯合出品,每周一至周五早8點騰訊視頻全網獨播,海峽衛視同日晚間黃金時段重播,從第一季到第三季都是采用線上線下互動傳播模式。《早餐中國》在海峽衛視播出效果雖不如騰訊視頻反響強烈,但該節目權威性、專業性從傳統媒體中充分體現。
與此同時,在互動融合傳播中,微信、微博等網絡社交平臺對節目內容進行創新式擴充,讓節目更加豐富完備地展現出來。如節目微博話題#早餐中國#已達到5億閱讀量,參與討論熱度達到14.4萬,引發了大量網友參與,“說出你認為什么樣的早餐最能讓你心滿意足”“早餐中國里的神評論”。還如每期節目海報制作,將節目的重點提煉成一句口號,“喜歡一個城市的理由,從早餐的味道開始”“早餐是生活美學的開場白,誰說儀式感不重要”,以簡單直接的方式宣傳節目。如此一來,新舊媒體之間互相造勢,引發收視狂潮,節目的傳播范圍較之傳統媒體單一傳播更加廣泛。
3.微影像:視聽的象征性表達
美食類紀錄片追求給予觀眾視覺“盛宴”,便以食物色澤、場景營造、配音、音樂等引發觀眾食欲,以此展現精美絕倫的饕餮大餐。“符號學家們認為,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在以各種符碼的方式發送有關我們的信息。”換言之,微紀錄片制作者通過總是通過一系列符號系統在傳達某種信息,讓它們進入我們的意識層面。
《早餐中國》對食物呈現大量運用特寫鏡頭,以微觀化的視聽真實地還原食物的細節,從而將食物呈現得更加完美細致。如第一季廣東汕頭《豬血湯》老板每天清晨五點出門采購豬血,節目通過5個特寫鏡頭表現豬血的色彩鮮紅、手感扎實到文火煨制變色過程。再如第三季《澳門蛋撻》通過7個特寫鏡頭表現蛋撻烤制過程,加以老板畫外音“你烤得好的時候,蛋撻就像在跳著舞,跳啊跳啊跳給你看”,觀眾通過畫面聲音想象食物美味,激發食欲從而完成對食物的推薦,使觀眾從節目被動接受者轉化為主動參與者,獲得更為開放的觀看體驗。另外,該節目較少采用解說,而是美食制作者也就是老板本人“微語境”的自我敘述,使節目從食物本身抽離出來置于更為抽象敘述,轉向人們對于現實價值與意義的關注。也就是說,通過老板在制作節目過程的自我敘述不僅表現食物本身的特點,也建構起與觀眾之間的心理橋梁,形成紀錄片與觀眾現實生活之間的溝通路徑。
二、《早餐中國》的精神內核與文化意蘊
著名飲食文化學者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姚偉鈞所說:“飲食是國計民生中的第一件大事,對食物烹飪的宥視和考究以及人們對于飲食的觀念,表現了一個國家的文化素養和文明的象征。”換言之,美食紀錄片不能局限于介紹制作品嘗美食,要彰顯節目內涵,表達文化意蘊。《早餐中國》主題“無需早起,便能找到故鄉”,鏡頭不僅只關注食物本身,也將鏡頭對準一群生活經驗豐富的早餐店老板,通過人物制作美食,完成了美食與人情世故的融合,引發集體性的情感共鳴,呈現人性的本質、生存的價值。
1.鄉愁的話語實踐
鄉愁有著不同的維度與層次,可以是對親友的懷想,可以是對舊日時光、故園風景的眺望,也可以指對遠逝的傳統與歷史的深情眷戀。“文化鄉愁”便是第三種鄉愁,一種最深層次的鄉愁。“文化鄉愁”,簡單地說就是一種隨現代全球化平整運動而產生的文化傳統的失落感和追憶情緒。它是“現代性”文明和文化的副產品,對于現代社會和現代人類來說,具有著 “家的意識形態”(the ideology of home)的性質。《早餐中國》中的食物象征一種文化符號,節目通過選取人與食物、人與人之間聯系,體現出全球化進程中古樸的集體歸屬感。在現代化快速發展過程中,物質極大豐富的同時是以地方性歷史文化為犧牲,各個城市之間特質逐漸變得同質化。在這其中,食物成為城市形象與記憶的差別標志,能夠喚起人們心靈歸屬感。于是,該節目有意選取的與千篇一律的現代城市餐廳相對立的,位于街頭巷尾中有著年代記憶的蒼蠅餐館,旨在通過一種烏托邦式的書寫,展現對歷史年代的懷舊。以第一季湖南長沙《肉絲粉》播出彈幕中不少網友評價“回家的第一件事便是嗦粉”,還有由此聯想到有自己家鄉獨特味道的拌粉、鹵粉等,《早餐中國》在傳播過程中還潛移默化地喚起了人們對于家鄉的思念。
2.文化的儀式傳承
文化是集體或群體通過符號所習得并傳遞下去的的各種內隱或外隱的行為模式,它是經過選擇的核心價值體系,是人類活動的產物。正如美國著名哲學家大衛·霍爾曾經所言“人類生活中還沒有哪方面是不受文化的影響,不被文化所改變的”也就是說,正是因為文化是歷史流傳下來的行為模式,人們在習得的同時也在約定俗成地傳承著。《早餐中國》并不拘泥全篇呈現食物為主,每期節目以類似的結構講述故事,節目前兩分鐘呈現食物,而后通過人物講述抽象的文化概念。以《山西蔭城豬湯》為例,丈夫通過節目表達了他一生的感悟“他用自己的兩只手和老婆的兩只手,創造了現在的家庭,第一天出工只賣出了十幾碗,后面一直堅持一直堅持,就是不掙錢也干”,簡短的畫面和語言傳遞出我國幾千年來一直堅持勤勞奮斗的優秀文化。正是這些優秀文化早已深植于觀眾心中,再通過節目的儀式化表現,進一步渲染了紀錄片的強烈感染力,也引發觀眾的情感共鳴。
3.匠心精神的彰顯
融媒體時代紀錄片雖迎合觀眾習慣“短、平、快”的即時便捷,但并未因此忽略品質,使美食制作者丟失靈魂。《早餐中國》導演王圣志認為:“匠心是很普通的,每一個人都有匠心,做每件事都需要匠心。”這種“匠心精神”在節目里得到了充分展現,看似坐落在街頭巷尾的早餐小店,卻彰顯了平凡人們的匠心精神。節目中里早餐點老板幾十年如一日的堅守體現了他們對食物的“匠心”,只為恪守人們心中的經典味道。紀錄片中有《澳門蛋撻》的老板50多年的匠心制作,每日手工搟制50余遍蛋撻皮,烤出的蛋撻酥脆可口,才會食客在品嘗后對于蛋撻的無限好評。還有《驢肉火燒》中手工搟制面皮薄至透光,用火可以點著,三平方米的地板早已被磨破。《早餐中國》這部紀錄片將一群真實自然、個性特征鮮明的美食制作者對食物的工作態度呈現給觀眾,他們雖然都是小人物、每日工作也看似單調乏味,但支撐他們的是在科技制造業高速發展下仍然堅守傳統手工制作的回望,是對浮躁社會中生活的人們心靈的凈化。
注釋:
[1][美]阿瑟·阿薩·伯杰:《媒介分析技巧》,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2]王前:《中西文化比較概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3]姚偉鈞:《飲食: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基》,《南寧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4年第4期
[4]萬俊人:《經濟全球化與文化多元論》,《中國社會科學》2001年第2期
[5]薛立磊、徐燁:《早餐中國:短視頻紀錄片的一次成功嘗試》,《傳媒》2019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