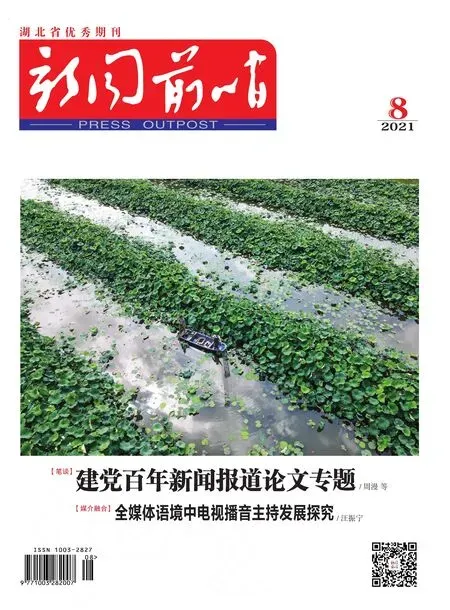真人秀綜藝節目的價值與發展探析
——消費主義視域下《乘風破浪的姐姐》解讀
◎舒 怡
《乘風破浪的姐姐》(下文簡稱《浪姐》)自2020年6月12日開播至9月4日成團夜收官,持續引發社會關注和討論。相關數據顯示,節目的微博話題閱讀量高達1000多億,微博熱搜榜優質內容600多條,微博話題談論量2000多萬,短視頻播放量9億多,綜藝熱搜人氣值第一。盡管節目整體熱議度極高,但若以周為周期進行數據分析則會發現,節目本身呈現出高開低走之態,節目第一次公演之后綜藝節目微博話題閱讀量等各項數據均到達峰值,此后呈現波動下滑。節目口碑也逐步下滑,從節目上線四天播放量3.9億、豆瓣評分8.6分跌至目前的7.0分。本文從消費主義視角分析節目文本,探析真人秀綜藝節目的價值與發展。
一、創新與守舊:消費主義下的節目生產
1.原創節目主題
作為國內首檔逆齡女團選秀節目,《浪姐》大膽突破《青春有你》等系列熱播養成系選秀類真人秀綜藝的年齡設定,一改傳統的小鮮肉小花選秀模式,啟用有一定資歷的女性藝人作為參賽選手,創新又精準地將受眾定位為30+人群,直面年齡問題,補充了選秀市場的空白,可謂是“舊瓶裝新酒”。在消費主義的社會背景下,傳媒在傳播實踐中對傳播內容的“可消費性”高度重視,媒體會傾向生產更受受眾喜愛的媒介內容。自2014年,湖南衛視、浙江衛視從韓國、歐美等地購買優質節目版權制作并播出《爸爸去哪兒》《中國好聲音》《奔跑吧,兄弟》等節目獲得觀眾喜愛后,國內綜藝節目制作市場便掀起了一股“拿來主義”之風,甚至競相模仿、抄襲、土味改編等等,同時還有一些引進節目在內容制作時只一味套節目模式,不注重本國國情,紛紛“水土不服”,這些都直接造成了今年來國內綜藝節目生產創新性、獨特性、內容性極差,市場上“劣幣”驅逐著“良幣”,而《浪姐》的火爆也證明了消費主義主導下的社會仍舊是以內容為王的。
2.凸顯社會焦點
近年來,現實中隨著生產技術的發展,社會經濟、文化、政治也隨之變化,女性受教育率提升,生產和創造價值能力提升,社會生產結構改變,女性的實際話語權提升,女性消費能力和獨立性大大提高,隨之大眾對于年齡焦慮的痛點也被放大,如“剩女”等。近年,“她經濟”影響下媒體不斷推出以女性MC為主的觀察類節目。《浪姐》的出現正是迎合社會需要,直擊社會痛點的存在。在節目對象上,它以30歲以上的姐姐為捕捉點,開創中年女性綜藝的先河,突破傳統女團打造偶像的框架,打破年齡歧視。同時,在節目內容上,它聚焦30位不同的姐姐個性化的行為和迥異的性格特征,呈現中年女性的多樣性,展現女性獨立的美好。《浪姐》消解女性“工具性”,賦予女性話語權。在節目中,女性可以是妻子、母親的身份,更可以單身追求自己喜歡的生活。在這里,女性主動追求自我表達和展示,彰顯中年女性價值,勇于打破社會對性別和年齡的偏見。此外節目中還有意呈現社會各界認真工作的女性們,大膽肯定女性價值的同時也為屏幕前的女性呈現無限可能。
3.難逃消費定式
盡管《浪姐》在節目形式和價值定位上都有不小的突破,但節目并沒有能夠擺脫經濟杠桿的束縛,節目始終難掩女性身體消費的理念。節目給觀眾呈現出來的是,女性無論年齡有多大,依然可以擁有外貌上的年輕,這何嘗不是身體年齡的刻板印象。當觀眾對比屏幕中姐姐們完美的身體時,會產生身體自卑感和向往感,降低了自我認同,從而會通過購買一系列消費品等多種方式來試圖縮小差距,當消費力不足時則極其容易產生自我不認同。而這種超越男性對外觀追求的價值觀念,表面上看是女性想要悅己,實質上仍舊是男權社會對女性身體的壓迫,是追求由男權社會和消費社會共同生產出來的“標準美”。節目只是告訴了觀眾,無論幾十歲,女性還是可以通過挑戰與突破保持美麗和魅力。事實上,直接抹掉了大眾可以選擇擁抱自然的衰老,眼角的皺紋與松弛皮膚未嘗不是大自然賦予人類的美好。
二、奇觀與快感:真人秀節目的消費本質
消費可分為三種即看與被看的身體消費、自我代入的情感消費和身份認同的符號消費。
1.看與被看的身體消費
看與被看的首先是姐姐們的身體。身體作為消費延展,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明星姐姐們姣好的面容、完美的身材滿足了人們視覺的審美需求;二是通過明星自身的消費引領、帶動受眾的消費,最顯著的例子就是《浪姐》帶來的梵蜜琳的品牌神話,幾乎一個夏天,梵蜜琳就因冠名《浪姐》而眾人皆知。其次看與被看的有明星的私人生活,參與者的內心欲望。電視屏幕為觀眾建立了一道安全線,大眾得以脫離現實環境,站在自身之外瘋狂窺視著另一群人的生活和內心,更有甚者站在道德的高地加以評判,從而滿足自己的好奇心,迎合自身的窺私欲,達成另類的自我認同,從而產生心理快感,這種快感催使觀眾沉迷于節目,并輕易接受節目輸出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如女人愛自己就要給自己買好的護膚品等。
2.自我代入的情感消費
以《姐姐》等選秀節目為代表的養成類選秀節目通過節目形式、觀看方式、投票主導等多方面建立與觀眾的深層互動,觀眾在觀看節目的同時也擁有著決定選手去留的權利,觀眾也因此會傾注大量的感情,大喊“某某某只有我們了,快去給她投票啊!”“你不投,我不投,XXX何時能成團”等等。另一方面,節目的主題往往就是夢想、成長、愛等,在呈現歌舞舞臺的同時,也會展現姐姐們的日常生活和排練生活,如呈現萬茜車禍受傷后住院和在醫院內堅持練習的片段,臺前臺后的交錯剪輯,使得觀眾更容易在細碎的真實事件里找到與自己生活相關的事情,代入自己的親身經歷,使觀眾將個人的情感轉嫁到姐姐們身上,形成情感共鳴,從而觀眾會產生事情解決、困境突破、夢想實現的滿足感,這是一種虛假的參與感,實質是觀眾在消費主義操縱下的集體狂歡。
3.身份認同的符號消費
庫利曾經以“鏡中我”概念來隱喻人的認同構建,包含三方面的內容:一是我所想象的,我在別人面前的形象;二是我所想象的,別人對我形象的評價;三是由上述兩方面引出的某種自我感覺,如屈辱、自豪等。《浪姐》就是一面巨大的女性之鏡,呈現了30種不同的鮮活人生,觀眾在觀看過程中會對與自己某些方面、經歷相似的姐姐產生角色認同,進行自我投射,癡迷其表現,認同其表現出來而自己并未擁有的優秀品質,在某一瞬間幻覺滿足觀眾自我滿足的愿望。但現實始終不同于幻想,觀眾在觀看節目中不自覺地產生對比,形成落差,最顯著的便是身體外貌的差異,這種差異帶來的落差感催使觀眾通過購買、消費的方式縮小兩者的差距,從而形成進一步的自我認同。節目的充斥了服飾、化妝品、營養品等的的廣告,姐姐們成為“青春活力”“成熟貴婦”“好媽媽”的代言人代言梵蜜琳、佳貝艾特、瓜瓜龍等產品,通過姐姐們個人魅力和觀眾縮小身份差距兩重因素引導著觀眾進行消費。
三、肯定與批判:真人秀節目的價值判斷
1.人文關懷,給予表達機會
“作為大眾文化的電視也并不只是擁有鮮花和陽光,它也擁有自己的社會母題,擁有理性思索具體表現為社會與民族性,心理積淀與時代性,以及政策性。”真人秀繼承了電視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它以人為中心。一方面,它尊重人的權利,給予大眾自我表達的舞臺,滿足大眾娛樂的需求。《浪姐》這個舞臺給大齡女明星、女演員們提供了的一個自我表達的盛大舞臺,姐姐們在這個舞臺中學習、拼搏、表達自我,再次被公眾看見,實現個人的價值增值。另一方面,它強調人的價值,關注人的命運。《浪姐》主動聚焦社會熱點女性年齡焦慮、刻板印象問題,通過展現30位大齡女明星的個性特征、生活現狀,以及社會各個職業里女性的身影,弱化女性與年齡的矛盾,向大眾傳遞著年齡不是束縛女性發展的繩索,刻板印象不應成為女性發展的牢籠,現代女性就要“不被定義”、不懼年齡、勇敢向前,全力展現著女性生活的多樣性。
2.娛樂至死,審美價值異化
正因比賽只能有一個冠軍,選秀只能有寥寥數個成團名額,從一開始《浪姐》這類選秀節目的開展本質就是對多樣性的抹殺,從側面告訴了大眾,也許不是只有冠軍所具備的品質才能成功,但這就是你現在所能看到的成功模板。選秀的形式從某種意義上統一了大眾的審美,而決定這種統一標準的正是市場,大眾的審美標準在不知不覺中被改變了。《浪姐》第一期的舞臺是每個人的自備舞臺,形式、選曲、發型、服裝都由姐姐們自己決定,沒有彩排,直接真唱,不來虛的,舞臺千人千樣。一期之后,姐姐們極快地認識到,勁歌熱舞更容易晉級,因此節目組的選取從開始的風格多樣,到后來的多以流行舞曲為主,歌唱也清一色是假唱。
盡管真人秀作為文化產品,承擔了傳遞社會價值的責任,但也不能逃脫娛樂商品的范疇。消費和娛樂的本質注定了真人秀節目必須想盡辦法提升收視率,拉動經濟消費。《浪姐》的高開低走正在于此,節目伊始的價值倡導吸引了被撕逼、賣慘節目圍繞的觀眾,但后期分團、剪輯帶來的各種爭論已經遠遠超過了對節目主題的關注。尤其是成團夜,盡管節目組請來了中國女排等女性代表角色,但網絡熱議的卻是寧靜的“我拿第一,不想成團”的爆炸言論,是萬茜手滑點贊黑郁可唯寧靜帖子。大眾在這場狂歡里追逐快感、娛樂至死。
注釋:
[1]數據來源:新浪娛樂微博#一周綜藝直播戰報#和#綜藝勢力榜,該數據統計時間范圍為6月12日至9月10日
[2]秦志希等:《媒介文化新視點》,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3][美]歐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黃愛華、馮鋼譯,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4]洪艷:《電視選秀節目的批判分析》,《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