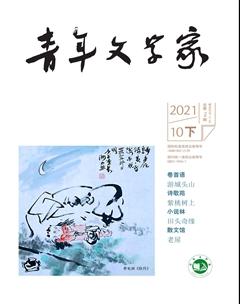五哥
趙天賜
“山灣”是個(gè)不大不小的盆地,四周環(huán)山,中間有一條東西走向的松花江,如過客一般緩緩駛?cè)耄o靜流出,從不打擾“山灣”里的世間萬物。老一輩人經(jīng)常對小輩念叨,“山灣”是命根,從“山灣”里走出的孩子要有德行,不能忘本;老一輩人還說過不要妄想逃出“山神”的手掌心。
老人們說過很多的話,有的留下了,有的被遺忘了,本來這些話是要集成冊子或刻在石碑上的,但至今都沒有人能完成這個(gè)“宏大”的工程。我很困惑,曾用白菜心大小的腦容量認(rèn)真分析老人們說過的話,卻總也想不出個(gè)子午卯酉,更不敢嘀咕出來。五哥比我勇敢,在我眼里心上他是個(gè)勇士,是一個(gè)敢于直面慘淡人生的勇士,為什么說他能夠直面慘淡的人生?五哥也曾這樣問過,我告訴他,一位偉大的文學(xué)家兼思想家“魯老爺子”說過: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
五哥每次聽我這樣的夸贊都會搓一搓頭發(fā),抹一抹臉。他說這是先人借用我的口對他的鼓勵與鞭策,憑我這锃亮的腦袋是絕對說不出這樣偉大的醒世格言。五哥說要向“魯先生”看齊,要懸壺濟(jì)世,要批判社會的不公,要正一正社會的風(fēng)氣。在我們眼里,社會很大,山以內(nèi)的都叫社會,山外的是什么?我只聽五哥說過“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shí)秋”,所以我覺得山外有青山,有高樓,有西湖,有歌舞,五哥說我是個(gè)土包子,只會啃書本,不知世界之大,不知煙波浩渺。五哥說得沒錯(cuò),我只會啃書本,僅能記住書上的幾句話,僅會背幾首課本上的詩句,但我還是很想知道山外面到底有什么。
“五哥勇士,你說山外面還有啥啊!”我遞給他一個(gè)夾了咸菜的饅頭,“咸菜是我媽做的,她說你瘦,得多吃點(diǎn)。”
“這個(gè)嘛,說多了你也記不住,知道那么多干啥!”他斜了我一下,躺在稻草垛上,咬了一口饅頭。
“五哥,我也要做勇士,不,是做勇士的跟班,誰要欺負(fù)你,我就揍他。”
“就你?瘦得像狗尾巴草,風(fēng)一吹就倒了。”他又咬了一口饅頭,望著天上的云怔怔出神。
“五哥,別舍不得吃,我家還有豬肉餡的包子,這就給你拿去。”我欲起身,五哥便把我喚住了。
“天兒,你看這云一會兒變成羊,一會兒變成馬,一會兒變成鳥,一會兒變成魚,地上有的天上都能變出來。”他叼起草棍,蹺起二郎腿,把我按了回去。
“山外面有人,他們都背著書包游山玩水,山外面有樓,比五指山還要高的樓。天兒,我要做天上的云,自由自在地飄,想怎么飄就怎么飄,高高在上地飄,要飄到上面去,飄到比五指山還要高出一個(gè)五指山!”
“五哥,那飄不出去呢?”我擔(dān)憂地看了他一眼,“聽奶奶說咱們都命中注定要待在山里伺候莊稼,插上翅膀都飛不出去。”
“沒出息,看你那針鼻兒大小的膽兒,挖地洞我也要把這座山鉆出一個(gè)窟窿。”五哥騰的一聲站了起來,油亮的頭發(fā)上插滿了細(xì)碎的稻草,他深深地吸了口氣,一瞬間迸發(fā)出來,直沖云霄。天空的老鷹盤旋了一圈又一圈后飛走了,電線桿上成群結(jié)隊(duì)的烏鴉剎那間四散開來,村子里不知誰家的狗大聲地叫,遠(yuǎn)處飄來了一股旋風(fēng),卷起了一堆又一堆枯敗的稻葉,帶著一粒又一粒塵土飄向遠(yuǎn)方。我思緒雜亂,無處安放的眼神終于找到了指甲縫里殘留著的深綠的咸菜葉,母親一遍又一遍的呼喚聲將我拉了回來,在挪了一小步后便撒開了腿奔向家里。
我好像忘記了離別時(shí)對五哥的鼓舞,但我會如往常一樣一直鼓舞他:五哥是個(gè)敢于直面慘淡人生的勇士。我的頭發(fā)剃了好幾茬,剃頭的次數(shù)少了,見到五哥的次數(shù)也少了,從半個(gè)月一次,再到半年一次,最后一年一次。頭發(fā)春天剃掉,冬天留起來,就像我家里養(yǎng)的那幾頭羊一樣,剃頭的推子也是剃羊的推子,我就是羊,羊也是我,誰是羊,誰是人,在我眼里都不及五哥重要。我很憔悴,像一根黃瓜一樣,由外到內(nèi)的憔悴。憔悴到看見水銀便想起了時(shí)間。
時(shí)間凝滯般緩緩地流動,與其說流動,不如說“蛄蛹”,往前一段的同時(shí),也得向后退一步。在我的意識中時(shí)間就是這么個(gè)樣子:頭發(fā)剃掉了,個(gè)子長高了;山羊下崽了,老羊賣掉了。我好像窺到了時(shí)間的流動,卻瞧不明白五哥的心思。五哥說得對,腦袋锃亮的我,想也想不出什么東西。在我眼里,月亮一天一個(gè)樣,不是大一點(diǎn),就是小一點(diǎn);太陽也還是那個(gè)太陽,再怎么變換顏色,我依舊能認(rèn)出它。當(dāng)我小學(xué)六年級的時(shí)候,就不再觀察太陽和月亮了,與山灣里的孩子一樣,走上了父輩祖輩都曾走過的路—伺候莊稼。山灣里的人都說莊稼是綠色的,我看不出綠色,從遠(yuǎn)看往近瞧,即便拿出放大鏡看,莊稼的細(xì)枝末節(jié)也都是磚青色的,這種顏色只有我和五哥見過,還是他告訴我的,山外有山,有樓,有青磚青瓦的樓。
在我剛剛學(xué)會如何播種,如何插秧,如何撒肥的時(shí)候,五哥來看我了。他衣著樸素,身上有股淡淡的香味,我在阿花的身上聞到過這種香味。五哥長高了,他背了一麻袋的書放在我家里,說是送給我的,但被我母親扔了出去。五哥與母親大吵了一架。轉(zhuǎn)天一早,母親給我?guī)Я烁杉Z,一把鼻涕一把淚的把我和五哥送上了前往山灣盡頭的牛車。牛車緩慢地走著,我和五哥枕著用麻袋包裹的行李,身下的雜草細(xì)軟撫人,天空中的老鷹帶著小鷹一圈又一圈地盤旋著。五哥說他已經(jīng)走出了一條路,也想帶著我走這條路,他說人就是云,云散云聚,緣生緣滅,一切都是順其自然,但是過于自然也不好,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我崇拜地看著五哥,他搓了搓頭發(fā),抹了抹臉說道:“是‘魯老爺子說的。”我們都笑了起來,笑得自然、灑脫,空中的老鷹踩著云朵劃走了,漸行漸遠(yuǎn),只能聽到風(fēng)聲與老牛的響鼻聲。
我記不清什么時(shí)候坐上開往縣城的客車,更記不清什么時(shí)候上的中學(xué)。對我來講時(shí)間就是一堆藏在地窖里的白菜,存得久了就爛了,也像倉子里擺放的一顆顆大蔥,時(shí)間長了也就枯干了。我意識到人得往前看,向前走,畢竟時(shí)間總體上還是前進(jìn)的,跟它掰腕子、摔跤,永遠(yuǎn)贏不了。于是我蹲在宿舍里,躺在操場上,不斷地看書。為什么看書呢?我不知道。但是五哥臨走前告訴我,真正的勇士是需要讀書,因?yàn)橛率康妹鎸K淡的人生,所以要提前做好準(zhǔn)備。我問五哥緣由,五哥說,讀書就像插秧,插秧前得買種子、化肥,但是這些都不夠,還得支大棚、育苗,火候到了,才有資格插秧、施肥,最后才會有收獲。我非常認(rèn)同五哥的說法,也更加明白,做什么都像插秧一樣,得認(rèn)真踏實(shí),還得有遠(yuǎn)見、有計(jì)劃。五哥就是我的遠(yuǎn)見,就是我的計(jì)劃,他說我不僅身體弱,精神上更弱,警告我別胡思亂想,做好功課,多讀書,讀好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