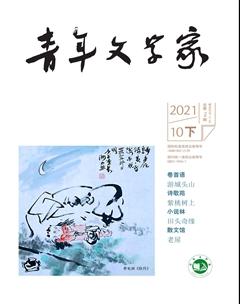李季蘭詩歌審美探析
于慕清
李季蘭是中唐時期重要的一位女詩人,歷代文學家對于她的詩歌創作都給予了較高的評價。文章通過對李季蘭詩歌文本的解讀,并參考歷代文學家的相關評述,旨在盡可能真實地還原李季蘭在詩歌之中蘊含的真情實感,并對她詩歌中蘊含的審美情感以及審美體驗進行詳細的闡述。
李冶,字季蘭,中唐女冠詩人。季蘭詩現存18首,全唐詩收錄16首,補遺2首。劉長卿稱她為“女中詩豪”;陸昶贊賞她的詩:“筆力矯亢,詞氣清灑,落落名士之風,不似出女人手,此其所以為女冠歟!”季蘭雖為女性,但在她的詩歌中卻不乏男子的豪情氣概。元人辛文房在《唐才子傳》中也收錄了李季蘭的作品,這從側面反映出他對于季蘭之詩持肯定的態度,甚至認為其可與男兒比肩。沈善寶在《名媛詩話·自序》中提到:“竊思閨秀之學與文士不同,而閨秀之傳又較文士不易……閨秀則既無文士之師承,又不能專習詩文,故非聰慧絕倫者,萬不能詩。”季蘭身為一名女子,她的詩能夠與當時的閨怨之作呈現出截然不同的藝術風貌,甚至超出許多同時代的男子,可見她的藝術造詣非常人所能及,這與她個人的生活經歷以及她所處的時代環境是息息相關的。
唐代的統治者對文化采取兼容并包的態度,李季蘭就在這種相對寬松的文化環境中成長,女冠的身份使得她更注重現實的享樂,傳統觀念中對女性的約束也更加寬松。她出家為道使她有更多的機會能夠與鴻儒交往、詩酒唱和,女冠的身份也使她不必拘泥于傳統理法的約束,亦可率性而為。在當時,與季蘭交往的名士眾多,有劉禹錫、劉長卿、陸羽等。《太平廣記》中載:“秀蘭嘗與諸賢會烏程縣開元寺。知河間劉長卿有陰疾。謂之曰:山氣日夕佳。長卿對曰。眾鳥欣有托。舉坐大笑。論者兩美之。”那個時代大膽至此的女性中,李季蘭當屬第一人。她同各個階層的名士交往,借此排遣自己精神上的孤獨與生活中的寂寞,可惜她生不逢時,這種恣意放縱的態度常常被看作“失行婦人”的代表。
李季蘭生活在一個開放、寬松、活躍的時代,使得她能夠充分發揮自己的文學才能,是她的幸運;但傳統意識給予女性的種種桎梏,也造成了她命運的曲折與不幸。《太平廣記》載:“李秀蘭以女子有才名。初五六歲時,其父抱于庭。作詩詠薔薇,其末句云:‘經時未架卻,心緒亂縱橫。父恚曰:‘此女子將來富有文章,然必為失行婦人矣。竟如其言。”這樣一則閑話揭開了她這一生的坎坷,年紀輕輕的季蘭被送入道觀一生與青燈古佛為伴。從她的父親開始,大家都以傳統禮教捍衛者的身份去反駁、曲解她,以“失行婦人”的眼光去看待她,哪怕是她中意的知己也以可有可無的友人身份去定義她,終其一生也未能改變。季蘭得不到知音,只能在泛愛中求偶,故而她的詩歌大多表達自己與眾位友人的深情厚誼,呈現出情意真摯、洗練流暢的特點。我們可以通過分析季蘭的具體詩歌對于她詩中特有的審美傾向進行探討。
一、審美情感的纖細與隱秘
劉勰認為:“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詩歌是人類情感的自然流露,審美的情感一方面受到審美對象的制約,另一方面又受到審美主體的影響。人所先天擁有的喜、怒、哀、懼、愛、惡、欲“七情”,都會影響到審美情感的表達,最終反映在詩歌中,就形成了不同的審美偏好。我們可以從季蘭具體的詩歌創作進行分析,探討季蘭詩歌形成這種獨特審美情感的原因。
李季蘭以五言詩獨擅一時,“如《寄校書七兄》詩、《送韓揆之江西》詩、《送閻二十六赴剡縣》詩,置之大歷十子之中,不復可辨。其風格又遠在濤上,未可以篇什之少棄之矣”。這里講季蘭詩可與大歷十才子比肩,并認為二者創作的差異“不復可辨”,雖有抬高之意,但正是作者看到了二者的創作之間的關聯。二者關聯之處在于都喜歡借助凄涼、衰颯的意象去傳達自己難以直言的隱秘情緒。如在《湖上臥病喜陸鴻漸至》詩中開篇說道:“昔去繁霜月,今來苦霧時。”借“繁霜”“苦霧”之極寒烘托作者抱病的可憐情狀以及孤苦無依的心理狀態。題目中作者與友人重逢雖說是“喜”,實則悲喜交加。“相逢仍臥病,欲語淚先垂。”一個“仍”字點出了作者抱恙已久,仿佛責怪友人姍姍來遲的情狀。時隔多年再與友人重逢,作者滿腔的委屈、憤懣、孤獨之情一時間沖上心頭,連話語都無法勾連成一句,只有滿目傷心淚能夠傳達出作者此刻無法訴說的復雜情緒。鐘惺在《名媛詩歸》中評價此詩:“微情細語,漸有飛鳥依人之意矣。”正是看到了季蘭詩中“蓄”的一面,《說文解字》中注:“蓄,積也。”我們既可以把“蓄”看作是審美感情表現一種方法,也可以看作是在詩歌中委婉的表達。她婉轉的表達方式讓我們能夠領略季蘭心中對于陸鴻漸的那份少女柔軟嬌憨的情態。作者以女性細膩的感官更容易體察到時節氣候的變換,對于“寒冷”“孤苦”的處境比起男人更覺敏感、悲涼,所以她在詩歌中借用了這些隱秘的意象將她難以直言的傾慕之情含蓄地表達出來。
季蘭詩中表達情感最為隱秘曲折的還屬《感興》,唐代處在皇權社會最為繁榮的時期,對于女性的壓迫雖然有所減輕,但是當時社會思想傳統的一面依然根深蒂固擠壓著女性的生存空間。她深受這種制度的殘酷禁錮和束縛,在詩歌中把自己不為世俗所容的愛憎、恩怨都大膽地借助她獨有的意象含蓄地表達出來。“玉枕只知長下淚,銀燈空照不眠時。”是作者長伴青燈古佛之時內心對于愛情、世俗向往的映照。道教以清規戒律限制俗世之人,作者雖身處道觀,但內心仍與紅塵有萬般糾葛,對于愛情的追求更是狂熱和迷戀。夜深人靜之時,作者不禁潸然淚下,回憶起與愛人之間的美好過往,自己此時此刻的孤寂思念更加痛切。“玉枕”“銀燈”都是女子閨閣中的常見陳設,它們見證了作者喜怒哀樂的心路歷程。“長下淚”“不眠時”更是極言思念之痛苦。末句“卻憶初聞鳳樓曲,教人寂寞復相思”中季蘭所抒發的應該更近于李白《鳳凰曲》中的題旨,而非《鳳臺曲》原本所述的游仙之意,詩人仰慕簫史、弄玉雙雙成仙而去,又為他們離開人間而感到哀傷。想起自己初聞《鳳臺曲》之時,良人還陪伴左右,如今只剩她一人與寂寞為伴,又勾起了纏綿無盡的相思之情。在《感興》一詩中,詩人表面上平淡地敘寫自己的相思之苦,卻將分別之煎熬、思念之痛苦、相思之綿長表達得淋漓盡致。季蘭身處的環境與她纖細的情感造成了她無法紓解的痛苦,因而在她的詩中,我們常常能看到她在情與禮、現實與理想之間的無法消解的矛盾與痛苦。季蘭與名士交際甚廣,他們之間的知己之情既不似愛情奔放,也不似友情直率,將這種復雜的情誼反映在她的詩里就形成了這樣一種隱秘、幽曲的情緒,借助她纖細的感知表達出來,就形成了她特有的審美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