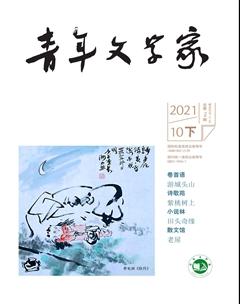泥土芳香少年時(shí)
侯廣安
我出生在吉林農(nóng)村,在那里度過了美好的少年時(shí)光。記得小時(shí)候,我剛記事時(shí)就會(huì)沒完沒了地向媽媽提很多問題,媽媽總是不厭其煩地回答我,而我問得最多的就是:“媽媽,我是從哪兒來的?”媽媽就會(huì)笑著對(duì)我說:“你是從大地里長(zhǎng)出來的呀!”
也就是從那個(gè)時(shí)候起,我總以為人就像小草、小樹或者莊稼一樣,也是從泥土里長(zhǎng)出來的。
我的爸爸媽媽都是農(nóng)民,童年時(shí)家里生活條件很艱苦,而在鄉(xiāng)下生活的我們對(duì)外面的世界又是一無所知,但廣闊的天地卻給我們提供了自由展示的舞臺(tái)。我們村的一群孩子可以不受任何約束,盡情地打鬧、玩耍,撒著歡兒地在大地上奔跑嬉笑。
在農(nóng)村,沒有專門照看孩子的地方,但我們獨(dú)自在家大人們又不放心,很多時(shí)候,我們就跟在爸爸媽媽的身后,來到自己家的莊稼地玩耍,孩子們基本都是在這巨大無比的天然游樂場(chǎng)里玩泥巴長(zhǎng)大的。那樣的天然游樂場(chǎng)是和大地緊緊連接在一起的,是孩子們健康成長(zhǎng)的樂土。
每次都是家長(zhǎng)把孩子們帶到地里后,就不再管了。大人們開始犁地、播種、撒肥,我們這些小孩子很快就湊到一塊兒,一會(huì)兒捉蟲子、逮螞蚱,一會(huì)兒抓小鳥、攆兔子,玩得別提有多開心了。小女孩兒就在地頭,三五個(gè)一起,玩她們自編自導(dǎo)的游戲。
我們開始在大地里盡情地狂奔、打鬧,可勁兒得蹦啊!跳啊!這時(shí)也有個(gè)別孩子開始揚(yáng)土,一時(shí)攪得大地塵土飛揚(yáng),再看我們,個(gè)個(gè)成了大花臉,汗水和塵土在我們臉上早就和了泥,但我們只知道取笑對(duì)方的臉太臟了,卻不知道自己也是滿臉泥土。
瘋累了,我們就偷偷用水和稀泥玩兒,這不能讓大人看到,因?yàn)槟菚r(shí)各家地里還沒有澆灌的水井,這些水都是大人們帶來喝的。當(dāng)然,要是我們誰(shuí)說喝水,家長(zhǎng)是不會(huì)阻攔的,就怕我們禍害水,等到大人們渴了想喝水就沒了,誰(shuí)都知道大熱天沒水喝的滋味是很難受的。
我們中有的孩子很快把泥和好,把泥土當(dāng)成了玩具玩的興高采烈。但畢竟那時(shí)我們還小,玩著玩著,就感覺到累了、困了。這時(shí)大人都在干活,哪兒顧得上我們,而我們也不管那么多,順勢(shì)躺倒在松軟的泥土中,感覺跟家里的土炕也差不了多少,可以舒舒服服地睡一覺。有時(shí)大人們聽不到我們這邊的動(dòng)靜,就會(huì)隔老遠(yuǎn)喊上一句:“孩子們,可別在地上睡著了,會(huì)著涼的!”但更多的時(shí)候他們根本顧不上往我們這邊看。我的嘴巴里嚼著一根不知名的香甜青草,眼前野花搖曳,漂亮的蝴蝶一會(huì)兒飛過去,一會(huì)兒飛過來,小鳥也在眼前掠過,躺在藍(lán)天白云之下,很快就睡著了,有時(shí)也會(huì)被夢(mèng)中的打鬧驚醒,但感覺那一切都很輕松舒暢,沒有一絲驚恐。
有時(shí)我們跑得遠(yuǎn)了點(diǎn),大人們看不到我們的人影兒,就會(huì)扯開嗓子大喊幾聲我們的乳名,空曠的土地上,呼喊聲被風(fēng)送得很遠(yuǎn),我們聽到喊聲知道估計(jì)是讓我們過去吃飯,即使玩興正濃,我們也會(huì)馬上扔掉手中的泥巴,大步向自己的爸爸媽媽身邊奔去。
這時(shí),爸爸媽媽看到我們滿手泥巴,滿臉塵土,不但沒有責(zé)怪,還會(huì)笑瞇瞇地說上一句:“看你們都瘋成啥樣了,也不知道餓呀?”在爸爸媽媽眼里,土地是最親密的伙伴,是大地養(yǎng)育了我們祖祖輩輩,在他們的意識(shí)中,泥土是最好的東西,只有在泥土里摸爬滾打過的孩子,才能結(jié)實(shí)無比地健壯成長(zhǎng)。
現(xiàn)在回過頭來想想,我還是認(rèn)為一個(gè)人的童年或者少年,最好多與土地接觸,最好能在鄉(xiāng)村度過。因?yàn)椴粌H是人類,包括動(dòng)植物都是來自土地,生于土地,最后還要回歸土地……
我在鄉(xiāng)村度過的那些與土地打交道的日子,是那樣歡樂和充實(shí)。可到了林區(qū),隨著城鎮(zhèn)化的推進(jìn),這里的孩子們的童年離土地越來越遠(yuǎn),我真心希望這里的孩子們也能有機(jī)會(huì)走進(jìn)自然,多多感受一下泥土的芳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