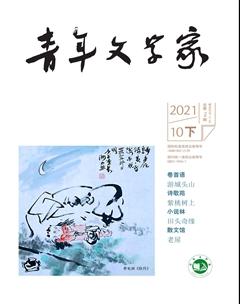李白《行路難》(其一)主旨研究述評
韓卓希
李白《行路難》(其一)的主旨問題一直為古今學(xué)者所重視。由于背景參照、辨析方法、闡釋路徑不同,主要分為“積極進(jìn)取”和“棄世遁逃”兩說。通過對諸家說法進(jìn)行梳理、辨別,發(fā)現(xiàn)“棄世”說一派挖掘了較多內(nèi)證材料以支撐觀點,而“進(jìn)取”說一派所舉的例證則數(shù)量有限、力度不足。同時,由于李白《行路難》組詩與《紀(jì)南陵題五松山》、《古風(fēng)》(其二十九)、《經(jīng)亂離后天恩流夜郎憶舊游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等詩表述相似、表達(dá)相同,因此《行路難》(其一)應(yīng)是以棄世遠(yuǎn)遁為主旨,表達(dá)了對天寶三載蒙譏去朝一事的沉痛與失望。
作為李白作品的重要組成部分,《行路難》組詩一直受到古今學(xué)者的充分關(guān)注。但由于李白“語多率然而成者”,導(dǎo)致詩旨釋義常常存在多解性和不確定性。在《行路難》組詩主旨理解中,前輩學(xué)者雖形成了一定的共識,即認(rèn)為《行路難》組詩承襲了樂府古題,以“備言世路艱難離別悲傷”為主旨,但在《行路難》(其一)的解讀上仍存在分歧。諸家對《行路難》(其一)的主旨研究,由于背景參照、辨析方法、闡釋路徑不同,呈現(xiàn)出一種駁雜面貌。而諸家所提出的觀點,不僅關(guān)乎對詩文原旨的闡釋,還涉及對李白政治活動、文學(xué)創(chuàng)作等方面的考訂與解讀。因此,探究《行路難》(其一)的主旨,需梳理諸家說法,厘清各派的研究脈絡(luò)與例證方法。
一、古代:從章句釋義出發(fā)
古人對于李白《行路難》(其一)主旨的解讀采用了中國傳統(tǒng)詩歌分析方法,或進(jìn)行直覺性的篇章釋義,或抓住意象、典故進(jìn)行句子解析,由此分為兩派。
一派認(rèn)為李白《行路難》(其一)沿襲樂府“世路艱難”的主旨。胡震亨認(rèn)為:“《行路難》,嘆世路艱難及貧賤離索之感。古辭亡,后鮑照擬作為多。白詩似全效照。”(《李杜詩通》)胡震亨認(rèn)為,李白所作《行路難》三首皆效仿鮑照,沿用樂府“備言世路艱難及離別悲傷之意”的原旨,表達(dá)“嘆世路艱難及貧賤離索之感”。明人劉鑒、朱諫持此解。此外,王文濡從用典的角度進(jìn)行補充,他認(rèn)為結(jié)語“直掛云帆濟滄海”一句化用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論語·公冶長》)典,“以明無復(fù)望用意,遂決志歸隱,不復(fù)留戀作結(jié)”。
另一派著眼于《行路難》句意解讀,認(rèn)為李白《行路難》(其一)將樂府原旨改為了積極進(jìn)取之旨。葛立方將《行路難》(其三)前四句解讀為對許由、伯夷等孤高名士的鄙棄,并以此為據(jù)指出《行路難》(其一)旨在“進(jìn)為”。這一論斷有斷章取義之嫌。首先,由于沒有直接證據(jù)證明《行路難》(其三)主旨能完全代表《行路難》(其一)主旨,因此是否能以《行路難》(其三)為判斷依據(jù)存在可商榷之處。其次,在對《行路難》(其三)的主旨解讀上,葛立方亦存在誤讀。詩歌結(jié)尾處寫道:“且樂生前一杯酒,何須身后千載名。”這直接表現(xiàn)了李白對于名利的擯棄,又何來“進(jìn)為”之說呢?嚴(yán)羽將此句詩釋為“上掃世外名,下掃世間名,都盡”,應(yīng)是正解。此外,《唐宋詩醇》認(rèn)為:“冰寒雪滿,道路之難甚矣。而日邊有夢,破浪濟海,尚未決志于去也。后有二篇,則畏其難而決去矣。此蓋被放之初述懷如此,真寫得‘難字意出。”《唐宋詩醇》通過對“閑來”“長風(fēng)”兩句進(jìn)行分析,認(rèn)為李白在此詩中仍有進(jìn)取之心。明人劉咸炘(1896-1932)同樣持這一論,他在《風(fēng)骨集評》中寫道:“渡河、登太行,濟世也。冰雪譬小人,猶《四愁詩》之水深雪霧也。溪上夢日邊,身在江湖,心存魏闕也。”諸家從句意著手,認(rèn)為李白《行路難》(其一)的主旨為積極奮進(jìn),這與樂府“感嘆世路艱難”的原旨已大為不同。
二、當(dāng)代:受考訂李白經(jīng)歷影響
古人對《行路難》(其一)的兩種解讀多被后人結(jié)合起來,認(rèn)為《行路難》(其一)寫于天寶三載(744)李白去朝以后,李白承襲了樂府舊旨表達(dá)了政治道路上遭遇艱難后的感慨,同時由于詩人個性所致,在末二句表達(dá)了積極進(jìn)取之意,表現(xiàn)了樂觀自信的精神。但隨著“兩入長安”說的提出,今人再次沿襲前人的二解分為兩派:一派再次提出“棄世”說,如詹锳、裴斐、陳子建、周維揚等學(xué)者認(rèn)為《行路難》三首同作于天寶三載,此年,李白被賜金放還,前途無望之下表達(dá)了棄世遠(yuǎn)遁的悲憤;另一派則提出“進(jìn)取”說,安旗、郁賢皓、薛天緯等學(xué)者認(rèn)為《行路難》(其一)與其他兩首創(chuàng)作時間不同,應(yīng)作于李白第一次入長安之時,表達(dá)了雖不得志但仍舊銳意進(jìn)取的心情(下文簡稱“開元進(jìn)取”說)。筆者認(rèn)為,“開元進(jìn)取”說存在諸多問題有待討論。
“開元進(jìn)取”說一派以王琦本在《行路難》(其三)題下注“此首一作《古興》”為立論,認(rèn)為李白《行路難》三首非組詩,故每首詩旨并非一定相同。在此基礎(chǔ)上,進(jìn)一步論證“進(jìn)取”說,其論證依據(jù)有三:其一,李白《行路難》(其一)與《擬古·世路今太行》的創(chuàng)作主旨、創(chuàng)作時間相同;其二,安旗先生認(rèn)為“閑來”二句“謂且歸隱以待時,或有如伊摯應(yīng)湯命之召”;其三,承襲前人對“長風(fēng)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一句的解讀,認(rèn)為化用了宗愨“愿乘長風(fēng),破萬里浪”一典,是“自勵之辭”,同時,薛天緯先生補充此句寫法源于李白的政治抒情具有“往往拖一條光明的尾巴”的特點。
筆者認(rèn)為,“開元進(jìn)取”說的三個依據(jù)有待討論。由于學(xué)界學(xué)者有關(guān)“閑來”“長風(fēng)”兩句的討論已非常多了,在此將不贅述,主要對宋本題下注和《世路今太行》兩點展開討論。
首先,《行路難》(其三)的題下注不能為論證做強有力的支撐,原因有二:其一,此注是否為李白自注還有待考證。郁賢皓先生認(rèn)同三首詩非同時所作,但他亦認(rèn)為題下注“乃宋人編集時所加”。其二,即使“古興”注為李白所注,作為孤證,并不能完全說明《行路難》(其一)將樂府古旨改為“積極進(jìn)取”。
其次,《世路今太行》創(chuàng)作主旨與時間不確定。安旗先生將李白《世路今太行》編在《行路難》(其一)之后,認(rèn)為兩詩一同作于開元十九年(731),應(yīng)為同旨。筆者認(rèn)為《世路今太行》(擬古其七)并不能直接證明《行路難》(其一)的創(chuàng)作時間與主旨,原因有二:第一,《世路今太行》不一定是在開元十九年創(chuàng)作。詩中“萬族皆凋枯,遂無少可樂。曠野多白骨,幽魂共銷鑠”四句描繪的場景,與《北上行》中“北上何所苦,北上緣太行……慘戚冰雪里,悲號絕中腸。尺布不掩體,皮膚劇枯桑……草木不可餐,饑飲零露漿”的場景非常相似。這樣的景象不應(yīng)出現(xiàn)在正值太平盛世的開元時期,更有可能出現(xiàn)在安史之亂時期。第二,即使《世路今太行》是作于開元十九年(731),但作為孤證,并不足以支撐《行路難》(其一)也作于此年。因此,此詩不足以說明《行路難》(其一)旨在積極奮進(jì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