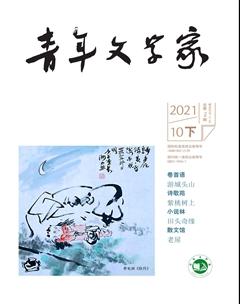變中之至理奇趣
褚凱
蘇軾《前赤壁賦》是中國古代文學史上偉大的名作。此文不僅從體裁上表現出有別于漢魏賦體的“變”體,還從佛家視角關注生命變化與永恒的哲學命題。此外,蘇軾在文中善用釋典的寫作技巧,體現出“新奇”的特點,更顯現出蘇軾文學創作方面的創新精神。
蘇軾的《前赤壁賦》不僅僅因為文中動與靜結合的寫景之妙,更因為蘇軾文筆對天地萬物滄桑驟變與永恒哲理的議論,使得這篇文章名垂千古。歷代文人墨客對此文皆有過特別的評賞,細細讀來更讓人覺得文章之妙。如鐘惺有云:“《赤壁》二賦,皆賦之變也。此又變中之至理奇趣,故此可以該彼。”其認為前后《赤壁賦》皆是漢賦之“變”體。這里所談《前赤壁賦》從體裁上來說是有別于漢魏賦體的“變”體,而就內容來看,即所謂“至理奇趣”,所以稱“新奇”。
讀到此文,首先應該注意到的是它的體裁方面的特點。《前赤壁賦》是賦,但有別于屈賦和漢大賦。屈賦在句里用“兮”字,但此賦只在歌里使用“兮”字,也不同于漢大賦夸張地描寫山川景物等,更不同于講究韻律的律賦。關于賦體的特點,古代文論家論述頗多。晉代文學家陸機在《文賦》里曾說:“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也就是說,詩是用來抒發主觀感情的,要寫得華麗而細膩;賦是用來描繪客觀事物的,要寫得爽朗而通暢,這主要是從內容上來看的。魏晉六朝時的劉勰在《文心雕龍·詮賦》中有云:“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說明賦是鋪敘,通過鋪敘辭藻來創作文辭,體察物象,抒發作者的情志,這主要從創作手法上來論及的。蘇軾寫這篇賦沒有按照漢魏六朝時的作家寫賦那樣大量堆砌文辭,而是使用了比較自由的句式來構成帶有韻腳的散文,既飽含詩意,又文采斐然。在北宋初期,這樣的文體還是一種新的體裁,是古典散文從駢文的桎梏中沖殺出來的取得勝利的一種新的體裁,即文賦。然而在當時,這種新的賦體很難駕馭,自宋初的歐陽修、蘇軾之后,便很少有人能創作了。所以,蘇軾《前赤壁賦》的新奇不只體現在體裁的創新上,更體現在對此種新文體的駕馭方面。
蘇軾的思想體系是將儒、釋、道三家哲學思想綜合在儒學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此賦文筆之間對天地萬物滄桑驟變與永恒哲理的議論,最易讓人感受到它的“至理奇趣”。“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蘇軾以月和水的變與不變來反問友人,認為水即使流走了,但它卻沒有變化;月亮即使有滿月和缺月的變化,最終也沒有消減或增長。《論語·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沒有說“未嘗往也”。蘇軾《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其中也未有云“卒莫消長也”。由物及“我”,這里涉及生命變化與永恒的哲學命題。關于此問題的探討,《莊子》中就早有涉及。《大宗師》有云:“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莊子認為人的生死,如同晝夜交替一樣,是“天”(自然規律)的范疇。莊子的生死觀首先承認物是變化的,只有順從“天”(自然規律),生死即是“夜旦之常”,就不會產生對生的貪戀和對死的憂懼,才能達到人真正的自由的“逍遙”狀態。我們可以看出莊子認為“我”不得不隨自然規律變化,只有順應變化才能使“我”永恒存在。與莊子觀點大相徑庭的是晉代僧肇,他在《物不遷論》則說:
夫人之所謂動者,以昔物不至今,故曰動而非靜;我之所謂靜者,亦以昔物不至今,故曰靜而非動。動而非靜,以其不來;靜而非動,以其不去。然則所造未嘗異也,所見未嘗同。
僧肇認為在俗人看來,現在所謂變化了的事物,是因為舊有事物沒有保存至今,所以說是“動”不是“靜”。而僧肇進一步認為舊有的事物沒保留到今天,站在“昔”的時間立場上看,事物正因為堅持本性未變,所以它才屬于“昔物”,而未成為“今物”,所以它是“靜”的,而不是“動”,正如他所說:“動而非靜,以其不來;靜而非動,以其不去。”僧肇以“物不遷”為命題,論證事物“不遷”的真理,而變遷的觀點只是世俗者所持有的。蘇軾當然并非俗人,他看到了水的流去,是靜的而不動,因為水不流去的話,流來的水就是流去的水,等于水不去;月有盈虛,也是靜而不動的,因為不管月亮是“盈”還是“虛”,始終是一個月亮。蘇軾接著又說:“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認為從“變者”角度去觀察,天地在“一瞬”之間就產生變化;而從“不變者”角度觀察,天地之間就存在無窮無盡的永恒了。這是釋家的觀點,如鐘惺所言,“變中之至理奇趣”,構成了此賦“新奇”的重要表現。
蘇軾的《前赤壁賦》于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時所作,此時的他正從儒家正視人生、積極入世之精神中漸漸脫離出來。當仕途的坎坷難行之時,當人生心灰意冷之后,他的佛禪思想從青年開始至晚年便習染漸深,慢慢發酵,逐漸地在詩文中表達出一種歸隱、出世、遁世的思想,正因如此,蘇軾的詩文才顯現出別于其他文人的以禪入詩的風格。這種風格具體表現在蘇軾擅長采用佛禪義理引入詩文,據《唐宋文醇》云:
(蘇軾)手書帖:“吾與子之所共食。”后人易“食”為“適”。釋典謂六識以六人為養,其養也,胥謂之食。目以色為食,耳以聲為食,鼻以香為食,口以味為食,身以觸為食,意以法為食。清風明月,耳得成聲,目遇成色。故曰“共食”。易以“共適”,則意味索然。當時有問軾“食”字之義,軾曰:“如食邑之‘食,猶共享也。”
“共食”本為佛禪術語,后人不知其內涵的精深,竟以“適”代“食”,就顯得意味索然了。這里不談“適”易“食”的意味問題,單就蘇軾此賦善用釋典的文學創作技巧,也屬于“至理奇趣”的另一表現。
蘇軾的《前赤壁賦》從體制上脫離了傳統賦的規格,不遵循老套路,并以佛家視角關注生命變化與永恒的哲學命題,論述獨到,另從他在文中善用釋典的文學創作技巧,都表現出“新奇”的特點,也體現出蘇軾文學創作方面的創新精神。蘇軾正是本著這種創新精神來寫《前赤壁賦》的。這也給后世文學創作以積極啟示:首先,文學作品的產生離不開時代背景、文化脈絡以及作者當時的狀態,更為重要的是,作者的內在修為在文學創作全過程中處處滲透、支撐,在此基礎上無論是“變”抑或是“不變”,均可能是點睛之筆。文學作品承載著思想和責任,要求創造者必須具備良好的人文情懷和思想修為,形成生存、生活、生命等具有層次的思考空間,在每一個細節中用心去感受人生進程中的大智慧。我們從蘇軾的《前赤壁賦》中充分感受其深厚的思想修為,即便不細品文章內容,滲透在字里行間的思想意蘊仍給讀者強烈沖擊,這便是文學創作者應當向往和追求的境界。其次,再觀“新奇”,顯然不是蘇軾的即興之作抑或隨意之舉,即便縱觀后世文學大家在作品細節上偶有呈現的“新奇”,均是自然恰當的“妙筆”。文學作品應當追求創新,但不能以此作為全部動力和沖勁,天馬行空地肆意揮灑,或是盲目效仿均無意義。這種創新應當在創作者成熟、深厚的思想脈絡上逐漸發展,在一定環境和時機下自然產生一種思想果實,經得起品味和推敲。蘇軾《前赤壁賦》之“新奇”自是明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