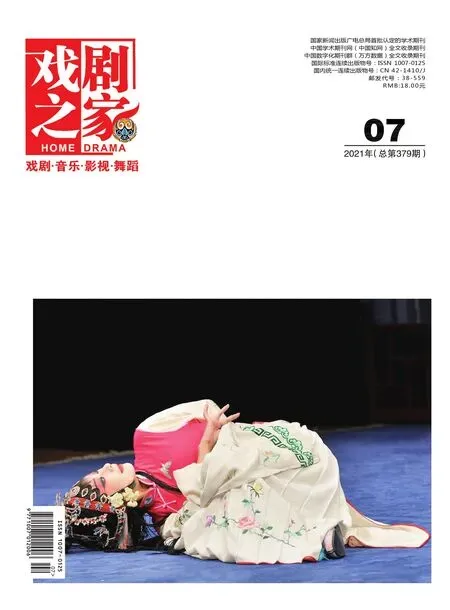淺析國內垂直類綜藝節目
李 華,涂衛寧,涂 畫
(1.武漢傳媒學院 湖北 武漢 430000;2.湖北衛視 湖北 武漢 430000;3.北京麥特文化 北京 100000)
所謂綜藝節目,通常是指利用多種形式制作出來的能夠滿足觀眾審美需求的節目,它是一種娛樂性的節目形式,包含了許多性質的演出,一般只在電視上播出。現在逐漸產生的互聯網綜藝節目,也是脫胎于傳統電視綜藝節目,依托于互聯網的方式進行傳播,是一種新興的綜藝形式。大部分綜藝節目會邀請觀眾參加現場錄制,或者現場實況播出。
垂直類綜藝節目則不同。“垂直”這一概念常運用于互聯網電商領域,比如聚美優品、海淘都屬于垂直類的電商,它們的用戶群大都是有垂直購物需求的人群,它們相較于淘寶來說是直接面向用戶群的,而不只是一個第三方承載平臺,操作更加專業化。因此,可以知道“垂直”指的就是深耕某一領域,內容更加專業,直接面向用戶群。現在各大視頻網站和電視平臺都在垂直領域做了大量的、多形式的探索,比如央視的文物類節目《國家寶藏》、愛奇藝的說唱類節目《中國有嘻哈》、米未的辯論類節目《奇葩說》等,它們都深入文化領域中的某一個點來制作節目,以此來達到宣揚各種文化的目的,取得了良好的社會傳播效果。
垂直綜藝打造的是在綜藝某一領域中更加細分化的節目,走的是小而專的路線。以《中國有嘻哈》為代表的垂直類綜藝節目在前幾年大火,屢創收視奇跡,效益頗豐。但好景不長,近幾年卻明顯呈頹勢,《中國有嘻哈》第一季豆瓣評分7.2,后更名為《中國新說唱》,第一季評分5.0,第二季評分5.3,其制造的輿論與話題也從過去的口口相傳,到了如今的鮮少問津。為什么這樣呢?在這里,筆者想談談我國垂直類綜藝節目的優勢、劣勢,以及如何破勢。
一、垂直類綜藝節目的優勢
首先,是節目的獵奇性。垂直類綜藝相較傳統意義上的綜藝節目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針對某一特定選題進行深入探討。那么,如何才能從眾多電視節目中脫穎而出呢?那就是充分利用觀眾的獵奇心理,即要求獲得有關新奇事物或新奇現象的心理。于是,循著這一邏輯,2017年由愛奇藝自制的音樂選秀節目《中國有嘻哈》爆火,除了創造超高收視紀錄,引領了海嘯般的公眾輿論之外,也獲得了業內的專業認可,并斬獲2017中國綜藝峰會匠心盛典“年度匠心剪輯”、“年度匠心視效”、“年度匠心品牌營銷”等獎項。音樂選秀類節目自2004年《超級女聲》、《我型我秀》開始就被各機構頻頻制作推出,但大同小異,讓觀眾產生審美疲勞,到前幾年,此類節目已經初顯頹勢。2017年《中國有嘻哈》推出,針對嘻哈文化進行挖掘,將這種小眾文化,在常人看來“專屬年輕人”的文化帶到了大眾眼前,使得這種所謂的“地下文化”有了在陽光之下“大放異彩”的機會。還有湖南衛視針對過著快餐式生活,無暇享受一點點愜意和悠閑的當代都市人推出生活服務紀實類節目《向往的生活》。帶著觀眾去田里采摘、養鴨趕鵝、打灶生火,回歸生活本身,去留意生活中那些細微易被忽視卻又難能可貴的美好。這種舍棄掉“廣而泛”的綜藝節目特性的垂直類綜藝節目保有的是“專而精”的制作優勢。它可以選擇一些小眾或不常見的題材,讓觀眾更加深入地體會和了解,帶領大眾去看一看世外的桃花源,讓人們驚奇中滿是驚喜。
其次,是節目的直接性。節目針對性的提升,換來的是受眾選擇時間成本的下降,以及接收有效信息密度的提高。這種“直接性”、“垂直性”的特點,在節目推出之際,就確立了一批匹配度極高的受眾群體。以往的綜藝節目包含多種節目形式,例如歌曲、舞蹈、小品、訪談等,有的也包含多種題材。舉例來說,想要收看歌舞類節目的受眾,首先在選擇節目的時候就會消耗較多的時間,在看完了喜歡的節目之后,又要花費時間去找尋下一個節目,或者說在觀看同一個綜藝節目時,只有特定的環節對于該觀眾來說是有效的,其他的環節實際上是在降低其對于節目的滿意度,因為在既定的時間里,受眾得到的對于他來說的有效信息是有限的。但是,隨著垂直類綜藝節目大時代的到來,喜歡美食類節目的觀眾就可以選擇《拜托了冰箱》、《中餐廳》;喜歡益智類節目的觀眾就可以收看《密室大逃脫》、《明星大偵探》;喜歡舞蹈類節目的觀眾就可以嘗試《這!就是街舞》、《舞蹈風暴》。不僅大大降低了受眾的時間成本,也能通過高密度的有效信息傳遞提高受眾對于節目的滿意度,從而提高效益。
不僅如此,這類節目能讓明星效應更大化,達到“指哪兒打哪兒”的效果。《奇葩說》讓蔡康永的溫潤睿智、李誕的大智若愚、高曉松的博學多知深入人心,“遙遠的哭聲”,“但行好事,不渡他人”,“沒有傷悲,就不會有慈悲”,一個個或多或少有悖于我們既定三觀的金句不禁引人深思。如果不是有這些帶有“智慧”標簽的明星出面坐鎮,我們真的會在一開始就正視這個節目嗎?我們之所以會正視,是否也因為這些明星符合、契合“辯論”、“益智”等這些單一的主題,在這一領域有一定的權威性和代表性呢?這樣的“垂直性”讓節目組在選擇明星嘉賓時能有更清晰的思路和更明確的導向,明星在面對節目組的邀約時更加能明白自己的工作是什么,參與起來也就更加游刃有余。《這!就是街舞》請來的導師易烊千璽、羅志祥、韓庚、黃子韜等,都是具有一定的話題性、流量,同時又在國內街舞領域有一定建樹的明星。又比如《潮流合伙人》里的嘉賓:吳亦凡,本身就是絕對的潮流引領者,作為早年韓國高人氣偶像男團中的一員,現如今不管是平日的私服穿搭,還是各大雜志封面的拍攝,都極具個人風格;潘瑋柏,一首《快樂崇拜》傳唱多年,國內娛樂圈“潮”文化的元老級人物;楊穎,擁有姣好的容貌,獲得阿迪達斯等多家服裝品牌代言權的她,對于潮流的品位自然也無需多說,且她本身也在節目拍攝地——日本有著極高的人氣,又有一定的日語對話能力。總的來說,“垂直類”節目能讓明星們更加大放異彩,能有針對性、有相對優勢地對節目起到添磚加瓦的作用。同時,明星們也能讓節目通過明星效應更具傳播力,增強了輿論性,從而吸收潛在受眾群體,實現互利共贏。
最后筆者認為,“垂直性”也能讓制作資金的投入相對集中、相對高效,在對資源的利用上也更有針對性。
二、垂直類綜藝節目的劣勢
首先,節目題材的選擇難度大。相較傳統綜藝節目多版塊形式,“垂直類”節目針對單一題材進行深入創作的特點,使其對題材的選擇要求更加嚴格,因為不是所有題材都符合國內觀眾的喜好。對于“垂直類”節目創作,國家政策有相應扶持,廣電總局于2017年8月發布了《關于把電視上星綜合頻道辦成講導向、有文化的傳播平臺的通知》,鼓勵各大電視平臺在晚間黃金時間段播放相應的文化類節目。通過臺網聯動,各大視頻網站相繼推出了垂直于科技領域的文化綜藝節目,比如優酷的《挑戰吧!太空》、《這!就是鐵甲》,愛奇藝推出的《機器人爭霸》。這類題材之前幾乎沒有被用于綜藝節目,在文化普及上有著十分積極的意義。此外,歐美國家也有同題材的長青節目為榜樣。原以為這類節目極具創新性和科普性,有政府扶持,又有資金投入,會成為收視爆款,但沒想到結果卻令人大跌眼鏡。《機器人爭霸》視頻網站點擊量只有8.7億,《這!就是鐵甲》為14.7億,而同期爆款《中國有嘻哈》達到31.2億,《明星大偵探3》達到35.5億。由此可見,并不是所有題材都適合“垂直類”形式。《這!就是鐵甲》所產生的輿論更多來自于明星在錄制過程中的八卦話題,而非節目本身。這樣的收視結果是不是有悖于初衷呢?“節目”是一種商品,賣家除了要對商品精心制作之外,還應該考慮市場需求,研究買家喜好。世熙傳媒董事長、CEO劉熙晨曾表示,首先從大類上來看,科技的關注度遠不如選秀的關注度高,因此也不會產生過大的影響力;其次中國人對于“機器爭霸”的熱衷也遠不如海外,“所以我們選擇垂直品類時應當考慮國內社會的審美”。確實,韓國對于選秀類節目尤為熱衷,是因為他們的韓流文化、偶像文化風靡全國。美國有檔人氣火爆的節目叫《荒野求生》,是美國探索頻道制作的一檔寫實電視節目,由英國冒險家貝爾主持,他會在極為惡劣的環境下,為脫離險境,做出一些極限舉動,比如生吃鼻涕蟲、蛇蛋等,同時節目也傳遞著冒險家敢于冒險的精神、堅定不移的意志力和一些荒野求生的知識。這檔節目符合了美國觀眾熱愛戶外運動、熱衷于探險活動的特點。國情不同,文化不同,環境不同,造就的是不同的收視群體、不同的收視習慣、不同的關注點。所以,節目的選題要遵循市場規律和市場需求,如此才能將“專而精”轉為優勢而非成為弊端。
其次,節目題材的選擇相對有限。垂直類綜藝節目對于題材的講究使得可開發的題材變得相對有限,節目“同質化”的現象日趨嚴重。同一個題材,被不同平臺接連不斷地制造出大同小異的節目,盲目跟風導致市場飽和、資源枯竭,觀眾審美疲勞。自浙江衛視2017年推出的國內首檔演技競技類綜藝《演員的誕生》獲得了極為不錯的反響之后,2019年,騰訊的《演員請就位》,優酷的《演技派》,愛奇藝的《演員的品格》以及浙江衛視的《我就是演員之巔峰對決》,同類題材撞車可謂慘烈。再來看,當愛奇藝推出的《樂隊的夏天》成為2019年暑假檔綜藝中最大黑馬后,緊接而來的是優酷的《一起樂隊吧》,江蘇衛視的《我們的樂隊》。順應市場的需求是理所應當的,但這樣蜂擁而上,擠破腦袋進一個門,吃相未免有些難看。雖說各個平臺推出的節目都有其自己的側重點,比如說《演員請就位》側重的是導演選角,《我就是演員》側重的是明星演員的自我挖掘,《演技派》側重的是對新人演員的培養,但從收視來看,只有《演員請就位》突出了重圍。作為一名觀眾,筆者更希望看到的是百花爭艷、欣欣向榮的場面,而不是大同小異、了無驚喜的斗獸場。
最后,題材“撞車”所導致的是有限資源被“泛消耗”。綜藝節目需要明星的加持,明星的人氣對節目的收視影響巨大。由此,垂直類綜藝題材的撞車難免會引發“嘉賓荒”的現象。《演員的誕生》和《聲臨其境》里的周一圍和翟天臨,《爸爸回來了2》和《爸爸去哪兒5》里的杜江和嗯哼。這樣的“重復利用”對節目來說沒了新意,對明星來說則是“過度營業”,容易失去熱度。加上在一定時期,某一特定領域,有流量、有對應才華又配合節目組的明星極為有限,因而使得嘉賓陣容易出現“供不應求”的局面,節目組也難免陷入首選嘉賓已成為熟面孔,新鮮面孔又擔心沒流量的窘境。在這樣的形勢之下,同題材的節目很容易陷入“拼大咖”的怪圈,這也是我們特別希望提出來的一點,電視節目最應該拿出來比拼的,是創意、是品質、是誠意,希望我國影視行業的所有作品都能以此為先,不要忘了根本。同時,被急劇消耗的不僅是嘉賓資源,更加慘烈的其實是選秀類節目中的選手資源:《中國有嘻哈》挖掘了國內近三分之二的說唱選手,使得之后的《中國新說唱》不得不增加海外賽區;在《創造101》、《偶像練習生》招選了大量的優秀“小鮮肉”之后,《青春有你》的選手們則顯得資質平平。
垂直類綜藝現有井噴爆發之勢,有著巨大的潛力。但數量雖然繁多,評得上爆款節目的卻只有《中國有嘻哈》和《演員的誕生》等。當然,成為現象級爆款節目除了有硬實力之外,也難免需要運氣。現在國內已經擁有技藝成熟的節目制作團隊,有著高新的技術和充足的資金支持,有著繁榮的市場需求,對制作方來說,在同等條件下,要想脫引而出,還是需要注重節目的創意投入,去創造新的節目模式,發掘新的選題,拿出更多的誠意,這樣才能在優勝劣汰的殘酷競爭中闖出自己的一席之地。
三、如何讓垂直類綜藝節目優勢盡顯
可以借鑒韓國綜藝節目,吸取前車之鑒,尋找進步空間。韓國的綜藝節目制作較為精良,他們的制作團隊不論是制作實力還是節目創意,在全世界來說都是首屈一指的。我國有許多高收視率的綜藝節目都是從韓國引進的,或者是借鑒了其節目形式。從韓國綜藝節目中感受到的不僅是節目的品質優秀、情節真實,更多的是制作團隊的誠意和心意。其中,為國內觀眾所熟知的有2008年韓國MBC電視臺制作的以藝人“假想結婚”為賣點的實境真人秀節目《我們結婚了》;2013年韓國KBS電視臺推出的親子娛樂綜藝真人秀節目《超人回來了》;2014年韓國JTBC電視臺制作放送的料理類脫口秀綜藝《拜托了冰箱》。在這里,我們結合韓國垂直類綜藝節目探討一下國內同類節目應該如何破勢,如何脫穎而出。
第一,節目運營。在韓國,一般來說點擊量超過兩千萬是證明視頻爆紅的一個標準。2015年由韓國tvN推出的網綜《新西游記》在播出后的一個半月內就創造了五千萬的點擊量紀錄。此外,這個節目在騰訊視頻與韓國同步播出,在中國的點擊量同樣突破了五千萬。但制作團隊并沒有因此自滿,他們趁熱打鐵,自我延伸內容,以節目中的同一批嘉賓又另起“番外式垂直綜藝節目”,如美食真人秀節目《姜食堂》,平均收視率8.3%,最高收視率為9.1%。此外,在《新西游記》的錄制過程中,導演羅英錫總是亂下游戲賭注,如在抽簽游戲中寫下百萬豪車、游輪體驗、國外旅游作為頭等游戲獎勵,而嘉賓恰巧贏得了這些獎勵后羅英錫又不得不誠摯地向嘉賓和節目組道歉,這已經成為《新西游記》的一大笑點和話題。于是,當嘉賓又抽到去冰島旅游的獎勵之后,節目組干脆就制作出了《新西游記外傳 三時三餐 去冰島的三餐》,雖然每集只有10分鐘左右,但也創造了不俗的網絡點擊率。之后,羅英錫又繼續“亂說話”,如果他的YouTube頻道訂閱量突破100萬,他將把節目嘉賓李秀根和殷志源送到月球。面對此類言辭,大家的評論是這樣的:“你訂閱,我訂閱,明天大根就登月”,“請謹記自己說過的話”,“老羅從來不長記性,允悲這嘴啊”。隨著訂閱量不斷上漲,制作團隊放送出了許多羅英錫焦慮、緊張的搞笑視頻,在最后真的突破了100萬后,制作團隊又隆重推出了羅英錫的道歉視頻,引得網友觀眾紛紛大笑。提到這個“梗”的目的是想重點探討制作團隊該如何制作和運用節目話題,又該如何與觀眾互動。試問國內哪一個制作團隊能做到跟觀眾有這樣良性、親密、類似朋友的互動呢?一個節目不該只是一個節目,它應該被運營成為制作團隊與觀眾之間溝通的橋梁。這樣的運作模式更加有效、合理地利用了既有的收視群體,也有可能持續吸粉,而團隊又節省了一定的宣傳成本。并且,在觀眾觀看這些“番外篇”的同時,也無異于在為處于新一季制作過程中的《新西游記》造勢回溫。國內的節目大都是在播出前造勢,在下一季播出之前大都處于真空期。如果我們能夠學習到韓國團隊這樣的運營方式,那么垂直類綜藝節目在有限的資源下,就能夠尋找到更深層次的發展空間。
第二,真實把握。現在許多垂直類綜藝都是以真人秀形式展開的,筆者認為雖說是“真人秀”,但節目應該在更加注重“真”的同時,避免給觀眾帶來“作秀”的感覺。比如拿韓國和國內的餐廳經營類節目《姜食堂》和《中餐廳》對比,《姜食堂》的第一季,嘉賓們將炸豬排選為了主推菜,豪言壯語地說要做最大的豬排:要將手掌大的豬排手工敲成長40多厘米,寬30多厘米,比“整只雞還大的豬排”。聽起來容易,但實操起來觀眾可以看到,要做成一塊可以下鍋的豬排,得敲將近20分鐘。所以付出的大代價就是,在開業前的晚上,嘉賓剛在住所放下行李之后,就去超市進行了大量的采購,然后五個男人在宿舍里不停地敲敲打打,一直持續到凌晨三點半。不僅是這一天,往后的每一天,在餐廳里辛苦錄制完節目后,他們都要回到宿舍敲豬排。雖然前一天敲豬排敲到凌晨,但是第二天一群人仍舊八點就起了床,早早來到餐廳,提前兩個多小時開始做各項開業準備工作。嘉賓姜虎東在去餐廳的車上還一路擔心那些敲了一整晚的豬排,碎碎念地給大家加油鼓勁。此外,因為要制作巨大的豬排,所以需要配備的蛋液量也很大。嘉賓殷志源在開業第一天就敲了一百多個雞蛋。十二點正式開門迎客后,眾人就忙得沒有一點休息時間了,擔任廚師的姜虎東和安宰賢在爐灶前拼“命”輸出美食;李秀根開啟“人肉洗碗機”模式,此外還身兼切菜工、洗菜工、服務員等等;飲料區的殷志源和宋閔浩也盡心盡力地為客人們服務。觀眾在看著他們敲豬排、打鬧般吐槽對方、緊張又盡全力為客人服務等種種場景時,不禁屢屢爆發出笑聲,同時也看到了他們背后的辛苦付出。在節目里,我們看到的不是韓國知名主持人,不是當紅偶像,不是人氣演員,不是實力派唱將,而是一個個手足無措、緊張不安但又拼盡全力、任勞任怨的餐廳經營界新人。這就是節目最應該呈現在觀眾面前的“誠意”,這樣的態度與感情是可以透過屏幕傳遞到觀眾心里的。而反觀國內同題材同類型的節目《中餐廳》,盡管嘉賓也在辛苦認真地經營餐廳,但其實這檔節目中明星的任務相對韓國版來說是比較輕松的。而節目又有些用力過猛,過于頻繁地去表達、渲染他們的辛苦、疲憊。這樣的操作反而起到了反作用,會讓觀眾有種“看戲”之感,讓明星有“作秀”之嫌,在完成了“秀”的同時,難免失掉了“真”。縱觀現在國內的垂直類綜藝節目,或許是為了給節目增加劇情性和觀賞性,難免會在節目中嘉賓遇到困難時,多下一些力氣來“處理”。這樣的處理手法固然需要,但要酌情。應該堅持以手法輔助劇情發展,而不是以手法主導劇情發展。
第三,內容取舍。垂直類綜藝節目成功的另一個要素就在于它的剪輯,因為在有限的題材之內,如何去再創造,在節目劇本之外去找尋新的亮點,挖掘更多的潛力,是極為考驗后期制作功力的,很多節目的笑點和意外的驚喜都源自后期的點睛之筆。前期錄制時素材固然豐富,攝制組也一定要去捕捉盡量多的可能性,后期在拿到素材之后,如何排列組合,如何取舍,也是至關重要的。同時,制作團隊也要想清楚,是明星為節目服務還是節目為明星人設服務,觀眾到底是看節目還是看明星?拿韓國和國內同題材的密室逃脫類節目《大逃脫》和《密室大逃脫》來比較。國內版在進入逃脫正題之前僅耗費了約11分鐘,而韓版則超過了20分鐘。看似國內版更早切入了正題,但我們來看看這11分鐘和20分鐘分別呈現了什么內容。國內版開篇是嘉賓們見面,互相打鬧斗嘴,互開玩笑,比如謝依霖開玩笑說自己“天下第一美”,楊冪又說自己的麥“悶悶不樂”,觀眾是笑了,但除了笑,除了知道明星之間關系融洽之外,觀眾還得到了什么有效信息呢?這些“梗”和內容可以出現在任意一個節目里,跟密室逃脫題材的垂直類節目有何關聯?又比如,后期還為楊冪的一個小口誤“密湖”專門做了一段小動畫,加在那里確實無傷大雅,但這個與節目主要任務無甚關聯的小誤會,真的值得占用節目這幾秒的時間和后期的制作時間嗎?我們再來看看韓版《大逃脫》,節目從嘉賓們第一次見面吃飯開始,但這并不是為了拍他們初次見面的場景和韓國的美食,而是他們在吃飯的時候就開始進行許多益智類游戲,從比較簡易的游戲開始,既緊扣了密室逃脫是一種“益智游戲”的主題,又在游戲過程中說明了嘉賓們不同的人設,比如神童是高智商玩家,金在鐘在“益智類”方面好像不太擅長,姜虎東是空有一身力氣,好像不太聰明,這都為后面的劇情發展和人物反轉作好了鋪墊。可以說韓版《大逃脫》的每分每秒都在為其節目內容服務。筆者認為,在垂直類綜藝節目中,在內容的取舍及后期的節目導向上,都應該全心全意為主題所服務,要盡可能高密度地向觀眾輸出信息,盡早地將觀眾帶入這個語言環境和劇情當中來。
第四,節目創新。我國的綜藝節目已從傳統單一的“泛綜藝”形式向垂直類綜藝轉變,綜藝形態向多元化發展,在節目形態上有了很大的創新。但不管是在節目形式、節目題材還是節目內容上,大都借鑒了國外的知名綜藝。比如《中國好聲音》是借鑒了美國的《The Voice》;由何炅和王嘉爾聯袂主持的網綜《拜托了冰箱》是借鑒了韓國的《拜托了冰箱》;愛奇藝爆款說唱真人選秀節目《中國有嘻哈》是借鑒了韓國2012年推出的《Show me the money》等等。借鑒好的節目內容,吸收優質的制作形式固然重要,但是原創更值得期待,希望國內的電視節目團隊能夠更多地制作出如《奇葩說》、《向往的生活》這樣的原創、優秀的垂直類綜藝節目,敢為人先,勇于去開辟尚且無人問津的領域,希望不僅僅是“國內首檔xx節目”,而是“全球首檔xx節目”,我們共同期待著這一天早日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