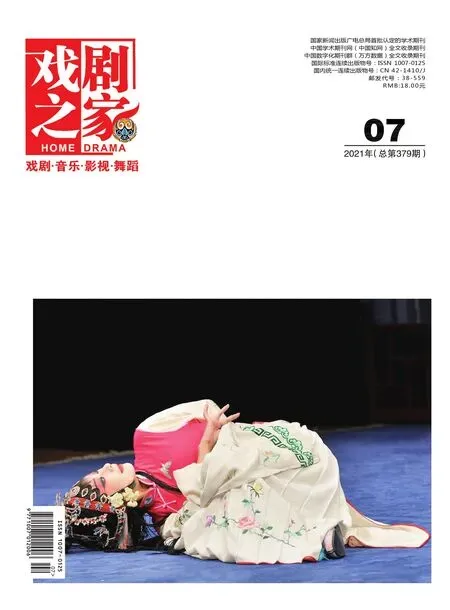《真心半解》:給電影做減法,讓青春片回歸校園
蘇 丹
(四川電影電視學院 電視學院攝影系,四川 成都 610000)
2020年全球電影業在疫情的影響下產出較少,由網飛出品、華裔女導演伍思薇執導的青春片《真心半解》成為電影市場的一劑良藥,一經播出便收獲了爛番茄96%的好評率,以及IMDB評分7.0、豆瓣評分8.0的好成績。電影以其優質的劇本、清新的畫面和唯美的風格斬獲翠貝卡電影節“最佳美國劇情片獎”。本文將從電影中的人物形象、敘事結構和思想表達三方面著手,對該片進行一個深刻的剖析,旨在為國產青春片的發展提供參考和借鑒。
一、美國青春片概述
關于青春片的界定,學界存在兩種主流說法:“有研究者認為青春片就是以青春故事為敘事對象,采用青年演員演繹的影片;有研究者認為青春片的受眾群體是青少年,所以青春片應定義為從青少年觀眾審美需求和審美水平出發制作而成的影片。”[1]事實上,青春片中演繹的青春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吸引著青少年受眾,而青少年受眾也熱衷于觀看貼近自己生活的、由同齡青年演員演繹的青春故事,兩種主流說法只是角度不同,實際并無沖突。
美國青春片獨立發展于20世紀中葉,青春故事中充斥著搖滾、暴力和性元素,該階段的美國青春片是以比較溫和的方式來呈現青年亞文化和主流文化之間的沖突,典型代表作有詹姆斯·迪恩的青春三部曲《無因的反抗》(1955)、《伊甸園之東》(1955)和《巨人傳》(1956);以20世紀六七十年代為分界線,從該時期開始,美國青春片中的文化矛盾呈現方式更加激進,吸毒、濫交等元素成為這一時期美國青春片的典型標簽,該時期的經典代表作品有邁克·尼克爾斯執導的《畢業生》(1967)以及喬治·盧卡斯執導的《美國風情畫》(1973);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美國青春片在激情退卻后呈現出反思意識,這一時期的青春片雖然也以呈現青年迷茫焦慮的亞文化影像為主,但大多會以勵志的結局為青少年受眾傳遞積極向上的主流價值觀,2020年5月由網飛出品的《真心半解》就是青年亞文化與主流價值觀相結合的一部優秀的電影作品。
二、建構:普適化的人物形象
英國學者斯圖亞特·霍爾指出,“現代的大眾是通過影響來構建社會知識的,并用這種知識來體味他們過往的生活”[2],觀眾會通過觀看電影獲得故事中人物的生活經驗,“人物塑造既關乎電影的品質,又決定著電影的壽命,人物形象是電影的命根子”。[3]《真心半解》中三個主要人物形象各有各的特點,導演利用普適化的人物形象設計,引起人們的普遍共情,讓觀眾通過人物的成長軌跡,回憶起自己的青春經歷。
(一)艾莉:從敏感自卑到接納自我
林崇德教授認為,“自卑感指個體因體驗到自己的缺點、無能或低劣而產生的不如別人的消極心態”。[4]生活中很多人都在一些特定方面具有自卑感,通過艾莉這個角色,觀眾可以從間接經驗中獲取“社會認知”,實現“身份認同”。
高中時期的艾莉是一個沉默寡言的學霸,私下做著幫人寫作業的“黑活兒”。這樣的人物設定讓人不禁想起泰國青春片《天才槍手》(2017)里的女主角小琳,同樣是校園青春片,同樣是學霸女主角,艾莉的形象塑造更加貼近真實生活中的高中生,她沒有縝密的心機,沒有深不見底的欲望,雖然幫人代寫作業,卻不想幫人代寫情書,她認為愛情應該是發自內心且真情實感的,不能為了獲取利益而傷害別人的感情。精于利益的同時還保留一份對待愛情的天真,這是艾莉人物塑造上的閃光點。
艾莉不喜歡和別人說自己的事情,她會因為保羅大大咧咧的問話而生氣地下車離去,會覺得和集體格格不入而不想上臺表演,會因為沒有做好萬全的準備而不允許保羅和阿斯特約會。故事開始時的艾莉龜縮在名為“自尊”的殼中與別人交往,一旦事情超出控制她就會躲到殼中尋求安寧。隨著劇情的發展,艾莉與保羅和阿斯特深交,她漸漸發現了自己內心真實的渴望,盡管她仍是一個帶著缺陷的角色,盡管她認識到愛情也許并不像哲學課本上的柏拉圖說得那么美好,但她仍然選擇了接受自己并悅納自己。艾莉用自己的人物弧光,獲得了觀眾的普遍共情,正如導演伍思薇所說:“通過這個故事,來表現很多觀眾都曾有過的青春經歷,包括不敢做的事、害怕的事、如何接受自己等等。”[5]
(二)保羅:從單線思維到理解他人
文學理論家福斯特曾在《小說面面觀》中提出“扁平人物”的概念,所謂“扁平人物”就是“基于某種單一的觀念或品質塑造而成的”人物,也就是說無論故事怎樣發展,這類人物在思想和行動上都不會有所改變,男主角保羅在電影前期就是一個典型的扁平人物。
高中生保羅是一個粗線條的運動健將,他勇于表達自己的感情,喜歡阿斯特就要寫情書去告白,即使沒做好準備也能鼓起勇氣與阿斯特約會,他愿意為阿斯特改變自己的性格,讀自己不喜歡的書,談論自己不喜歡的話題,但當艾莉追問保羅喜歡阿斯特哪一點時,連保羅自己都迷茫了,他像是一個為了戀愛而戀愛的“追愛機器”。在這一階段,保羅是一個典型的扁平人物。
福斯特在《小說面面觀》中也曾提出:“扁平人物假使超過一種因素,我們的弧線即趨向圓形。”[6]于是觀眾看到,當保羅意識到自己真正喜歡的人是艾莉時,他的人物性格產生了巨大轉變,他從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莽莽撞撞的人,逐漸成長為一個可以理解艾莉,并愿意包容艾莉所思所想的人。誠如福斯特所說:“檢驗一個人物是否圓形的標準,是看他是否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讓我們感到意外。”[7]在艾莉的父親詢問保羅是否跟艾莉分手的那場戲中,粗線條的保羅居然脫口而出“你根本不懂她,不知道她是什么人,也不知道她會成為什么人。”愛情帶給了保羅陣痛和成長,也令保羅從一個扁平人物真正成為了一個圓形人物。
(三)阿斯特:從隨波逐流到挑戰權威
在整個故事中,阿斯特的戲份比較少,但她卻是一個十分重要并串聯起整個故事的關鍵性角色。《真心半解》中很多重要的情節轉折都源于阿斯特,比如她撞破三人的三角戀關系,促使他們彼此在失戀中探尋自我;比如她在教堂中被求婚,使得另外兩位主角坦白心跡等。
阿斯特這個角色代表了一部分觀眾,從小循規蹈矩,是班里的人氣王,擁有幸福的家庭和優秀的伴侶,生活看起來處處如意,但內心非常苦悶。最典型的一個細節就是阿斯特面色尷尬地戴上同班女生贈與的粉色花環,即使她的內心很排斥這個花環,但仍舊要表面“合群”并違背自己本心地把花環戴起來;她不喜歡自己的未婚夫,卻因為父母之命不得不與未婚夫相處;她喜歡美術,卻因為父親的要求不得不放棄。在電影結尾她拒絕了盲從,拒絕了求婚,并報考了藝術院校去追尋真正的自己。
阿斯特人物形象的塑造與美式青春片中一貫的“權威的質疑”有關,“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美國青年運動先驅最先提出‘根本不要相信三十歲以上的任何人’和‘權威的質疑’的口號”[8],促使一大批青春片將“青少年——成年人”作為二元對立來書寫故事,例如經典影片《小鬼當家》系列中的小男孩和蠢賊。《真心半解》在展現“青少年挑戰權威”這一點上更加具有時代性,導演用更柔和的手法展現了青少年與成年人、與周遭環境的對抗,并最終回歸到主流價值觀上,引導青少年健康成長。
電影雖然講述了青春片中最為常見的三角戀關系,卻沒有把故事拘泥于表現青春期的情情愛愛,三個普適化的人物形象為觀眾展現了不同性格的少年在面對成長時的困惑與焦慮,導演在劇作中表達出的強烈的人文關懷讓一部青春片有了更深刻的意義。
三、回歸:單線簡潔的敘事結構
從電影的敘事結構入手,可以將電影分為最基本的線性結構、非線性結構以及反線性結構,人類對線性敘事最早的界定可以一直追溯到亞里士多德的《詩學》。在電影領域,羅伯特·麥基的“故事三角”原理為線性敘事提供了強大的理論支撐,希利斯·米勒在他的《解讀敘事》一書中,闡明了“敘事線條”以及“線條意象”等諸多概念。歸根結底,線性敘事中的“線性”只是一個比喻,即指敘事本身像一條線,前后緊密相接,順時而不間斷。
隨著觀影群體影視審美水平的提高,單純的線性敘事已經很難給觀眾帶來刺激,越來越多的青春片使用倒敘和插敘的手法來完成雙重敘事,也就是非線性敘事,以增強故事本身的吸引力。比如《七月與安生》(2016)中,電影先倒敘了一段26歲的李安生在上海遇到蘇家明的情節,然后依據小說回到李安生十三歲的時間點,隨后電影通過交替呈現兩個時空,講述了林七月與李安生的青春故事;而在《匆匆那年》(2014)中,敘事從趙燁投送婚禮請柬的2014年開始,隨后回到1999年的讀書時光,并不斷在過去和現在兩段時間中來回跳躍。通過非線性敘事的手段,青春片的節奏張弛有度,既滿足了觀眾對主角的愛情故事抽絲剝繭的窺探心理,也使得觀眾可以將回憶的美好與現實的殘酷進行鮮明的對比。
非線性敘事容易抓人眼球,但并不是每部青春片都需要使用這樣的敘事手段來吸引觀眾,導演伍思薇就選擇了回歸單一的線性敘事,用最簡單平實的方式來給觀眾展現一場青春時期的懵懂愛情,讓看慣了雙重時空敘事的觀眾們耳目一新。如果說非線性敘事的目的是制造懸念,讓觀眾不能輕松地看懂電影,那么線性敘事的目的就是讓觀眾能夠輕松地看懂電影,從而集中注意力在故事本身,觀眾可以完全沉浸在故事的劇情里,去感受戲中人物的細膩情感。
四、表達:復雜多元的人類情感
導演伍思薇成功地建構了主角三人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愛情故事線,故事中三個年輕人之間都存在著朦朧的愛情情感。艾莉因為與阿斯特愛好相同、想法相近,故而在代筆過程中懵懵懂懂地愛上了阿斯特,但這并不妨礙她在生活中為保羅付出,她仍然會孜孜不倦地給美食評論家寫信,幫助保羅實現愿望。影片末尾,艾莉與保羅兩人就像浪漫愛情劇里的男女主角,一人追火車,另一人哭著說對方是傻瓜。艾莉與保羅的關系并不能被簡單地歸結為純粹的友誼,那這種存在“異性情感”但又不是愛情的親密關系應該如何定義?導演聰明地把這個問題拋給了觀眾。
“校花”阿斯特本身擁有一個已經建立親密關系的男朋友,然而在“保羅的情書”的狂轟濫炸之下,她迅速地被保羅所吸引并愛上了保羅;在與保羅建立親密關系之后,她漸漸發現真正吸引自己的“靈魂伴侶”并不是保羅,而是艾莉,這令她產生了關于愛情的困惑,她強吻保羅似乎是想要證明自己喜歡的人是保羅,但吻過之后才發現事實并非如此,于是在影片結尾,她沒有選擇兩個人中的任何一個人,這是該角色心中的答案,也是大部分人對待復雜情感的處理方法。
在教會表白的這場戲中,艾莉、保羅和阿斯特都明白了愛不是假裝,愛是做真正的自己,他們看似是在表達愛情,實際上是在接納真實的自我。通過觀看電影,觀眾們明白了想要愛別人,先要勇敢做自己。這呼應了電影開頭艾莉的獨白:“這不是一個愛情故事,或者說不是一個所有人得償所愿的故事。”電影結尾時,導演沒有正面展現幾位主人公的愛情結局,但觀眾卻在觀看過程中明白了要鼓起勇氣接受那個并不完美的自己。
五、結語
作為一部青春片,《青春半解》擺脫了美式傳統下性與暴力的青春狂歡,描繪出青少年群體青澀懵懂的戀愛初體驗,影片沒有使用復雜的非線性敘事策略,而是回歸到簡單質樸的線性敘事中,通過一個具有現實關懷意義的青春事件,展現了人類復雜多元的情感,并最終落腳在悅納自我的社會主流價值觀上。該片對于國產青春片具有一定的啟發作用,如何構建富有現實意義并具有思想深度的青春故事,以人文主義的價值觀展現具有時代性的青春影像,這將是未來國產青春片需要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