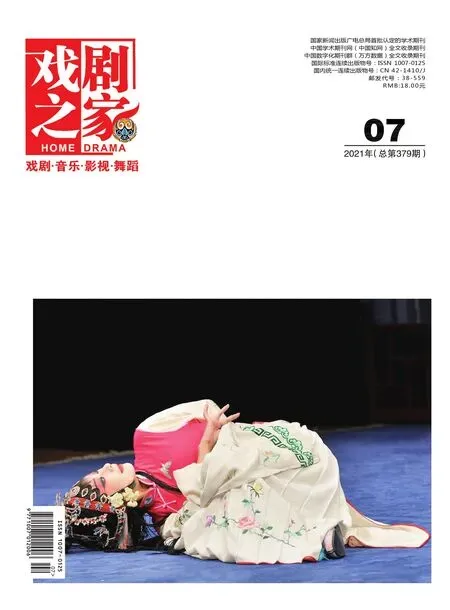宮體詩藝簡析
信福艷
(煙臺大學 人文學院,山東 煙臺 264005)
公元五世紀的開端,準確來說是在502年,蕭衍經過漫長的政治博弈與戰場廝殺在是年春天登基稱帝,一個新的王朝由此開始。如果從宏大的歷史背景加以審視,這不過是南北朝亂世中的一個微末節點。但無可否認的是,蕭梁王朝是中國歷史上最輝煌、最富有創造力的朝代之一,同時也是最被低估、受到誤解最深的朝代之一。關于蕭梁王朝的文化想象,是端坐高位、沉迷佛學的昏聵帝王;是同室操戈、相互傾軋的皇室內斗;是偏安一隅、醉生夢死的文士狂歡;是止乎秹席、思極閨房的頹廢抒寫。在這些種種負面的想象中,最為人廣泛接受也最為人所排斥的無外乎是給蕭梁王朝涂抹了極為香艷色彩的宮體詩的流播。“宮體詩”一詞的概念有廣義和狹義兩說。從文學史發展脈絡來看,“宮體詩”可以被歸為“艷詩”在特定時期的一種新發展。然而“宮體詩”畢竟不同于“艷詩”,“宮體”之名本身是一個歷史的概念而非嚴格意義上的文學題材概念。宮體詩有著一個比較清晰的生命周期,主要流行于蕭梁(尤其是蕭綱入主東宮以后)以迄唐初,此后雖有余波,也只不過是末世的幻影復制。宮體詩的寫作對于強調“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的傳統詩學觀而言是一種大膽的越界,這種越界回避了崇高的主體精神,但同時將“物”還原成“物自體”,從傳統表現抒情的框架另辟出再現摹寫的新變。
一、審美境遇
如果對中國詩歌進行溯源,普遍意義上會指向《詩經》,然當時所謂的“詩”更是周代禮樂文化下的音樂實踐。詩三百所包羅的眾生萬象如同一個遙遠傳說的浮世繪,無論是男女之間的言情篇章,亦或是大夫卿士的國殤挽歌,底層布衣的窮愁掙扎……這些為生存而爆發的歌唱有著強烈的暗示性和故事性,它能夠展開一段漫長的歷史記憶,此所謂孔子“興觀群怨”之理。與詩三百共時呈輝的是南方楚國屈原的個人吟誦,《楚辭》真正代表了個體在絕望與希望之間的悲劇宿命。在此時期,我們之所以把《詩經》和《離騷》看作是有別于諸子散文的另類言說,其關鍵在于它們詩性地表達了一種情緒的沖動,形式上受到了不同音樂結構的限制,我們統一稱之為粗野原始的“詩”。古樂消亡后,“三百篇”成為書面上的歌詞。當不知所謂“先王之樂”的經生面對竹簡上的《詩經》時,他們從孔子的音樂批評標準出發,確定了他們評價詩篇的標準。孔子的政教音樂學一變而為漢儒的政教詩學,《楚辭》也被拉入“五經”的旁系(王逸:“夫《離騷》之文,依五經以立義焉。”)①,香草美人的抒情態度充滿了愛情與政治的隱喻關系,可以說中國詩歌從誕生伊始便背負著沉重的情感張力,主客體混融糾纏,“失意”被高歌成“詩意”。直至漢末建安時期,曹丕、曹植兄弟在時代的肅殺氛圍中憑借一種少年的銳氣開拓出華美的詩歌形式。不同于其父曹操的古直悲涼,他們偏愛在經驗自我的反思中創設出詩性自我,把漢代古詩和樂府詩這兩種非個體化的詩歌形式改造為個體詩人進行自我寫照的工具。這種對自我的張揚在傳統詩學話語體系中被統一置換成“言志”解讀。最典型的替換是東晉時期陶淵明筆下的“菊”,毋庸置疑,陶淵明由自我投射對菊花展開的想象敘述已成為后世之人無可發揮的一個原型符號,這種人格化的審美期待帶來的是菊花自然的審美屬性被消泯。也許是玄言詩的寡味太甚,宋齊詩壇開始反向度地著力追求聲色大開,從鮑謝辭章用力于“富艷難蹤”,到永明體對“八音諧唱”的終極探尋,中國詩歌在形式上的唯美表現逐漸趨于完善。南梁宮廷詩人就是在如此豐富的文化背景下衍生出了以“新變”為特色的趨小詩學空間。
宮體詩孕育于艷詩傳統,脫胎于詠物詩的風行。被看作是宮體詩學代表成果的《玉臺新詠》所收錄的詩歌從漢代的故事敘述逐漸轉向“物”的靜觀,但無一例外重點都在于關注女性向的生活空間。漢代樂府民歌《陌上桑》是最具典型意義的艷詩原型之一,所以受到后世詩人的反復演繹。《陌上桑》的敘述中心聚焦于羅敷身上,但是整個文本具有一種集體參演的性質。我們感受到綺艷的那部分描寫,諸如“青絲為籠系,桂枝為籠鉤。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緗綺為下裙,紫綺為上襦。”、“何用識夫婿,白馬從驪駒。青絲系馬尾,黃金絡馬頭。腰中鹿盧劍,可值千萬余。”②雖然也運用了一種強烈的視覺感官刺激,最終是要勾勒出羅敷的形象與美德,它依然是對傳統宏觀詩學的有效敘述。曹植《美女篇》“美女妖且閑,采桑歧路間”,將《陌上桑》中具體所指的羅敷替換成了泛符號化的“美女”表達,“妖且閑”的氣質賦予也能感受到詩人自我的審美投射,“采桑”的意象承繼保持著故事的意義沉淀,而場面描寫的綺艷性則在此基礎上有了質的變化:“柔條紛冉冉,葉落何翩翩。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頭上金爵釵,腰佩翠瑯玕。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羅衣何飄飄,輕裾隨風還。顧盼遺光彩,長嘯氣若蘭。行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餐。”③這里通過“柔條”一詞開啟了對佳人形象的構建,她的配飾光華流轉,她的衣袂飄飄出塵,她的顧盼和長嘯都讓人感到優雅的官能體驗,無形中進入到純粹的美的享受。事實上曹植的華美文學意味已經是傳統詩學不可忍的“余事”之作,但政治命運的沉淪為此種寫作提供了一種屈原式的解讀出口。吳兆宜《玉臺新詠》箋注按郭茂倩解為:“美女者,以喻君子。言君子有美行,愿得明君而事之。若不遇時,雖見征求終不屈也。”④《美女篇》中女性雖已成為詩歌舞臺的獨一表現體,然而終究是如同霧中看花,隔著宏大的男性理想,女性被塑造成了隱約朦朧的精神象征。齊梁詩壇風云多變,由山水的形似到對于日常用物的吟詠,“趨大的描繪”被“趨小的描繪”所代替,尤其是在梁代宮廷詩人那里,開始了對物自體的凝神細觀。梁簡文帝蕭綱《艷歌篇》、《美女篇》二首是《陌上桑》母題在褪去外在倫理包裹的單一摹寫。《艷歌篇》“凌晨光景麗,倡女鳳樓中”與“羅敷善采桑,采桑城南隅”、“美女妖且閑,采桑歧路間”有著一種明確的區分,如果說《陌上桑》和曹植《美女篇》都是走向外部世界的,那么《艷歌篇》從最開始便劃定了自我內轉空間。詩人拋棄了向外探尋的意義疊加,把筆觸對準鳳樓中的倡女:“前瞻削成小,傍望卷旌空。分妝間淺靨,繞臉傅斜紅。張琴未調軫,飲吹不全終。”⑤如同繪畫一般,從各個角度去看客體最本真自然的狀態,細細雕琢,淺淺上色,只為獲得美感舒適度。“誰言連尹屈,更是莫敖通。輕軺綴皂蓋,飛轡轢云驄。金鞍隨系尾,銜璅映纏鬃。戈鏤荊山玉,劍飾丹陽銅。左把蘇合彈,旁持大屈弓。控弦因鵲血,挽強用牛螉。”這些對于所愛之人的涂飾之詞不再像《陌上桑》那樣是為了增強道德說教的戲劇張力,而是在一種美感氛圍中自然而然引發的聯想。“暉暉隱落日,冉冉還房櫳。燈生陽燧火,塵散鯉魚風。流蘇時下帳,象簟復韜筒。霧暗窗前柳,寒疏井上桐。”⑥從凌晨光景到暉暉落日,對于散落在人物周邊微末之物的觀照,諸如燈火風塵、流蘇象簟、霧柳寒桐,實際上是在時間的延續和空間的靜止中展開的感官擴張與交融。《美女篇》中“約黃能效月,裁金巧作星。粉光勝玉靚,衫薄似蟬輕。密態隨羞臉,嬌歌逐軟聲”⑦,是在用一種非常宮體的筆調呈現出一個靜止的女體。在視覺、聽覺、觸覺的感官交融中,詩人想要呈現的是基于觀者美感經驗所喚起的感覺張力。《美女篇》完全不見《陌上桑》試圖通過故事敘述從而建構道德語境的復雜意味,它在一個非常美的戀物結構中展開了趨小的描繪。蕭綱的宮體寫作在傳統詩學的維度里無法找到一個合情合理的位置,屈原式的政治隱喻也與蕭綱本人身份有著巨大的背離,他所受到的負面批評較之一般的宮體作家也尤為嚴厲。
英國藝術理論家諾曼·布列遜曾就靜物畫的發展史重新定義了“趨大的描繪”和“趨小的描繪”:“‘趨大的描繪’即是對世界中偉大事物的描繪——譬如神的傳說、英雄的戰爭和歷史的危機等;‘趨小的描繪’則是對那些并不重要的事物的描繪,這種事物平平淡淡,是與‘重要性’常常無關的生活中的物質性基礎。”⑧靜物畫和宮體詩都無法從那種日常平淡的細節糾纏中抽取出來,不能創造與純粹的感官愉悅相對立的精神愉悅。由此可見,靜物畫被列于藝術家族的最低形式與宮體詩被視為墮落的詩藝是何其相通的命運。
二、審美特質
田曉菲女士在《烽火與流星:蕭梁王朝的文學與文化》中指出,宮體詩的寫作背后有著蕭梁的佛學文化意蘊,宮體詩人對佛學之“念”作了富有創造性的發揮,通過把時間之流分解成“萬念”,進而強調對于其中每一念、每一瞬間的關注。所以宮體詩不應該僅僅是“關于女性和艷情的詩歌”,而是一種關于定力、關于凝神觀看物質世界的新方式的詩歌。在《擬落日窗中坐》里,蕭綱吟詠了一位夕陽時分獨坐窗下的佳人,落日提供了一種光影交錯的效果,窗欞框定了畫面的聚焦點,這種時空組合無疑有著無限可能的審美感發。“杏梁斜日照,馀暉映美人。聞函脫寶釧,向鏡理紈巾。游魚動池葉,舞鶴散階塵。空嗟千歲久,愿得及陽春。”⑨余暉斜映的黯淡布景之下,佳人作為畫面結構中的唯一主體是詩人注視的焦點,而自在歡騰的游魚舞鶴作為一種點綴則襯出了佳人脫妝的失意氛圍。無可否認,佳人形象構建確實是在靜止的狀態之中在男性的凝視之下完成的,可是這并非完全的靜止不動,而是在靜止不動當中暗示了時間的流轉。為之嗟嘆的不止于黑夜將至,還有青春易逝、紅顏老去的悲哀。宮體詩中的佳人就如同靜物畫中燦爛的花卉,充滿了對時間的敏感和惶恐。而對于美的執著更是促使著藝術家們盡最大的努力在時間之流當中去捕捉每一個瞬間的美感具象。
蕭梁的宮體詩寫作在歷史趨大的建構中處于被壓抑的位置,在五四文學史觀的價值評判之下始終難逃被污名化的命運。通過對中國古典詩藝的探討分析,也許可以為宮體詩在當下的闡釋語境中找到一種新的可能性。
注釋:
①王逸.楚辭章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第6頁
②吳兆宜注,程琰刪補,穆克宏點校.玉臺新詠箋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7,第12頁
③吳兆宜注,程琰刪補,穆克宏點校.玉臺新詠箋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7,第57頁
④吳兆宜注,程琰刪補,穆克宏點校.玉臺新詠箋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7,第56頁
⑤吳兆宜注,程琰刪補,穆克宏點校.玉臺新詠箋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7,第309頁
⑥吳兆宜注,程琰刪補,穆克宏點校.玉臺新詠箋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7,第310頁
⑦吳兆宜注,程琰刪補,穆克宏點校.玉臺新詠箋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7,第269頁
⑧(英)諾曼.布列遜著,丁寧譯.注視被忽視的事物—靜物畫四論.[M]杭州:浙江攝影出版社,2000,第63頁
⑨吳兆宜注,程琰刪補,穆克宏點校.玉臺新詠箋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7,第33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