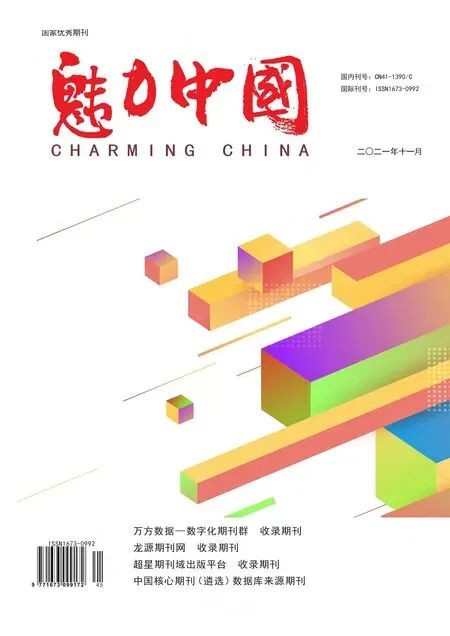探究二語學(xué)習(xí)動機(jī)中的愿景
張穎
(浙江傳媒學(xué)院 國際文化傳播學(xué)院,浙江 杭州 310018)
一、研究背景
愿景的重要性源自二語動機(jī)自我系統(tǒng)理論與心理學(xué)研究的緊密關(guān)系。2005 年,D?rnyei 依據(jù)在匈牙利對二語學(xué)習(xí)者學(xué)習(xí)動機(jī)的歷時性調(diào)查結(jié)果,借鑒了心理學(xué)家Markus &Nurius(1986)的可能自我理論和Higgins’s(1987)的自我差異理論,提出了以自我為導(dǎo)向的二語動機(jī)自我系統(tǒng)(L2 Motivational Self System)[1]。而愿景、意象等表示意識層面存在的術(shù)語,在心理學(xué)領(lǐng)域的研究中由來已久了。D?rnyei 在將心理學(xué)研究成果與二語學(xué)習(xí)動機(jī)研究融合的過程中敏銳地注意到愿景這個術(shù)語在其抽象含義以外強(qiáng)烈的感官層面,認(rèn)為它將是探究學(xué)習(xí)者動機(jī)的關(guān)鍵,“可以為增強(qiáng)二語學(xué)習(xí)動機(jī)打開新通道,即通過生成語言學(xué)習(xí)愿景和增強(qiáng)表象能力來增強(qiáng)語言學(xué)習(xí)動機(jī)”(through generating a language learning vision and through imagery enhancement)[2]。D?rnyei 甚至稱愿景為最高級別的動機(jī)構(gòu)念(the highest-order motivational construct)[3]。
二、愿景動機(jī)機(jī)制的核心是其可感知性
依據(jù)牛津英語詞典,愿景指“用想象來思考或規(guī)劃未來的能力”,或者是“一種頭腦中活生生的景象,多用于對于未來的幻想”。可見愿景是頭腦中所想象的關(guān)于未來的有畫面感的意象,可以讓我們提前對還沒發(fā)生的事有所體驗。愿景廣泛出現(xiàn)于媒體和各領(lǐng)域的語境中,van der Helm(2009)在歸納出七種不同的愿景類型后,指出了所有愿景所具備的三個特質(zhì):(1)事關(guān)未來,(2)理想中的狀態(tài),(3)主動改變的渴望。[4]
在二語學(xué)習(xí)動機(jī)語境中,愿景即學(xué)習(xí)者在頭腦中所呈現(xiàn)的未來的自己作為所期望的二語使用者的景象。D?rnyei 強(qiáng)調(diào)這一景象不同于目標(biāo)[2]。目標(biāo)是抽象的、認(rèn)知的,而愿景則包含了強(qiáng)烈的感官要素,即那些與目標(biāo)相關(guān)的可以帶來真切感受的畫面。這些畫面中的要素不局限于視覺。D?rnyei(2013)的研究指出,愿景本質(zhì)上是包含多重感官的[5]。這就類似人可以在夢境中看到畫面、聽到對話一樣。因此可以理解為,愿景是在目標(biāo)的基礎(chǔ)上加上個體對未來成功的想象,這種想象因其具體、生動,使個體好似能直接置身于目標(biāo)達(dá)成的最終時刻,看到成功的樣子,品嘗到成功的滋味。D?rnyei(2014)指出愿景所形成的可視化可感知的目標(biāo)能增強(qiáng)學(xué)習(xí)者對未來狀態(tài)的渴望,從而對當(dāng)前個體產(chǎn)生指向未來的牽引力,驅(qū)動個體調(diào)集能量,做出改變以向未來靠攏[3]。可見,愿景之所以具有強(qiáng)大的驅(qū)動力,未來目標(biāo)狀態(tài)在頭腦中可感知的呈現(xiàn)方式是關(guān)鍵。要探究愿景的動機(jī)機(jī)制,就要抓住其可感知性這一核心特點。
三、愿景與二語自我導(dǎo)向(理想自我和應(yīng)該自我)
愿景是通過二語動機(jī)自我系統(tǒng)理論進(jìn)入二語動機(jī)研究領(lǐng)域的。我們可以看到,在愿景中,對未來自我的意象是整個機(jī)制的核心,語言在其中作為自我的一部分而存在。這種整體性和可感知性的特質(zhì)促使D?rnyei 采用全新的方式來理解二語學(xué)習(xí)動機(jī),在借鑒融合了心理學(xué)研究中同樣強(qiáng)調(diào)“可以感受到的圖像和感覺”的可能自我理論和自我差異理論后,構(gòu)建了二語動機(jī)自我系統(tǒng)理論。
愿景是二語動機(jī)自我系統(tǒng)機(jī)制的基礎(chǔ),但它并不直接出現(xiàn)在該系統(tǒng)的三元架構(gòu)中。二語動機(jī)自我系統(tǒng)包含三個要素:理想二語自我,應(yīng)該二語自我和二語學(xué)習(xí)體驗。理想二語自我表示個體理想自我中與二語學(xué)習(xí)相關(guān)的方面,如果個體理想中要成為的人能熟練掌握某種第二語言,為縮小現(xiàn)實與理想之間的差距,就能產(chǎn)生較強(qiáng)的學(xué)習(xí)動力;應(yīng)該二語自我,表示個體認(rèn)為自身應(yīng)具備的與二語學(xué)習(xí)相關(guān)的特征,以滿足他人的期待、避免負(fù)面結(jié)果的出現(xiàn);二語學(xué)習(xí)體驗,表示與具體學(xué)習(xí)情境相關(guān)的動機(jī)要素,包括教師、課程、學(xué)習(xí)同伴等對個體的影響。
在這個三元架構(gòu)中,二語學(xué)習(xí)體驗所代表的是與真實自我相關(guān)的直接體驗,包括過去和現(xiàn)在。理想二語自我和應(yīng)該二語自我則指向個體未來的狀態(tài),因此兩者合稱二語自我導(dǎo)向(future L2 self-guides)或二語可能自我(possible L2 selves)。二語自我體驗所包含的要素聚焦學(xué)習(xí)者外部環(huán)境層面,這些在傳統(tǒng)動機(jī)理論中都已有論述。而二語自我導(dǎo)向強(qiáng)調(diào)的是個體如何作為一個“完整的人”在情感、認(rèn)知及行為等方面激勵自己達(dá)到理想中的狀態(tài),以發(fā)揮其未來導(dǎo)向的作用。這是該理論區(qū)別于傳統(tǒng)的一大創(chuàng)新。
愿景在系統(tǒng)中對應(yīng)二語自我導(dǎo)向,即理想二語自我和應(yīng)該二語自我,是學(xué)習(xí)者在頭腦中構(gòu)建的關(guān)于這兩個自我的意象。愿景的存在強(qiáng)調(diào)了這兩個自我不僅描述了學(xué)習(xí)者希望達(dá)到的目標(biāo)狀態(tài),更包含了對目標(biāo)狀態(tài)具體畫面的構(gòu)建。學(xué)習(xí)者可以借此看清努力方向,產(chǎn)生持續(xù)的學(xué)習(xí)行為和自我調(diào)節(jié)行為。這部分的動機(jī)機(jī)制因而可以看作是學(xué)習(xí)者對未來想要成為的語言自我投以愿景的結(jié)果。構(gòu)建愿景,體驗其帶來的具體生動的感官體驗是學(xué)習(xí)者動機(jī)被激發(fā)的關(guān)鍵。
四、愿景與兩個可能自我的差異
在以二語動機(jī)自我系統(tǒng)為理論框架的研究中,大量研究關(guān)注兩個未來可能自我,并因此積累了豐富且寶貴的實證經(jīng)驗。但是基于理想自我與應(yīng)該自我的研究不直接等同于基于愿景的研究。
基于愿景的研究更關(guān)注操作層面。大量研究已證實理想自我、應(yīng)該自我越清晰,則學(xué)習(xí)動機(jī)越強(qiáng)(Taguchi et al.,2009[6];劉鳳閣,2015[7];詹先君,2015[8])。而提升兩個可能自我的關(guān)鍵在于增強(qiáng)愿景。因此,當(dāng)我們基于愿景來探究二語動機(jī)時,實際上把視角聚焦到與構(gòu)建可感知的想象畫面的能力相關(guān)的層面,這不僅更精準(zhǔn)地抓住了二語動機(jī)自我系統(tǒng)不同于傳統(tǒng)動機(jī)理論的核心特質(zhì),更是直接作用于干預(yù)語言學(xué)習(xí)動機(jī)的操作層面,即探究愿景的生成機(jī)制以及如何通過生成語言學(xué)習(xí)愿景和增強(qiáng)表象能力來增強(qiáng)語言學(xué)習(xí)動機(jī)。這將具有廣泛的應(yīng)用前景,使二語動機(jī)理論研究具有指導(dǎo)課堂教學(xué)的現(xiàn)實意義。
這兩種研究視角實質(zhì)上的差異,在實證研究所使用問卷的問題設(shè)置中可以得到直觀的反映。下表選取了Taguchi et al.(2009)[6]基于動機(jī)自我系統(tǒng)三要素的研究和D?rnyei(2013)從愿景視角展開的研究中所使用問卷的部分內(nèi)容。Taguchi et al.(2009)量表是國內(nèi)許多二語自我研究(韋曉保,2013[9];劉鳳閣,2015[7];詹光君,2015[8])中問卷設(shè)計的參考來源。Taguchi et al.(2009)量表沒有直接考察愿景的內(nèi)容,我們選取問卷中與理想二語自我相關(guān)的題項。D?rnyei &Chan(2013)[5]問卷則在理想自我、應(yīng)該自我以外,有專門指向愿景的題項。兩個問卷這部分都采用了里克量表,由學(xué)習(xí)者自評。通過對比可以發(fā)現(xiàn),左欄理想自我的題項考察了學(xué)習(xí)者對未來自我使用二語的具體想象,借此我們可以了解學(xué)習(xí)者是否具有此類想象,及想象的豐富程度。這有助于我們對學(xué)習(xí)者狀態(tài)的了解,但對于如何提升愿景構(gòu)建的能力提示有限。而右欄愿景相關(guān)題項則聚焦對未來自我想象能力的更多方面,如愿景的呈現(xiàn)質(zhì)量,學(xué)習(xí)者生成愿景的能力,學(xué)習(xí)者區(qū)分愿景與目標(biāo)的能力,學(xué)習(xí)者感知愿景的能力,學(xué)習(xí)者認(rèn)知習(xí)慣等。這些維度的探索可以豐富我們對愿景的的認(rèn)識,從而使增強(qiáng)愿景的操作路徑更加清晰。

五、基于愿景的二語動機(jī)研究
基于愿景的研究可以圍繞進(jìn)一步深化對愿景的認(rèn)識來進(jìn)行,也可以從愿景的可感知性出發(fā),探索將愿景的動機(jī)效應(yīng)轉(zhuǎn)化為切實的學(xué)習(xí)行為的方法。
(一)進(jìn)一步認(rèn)識愿景的研究
D?rnyei &Chan(2013)的研究在驗證了愿景的動機(jī)效應(yīng)之余,證實了學(xué)習(xí)者的感知、表象等生成意象的能力一定程度上能決定動機(jī)強(qiáng)度。此研究還證實了學(xué)習(xí)者可以有多個獨(dú)立的語言可能自我。You &Chan(2015)[10],You,D?rnyei &Csizér(2016)[11]揭示了愿景的動態(tài)屬性,證實愿景的變化會影響動機(jī)強(qiáng)度、學(xué)習(xí)行為和語言水平,而這些因素的變化也會反過來觸發(fā)愿景的改變。You,D?rnyei &Csizér(2016)的研究中還分析了性別差異在愿景中的表現(xiàn)。Vasquez &Buehler(2007)[12]證實愿景中的自我是以第一視角還是第三視角出現(xiàn)會帶來不同的動機(jī)效果。這些國外研究先例加深了我們對愿景的認(rèn)識,同時也給我們的研究打開了新的視角,有關(guān)愿景的未知還有很多,我們可以沿這條道路繼續(xù)探索。另外,隨著動機(jī)研究進(jìn)入社會動態(tài)階段,在研究方法上可以采用混合式的方法,更多進(jìn)行歷時的研究,從而更好地揭示愿景的本質(zhì)。
(二)將愿景的動機(jī)效應(yīng)轉(zhuǎn)化為切實的學(xué)習(xí)行為的研究
二語愿景的激勵作用并非自動發(fā)生,D?rnyei 給出了六大動機(jī)策略,但這些策略的提出主要基于理論總結(jié),缺乏實證研究檢驗,具有強(qiáng)烈的假設(shè)色彩。雖然一些研究者已通過實施增強(qiáng)愿景的訓(xùn)練活動進(jìn)行動機(jī)干預(yù)研究,調(diào)查愿景對二語動機(jī)的影響(Magid &Chan,2012[13];Sampson,2012[14]),但是研究總量仍讓極少。怎樣讓二語愿景更有可能轉(zhuǎn)化為二語學(xué)習(xí)的行動,愿景的變化與學(xué)習(xí)努力程度波動的關(guān)系等我們?nèi)灾跎伲祟愌芯窟€有待加強(qiáng)。喜人的是在現(xiàn)有研究中大部分學(xué)習(xí)者不僅通過活動提升了努力程度,而且對用于增強(qiáng)愿景的課堂活動非常歡迎,樂于參加(Chan,2014)[15]。這讓我們可以對未來的研究抱有信心。
六、小結(jié)
二語學(xué)習(xí)動機(jī)中的愿景指學(xué)習(xí)者在頭腦中所呈現(xiàn)的未來的自己作為所期望的二語使用者的景象。它的可感知性,即它所包含的那些與目標(biāo)相關(guān)的可以帶來真切感受的畫面是它具備動機(jī)激勵作用的關(guān)鍵。對這一特質(zhì)的把握使基于愿景的動機(jī)研究區(qū)別于基于理想自我和應(yīng)該自我的研究,因而研究側(cè)重點應(yīng)該轉(zhuǎn)向進(jìn)一步豐富對愿景的認(rèn)識和對愿景轉(zhuǎn)化為學(xué)習(xí)行為可行性的進(jìn)一步探索,從而實現(xiàn)理論向指導(dǎo)教學(xué)的轉(zhuǎn)化。具體來說,我們可以借鑒國外已有的研究范式打開思路,推進(jìn)愿景相關(guān)的研究在中國語境下的開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