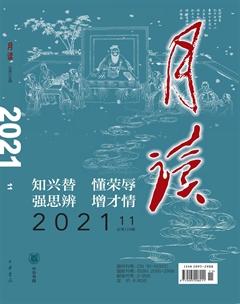張益州畫像記(節(jié)選)a
〔宋〕蘇洵
至和元年秋b,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c。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yǎng)亂,毋助變。眾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為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推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于凈眾寺d,公不能禁。
眉陽蘇洵言于眾曰e:“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是惟元年之秋,如器之欹f,未墜于地。惟爾張公,安坐于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為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繄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為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于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砧斧令g。于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于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qū)之以法,惟蜀人為易。至于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于法律之外,以威劫其民,吾不忍為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
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yè)在史官,無以像為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于斯?雖然,于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鄉(xiāng)里之所在,以至于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h,以想見其為人。而史官亦書之于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于心,則存之于目;存之于目,故其思之于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為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為之記。
公,南京人i,為人慷慨有大節(jié),以度量容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
(《全宋文》卷九二七)
注釋:
a 張益州:即張方平,字安道,自號樂全居士,北宋大臣,官至參知政事。當(dāng)時任益州知州(治今四川成都),故稱張益州。
b 至和:宋仁宗趙禎的年號,時間從1054年到1056年。至和元年即公元1054年。
c 京師:京城,指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開封)。
d 凈眾寺:又名萬福寺,在成都西北。
e 眉陽:蘇洵是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
f 欹(qī):傾側(cè)不平。這里指傾斜將倒的狀態(tài)。
g 以砧(zhēn)斧令:即“以砧斧令之”。用刀斧等刑具命令他們,使他們因畏懼而服從。砧,古代刑具,即鍘刀下面的砧板。令,役使,差遣。這里的意思是“命令”。
h 詰(jié):追問,進一步深問。下文的“無以詰”是無以反駁、無話可說的意思。
i 南京:北宋的南京,即今河南商丘。
大意:
宋仁宗至和元年秋天,蜀人傳言有敵寇侵犯邊境。駐邊軍士夜里都惶恐不安,城外也沒有人敢居住了。謠言流傳開來,京師大為震驚。正當(dāng)朝廷準(zhǔn)備下令選派將帥時,皇帝說:“既不要姑息延誤而釀成禍亂,也不要輕率調(diào)兵,助使變亂發(fā)生,盡管謠言蜂起,但我的主意是堅定的。我認為外患并不足以使人驚慌,只怕內(nèi)亂從中發(fā)生。這既不能用文書法令讓他們遵守法度,也不能用武力去同他們較量,我只需要一兩個大臣去處理。誰能協(xié)調(diào)好用感召教化的方法和用武力較量的方法兩者之間的關(guān)系,我就派誰去安撫。”大家推舉說:“張方平就是這樣的人。”皇帝說:“可以。”張公以贍養(yǎng)雙親為由加以推辭,但沒有得到允許,于是就出發(fā)了。冬季十一月,他到了蜀地。到達的當(dāng)天,他就遣返了屯守在邊境的軍隊,撤除了邊境的守備,并派人到各郡縣去告諭:“敵寇由我來對付,就不必勞苦你們了。”第二年的正月初一,蜀地百姓像往常一樣慶賀新年,從此也就平安無事了。又過了一年的正月,百姓私下商量要在凈眾寺里擺放張公的像。張公無法禁止大家。
眉陽人蘇洵對眾人說:“變亂還沒發(fā)生時,容易治理;變亂已經(jīng)發(fā)生,也容易治理。變亂正在醞釀中,但還沒有實際發(fā)生,這叫作將亂,將亂的狀況是最難治理的。既不能因為有變亂的萌芽而操之過急,也不能因變亂還沒發(fā)生就放松警惕。至和元年秋天蜀中的局勢,就好像器物已經(jīng)傾斜,但還沒有倒在地上。只有你們的張公,安穩(wěn)地坐在旁邊,面不改色,慢慢地站起來,扶正了它。扶正之后,又從容身退,而且沒有驕矜自夸的神情。幫助天子治理百姓而不知疲倦的人,只有你們的張公。你們?nèi)克派嫦聛恚褪悄銈兊母改浮6覐埞?jīng)對我說:‘老百姓的性情是可以改變的,只看上邊的官員如何對待他們。人們都說蜀人常常發(fā)生變亂,于是上面就用對待盜賊的態(tài)度去對待他們,用處理盜賊的法令去懲罰他們。對于本來已經(jīng)小心翼翼的百姓,卻用嚴刑峻法去鎮(zhèn)壓,于是百姓才狠下心來拿他們的父母妻兒所仰賴的身體,去投靠盜賊,所以往往釀成大亂。如果用禮義去約束他們,用法度去差使他們,蜀人是最容易治理的。至于為政太苛逼迫他們而發(fā)生變亂,即使是在號稱禮樂之邦的齊魯之地,也會這樣。我用對待齊魯百姓的辦法來對待蜀人,蜀人也會用齊魯?shù)胤桨傩盏臉?biāo)準(zhǔn)來約束自己。超出法度之外而為所欲為,用權(quán)勢欺壓百姓,我不忍心做呀!唉!愛護蜀人如此深厚,對待蜀人如此仁慈,在張公以前的官員中,我還不曾見過呢。”大家聽了,都再三叩拜說:“是這樣的。”
蘇洵又說:“把張公的恩德銘記在你們的心里,你們死了,就銘記在你們子孫的心里。他的功業(yè)將由史官來記載,不必畫像了。況且張公心里也不愿這樣,你們看怎么辦呢?”大家都說:“張公本來不在乎畫像。即使這樣,我們心里卻深感不安。現(xiàn)在就是平時在家里聽說有人做了一件好事,還要問問那人的姓名和他所住的地方,一直到他身材的高矮、年紀的大小、容貌的美丑等,甚至有人還要問他的生平和嗜好,由此來想見他的為人。史官也會把這些情況寫在他的傳記里,意思是讓天下之人不僅在心里紀念他,而且在眼里也能看見他。眼里留存著他的容貌,心里對他的紀念也就愈加牢固。這樣看來,畫像也不是沒有用吧!”蘇洵無法反駁他們了,于是替他們寫了這篇畫像記。
張公出生于南京,為人慷慨且有高尚的節(jié)操,以器度寬廣聞名天下。國家遇到重大事情,張公是可以托付的。
【點評】
此文是蘇洵的代表作,作者先記事,后議論,以多種手法塑造了一位寬政愛民的官員形象。
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傳言少數(shù)民族首領(lǐng)儂智高將入蜀,蜀地因而發(fā)生騷亂,人心惶惶,軍隊也調(diào)集起來。朝廷委派張方平前去處理。張方平到任后采取安撫的辦法,撤除邊境守備,號召百姓從事農(nóng)桑,很快就穩(wěn)定了局勢,恢復(fù)了社會秩序。兩年后,張方平奉召回京,當(dāng)?shù)匕傩諡榱吮硎緦λ膽涯睿瑸樗籼茫嬒瘛LK洵為蜀地人,與張方平也有私交,很敬重他的為人,為此寫下了這篇“畫像記”。
文章突出了為官者張方平臨危受命的勇氣和擔(dān)當(dāng),遇事沉著冷靜、舉重若輕的非凡才干,以及功成身退、謙虛謹慎的品格和風(fēng)度;同時也從側(cè)面反映了作者蘇洵的為政思想,那就是以民為本,以禮義安撫人心。
(海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