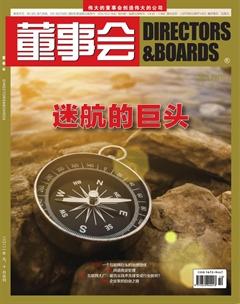互聯網大廠:能否從技術先鋒變成行業新風?
聶輝華
最近的互聯網行業很可能迎來了“至暗時刻”。先是螞蟻金服上市被叫停,然后是滴滴上市涉及數據安全問題,接著是在線教育企業被“團滅”,最近阿里又出現女員工被性侵事件。可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果說2021年之前的十年是互聯網企業“野蠻生長”的春天,那么此刻就是互聯網企業的漫長寒冬。中國網民數量已經接近飽和,此謂“天時”已盡;中美之間的互聯網技術鴻溝已經縮小,此謂“地利”已失;互聯網巨頭的資本收割惹得民意沸騰,此謂“人和”已去。我們不禁要問:中國互聯網企業,何去何從?
從上世紀90年代末期互聯網技術開始引入中國以來,中國的互聯網行業快速發展。互聯網技術與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云計算等底層數字技術的結合,催生了數字經濟的崛起。根據中國信通院的報告,中國數字經濟的規模從2005年的2.6萬億元一直增長到2020年的39.2萬億元,占GDP(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2005年的14.2%一直增加到2020年的38.6%。互聯網行業或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主要得益于中國的“天時地利人和”。一是人口基數大,消費群體廣,同時應用場景豐富;二是政府管制松,并且互聯網企業與國企沒有什么正面競爭;三是利用西方先進技術,實現了“彎道超車”。尤其是,以騰訊、阿里、華為為代表的互聯網大廠,在人工智能、云計算、物聯網、在線支付等先進技術領域,已經占據了世界第一梯隊,儼然成為數字經濟領域的技術先鋒。
但是,互聯網大廠不能在國運帶來的功勞簿上“躺平”,從此享受壟斷紅利。當野蠻生長帶來的暴利和亂象引起口誅筆伐時,對互聯網行業的規范管理必然要跟上。這一點,歐洲的數字企業已經見證了歷史,中國互聯網大廠應該清醒地看到監管拐點已經來臨。在這種大背景下,不管是互聯網大佬們“退隱山林”,還是互聯網大廠低調行事,抑或是涉事大廠“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都只是迷失在個案的應對和公關之中,無法規避一系列監管風暴。
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必然要大力發展數字經濟、實現數字化治理,這已經是“制度優勢”的一部分。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中國的互聯網企業應該放長歷史的視界,展示更大的格局。要走出當下的困境,互聯網大廠應該勇敢地擔當起時代的重要使命。這個使命就是,從單純的追求技術先鋒,轉變為引領行業新風;從傳統的勞資關系,轉變為敬畏契約精神,重塑商業倫理。
人類社會前進的方向,是從農耕文明進化到商業文明,從人情社會進化到契約社會。現代市場經濟,本質上是一種商業文明和契約社會。它們背后的支撐力量是契約精神。商業文明中的契約精神,至少包括以下幾點。第一,契約關系是平等自愿的。在商業交往和工作關系中,大家只有分工不同,沒有高低貴賤之分。第二,契約關系是一種非人格化的交易機制。規則重于人情,制度勝過關系。第三,契約關系是有邊界的,理應權責對等、公私分明。單位不是領導自己的“地盤”,員工不是領導的“仆人”。
互聯網行業是數字經濟的領頭羊,互聯網大廠是中國經濟的“名片”。權力越大,責任越重。因此,互聯網大廠應該帶頭推進商業文明,貫徹契約精神。比如,談生意能不能少喝酒甚至不喝酒?喝酒能不能完全自愿?如何在工作規則中全面貫徹男女平等?能否借機構建一套完整的反職場性騷擾制度,并且在整個相關行業推廣?進一步,能不能規范加班現象,防止無限“內卷”?能不能把下班時間和周末還給家庭?同行業之間,能否尊重對手,恪守底線?
憑心而論,今天的互聯網大廠,在削弱等級制度、提高工作待遇、減少酒桌文化方面,總體上做得比傳統行業要好。但是,與互聯網大廠擁有的巨大光環和影響力相比,它們還有很大的提高空間。“不要浪費每一次危機”。與其被動應對個案困境,不如勇敢革新自我,并且推動行業新風的形成。如此,互聯網大廠才能行穩致遠,成為現代化中國的進步力量,并重新贏得民意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