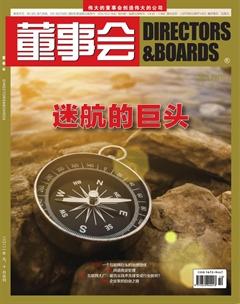一份引發爭議的歐盟委員會公司治理報告
John C Coffee Mark J. Roe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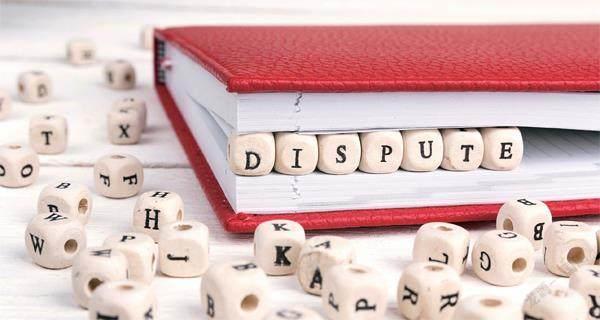
2020年7月,歐盟委員會(the European Commission)發布了其委托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制作的報告——《董事職責與可持續化公司治理研究》。該報告評估了歐盟領域內上市公司的“短視主義”(short-termism)問題,討論了其與當前市場實踐以及監管框架之間的相關性,并在歐盟層面上確定可能的解決方案。
在該報告中,安永通過案頭研究和田野調查,對歐盟內部上市公司短視主義問題進行了證據的收集和分析。收集的數據顯示,在上市公司中,股東支出占公司收入的比重不斷上升,從1992年的不到1%增至2018年的近4%;與此同時,公司資本性支出(CAPEX)和研發性支出(R&D)占收入的比重卻一直在下降。安永認為,這是證明歐盟上市公司存在短視主義趨勢的重要依據,而此趨勢將給歐盟乃至整個世界帶來諸多不利影響,例如環境惡化、社會不平等、企業發展資源減少等,并將威脅“氣候變化《巴黎協定》”以及“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的實現。
報告指出,公司短視主義根源于監管框架的導向作用和市場實踐的通行做法,其主要體現在以下七個方面:1.對董事職責和公司利益的狹隘理解;2.來自短期投資者的巨大壓力;3.公司缺乏可持續發展的戰略視角;4.董事會薪酬結構不合理,誘使董事更關注短期股東利益,而不是為公司創造長期價值;5.當下的董事會構成不利于公司可持續性轉變;6.公司治理框架和實踐沒有充分關注利益相關者的長期利益;7.其他利益相關者或監管機構無權代表公司發起訴訟,導致董事為公司長期利益行事的義務是有限的。
基于以上,安永認為歐盟需要采取措施來引導公司決策以促成更為可持續化的公司治理,歐洲各國的公司治理框架各異,在歐盟層面采取統一行動可以使問題可以得到更為有效的解決。對此,安永也為歐盟給出了自己的改革建議。
2020年11月11日至13日,牛津大學舉行了為期三天的國際會議,為了更好地評估和適用該報告,此次會議對其進行了介紹與討論。哈佛大學法學院的馬克?J.洛教授和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的約翰?C.科菲教授也在會上對其進行了評論。馬克?J.洛教授對報告的具體內容進行了細致剖析,而約翰?C.科菲教授則在更深的層面上給出了他對短視主義的思考和建議。
藥用錯了可能適得其反
《董事職責與可持續化公司治理研究》聲稱,有證據顯示,短視主義削弱了歐盟的公司治理,并提出了一系列措施來支持可持續化的公司治理。馬克?J.洛教授等專家認為,該報告在證據以及分析上存在重大缺陷:
毫無意義的證據
該報告的第3.1.1節介紹了其主要用以證明歐盟上市公司短視主義的經濟證據:歐洲上市公司總支出(股息和股票回購)率的增加與投資(CAPEX和R&D)強度的下降(1992-2018)。
美國讀者可能會熟悉這套推理邏輯,因為他們可能聽到過對企業高支出的抱怨,稱其削弱了美國企業的投資能力。但首先需要明確的是,總支出對于公司長期投資能力來說是一個誤導性的指標,因其實際上還取決于公司是否仍在籌集新資金。因此,企業的凈支出才是真正關鍵的指標。只要支出被負債或股本等新融資的注入所抵消,公司就不會被剝奪用于投資的資金,而這正是現實中的主要情況:股東凈支出率不是特別高。舉例而言,在1992-2019年期間,歐盟的公司分配了2.6萬億歐元股息并回購了6,640億歐元的股份(總計向股東支出了約3.2萬億歐元),約占這些公司總凈收入的60%。但在同一時期,歐盟上市公司發行了2.5萬億歐元的股票,因此股東的凈支出僅為7570億歐元,僅占這些公司總凈收入的14%。
其次,該報告通過對投資的分析得出結論:歐盟上市公司的CAPEX和R&D強度有所下降。得出這樣的結論,其實是因為其研究的樣本是不完整、前后不一致且有偏向性的。例如,該報告并沒有對凈收入為負的研發密集型公司進行審查,但此類公司的R&D是資本市場運作良好的最好標志,沒有理由將這些公司排除在外。我們通過對完整且一致的樣本進行考察后發現,在報告選定的時間段內,無論是從絕對金額還是從收入份額來看,歐盟上市公司的CAPEX和R&D實際上都在增加。
第三,報告傾向于使用總支出占凈收入比重的統計數據來衡量向股東支出是否剝奪了公司投資所需的資金,但這一數據具有加倍的誤導性。它錯誤地暗示:“凈收入”反映了公司運營能夠產生的全部投資資源。實際上,凈收入是在減去用于將來活動支出的許多費用后才得出的,例如大量的R&D支出,也就是說,凈收入是經過特定投資后的盈余。實際上,在同等變量下,對研究進行更多投入的公司將擁有更低的凈收入和更高的股東支出比率。
綜上所述,歐盟上市公司的股東支出體量并沒有剝奪他們進行投資或創新的能力。盡管歐盟上市公司一直在進行大量投資,并不斷增加投資,但在面臨有吸引力的投資機會時它們已經積累了足夠的現金儲備來追加投資。
考慮不周的改革方案
該報告從七個方面擬議了改革措施:1.拓寬董事責任,將利益相關者的利益納入董事職責考量;2.減輕投資者的壓力,比如增加長期股東的投票權;3.要求進行可持續的計劃和披露;4.將高管薪酬與持續性指標掛鉤;5.要求公司在董事會提名中考慮持續性;6.要求公司董事會建立相應機制來與內、外部利益相關者在識別、預防和緩解持續性風險方面進行接洽,并作為公司戰略的一部分;7.允許除股東之外的利益相關者提起訴訟,指控董事違反了勤勉和忠實義務。
“短視主義將導致公司投資數額下降”,這一說法看起來合理,但更像是個海市蜃樓,這也讓人不由地懷疑上述改革措施其合理性,這些改革措施提出的前提正是這一被上文所否定的說法。但報告并未明確指出真正的問題所在——外部性和分配問題。該報告認為,公司治理的問題在于破壞性極強的短視主義。它指出短視主義對環境、氣候和其他利益相關者都十分不利,但其實它將縱向的時間問題和橫向的外部性問題、分配問題混為一談。“負外部性”是指由公司決策者之外的其他人員來承擔的成本,這可能會誘使公司決策者進行對總體有害但對自己有利的決策。即使在沒有外部性的情況下,不合理的分配問題也會引起擔憂,在這種情況下,被分配者的收益懸殊巨大,應該獲利的群體沒有獲利,不該獲利的群體卻得到了好處。
此外,當該報告轉向短視主義的其他證據時,它有選擇地列舉了一些支持其觀點的學術研究,但并沒有提及還有大量文獻持相反觀點。有重要研究顯示,通過對一個時間段內的樣本進行調研,在公司中并沒有發現短視主義的存在。不僅如此,一些實證研究甚至表明公司目前可能存在過度長期主義的問題。
疾病的治療講究對癥下藥,沒有哪種藥能夠包治百病,藥用錯了甚至可能適得其反。我們希望該報告的提案不會被歐盟委員會遵照執行,如果歐盟委員會真的要執行,也必須等到潛在問題以及提案的可適用性被重新徹底檢驗之后,也必須重新徹底地檢驗潛在的問題和提案的可適用性。
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在約翰?C.科菲教授看來:安永為歐盟委員會做的《董事職責與可持續化公司治理研究》闡釋了一個正當性問題(legitimate problem),但其提出的補救措施與問題之間并沒有緊密的聯系。不客氣地說,安永“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實際上,相較于董事會,問題的癥結更在于股東,更準確地說,在于代表公司最終實益享有者的專業中介機構(institutional intermediaries)。如今,從僅持股一兩年的激進對沖基金到永久股東(通常為多元化資產,甚至是指數資產管理公司,貝萊德(BlackRock, Inc.)就是其中的標志性例子),在公司這個連續體中到處都有中介機構的身影。
我們需要明確的關鍵一點是,除非雙方偶爾達成觀念上的一致并結為同盟的情況下,激進主義者往往是股東主導地位的自然擁護者,并且通常對持續性政策持敵對態度,而永久股東則更傾向于采取相反的立場來支持持續性發展戰略。
證據與擬議的改革措施
安永在提交的報告中重點關注了向股東支出的現金總額占公司收入比重的上升趨勢,以及CAPEX和R&D占收入比重的下降趨勢。雖然該調查結果令人震驚,但并不能作為具有決定性的證據,因為這一數據實際上取決于公司是否籌集新的股權資本(equity capital)來代替這一支出,以及這一替代過程在大多數歐洲國家是否有充足的機會得以實現。
使這一問題更加嚴重的是,支出/收入比超過75%的公司數量也大幅增加。在一些歐洲國家(斯洛伐克和比利時),此比率現已超過100%。是什么原因導致了這些高支出比率產生?表面上看,股票回購的盛行成為這一現象的直接導火索,而挖掘其背后的深層原因,實際上是來自激進股東的壓力以及回購股票帶來的稅收優惠造成了這一現象。
針對這些問題,安永在報告中提出了一些改革方案,我們將其簡要概括為四個方面并加以分析。
其一,停止使用季度收入(quarterly earnings)這個指標,取消盈余預測(earnings guidance)。在我看來,這實際上是在要求股東“戴上眼罩”。作為回應,股東勢必將求助于證券分析師,選擇性披露現象也將變得更為普遍。而股東在黑暗中進行交易,內幕交易現象也可能會增加,隨之而來的將是市場的加劇波動。總而言之,不管怎么樣,富有的股東都將獲取到他們所需的信息,但散戶投資者卻只能依靠自我猜測。
其二,限制管理層,以使他們至少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不能出售作為報酬的股票。盡管這一舉措響應迅速,短時間內可以帶來顯著的效果,但它可能會破壞歐洲高管勞動力市場的穩定,并導致大量高管人才流向監管環境相對寬松的美國公司,這顯然將使歐洲公司的國際競爭力大幅降低。另一方面,即使這一舉措使管理層不再那么以短期績效為導向,但其并不能改變股東對短視主義的偏好,也不會打消激進基金為追求短期業績而施加壓力的動機。
其三,改變董事會的組成,尤其是實現更大程度的性別平等。安永刻板地認為董事會中的女性成員可能會更為優先地考慮公司的持續性發展,而不是利潤。然而一旦由舊董事們組成的提名委員會選舉出了新董事,這一假設將被證明是錯誤的,因為可以預見的是現有董事會可以很容易地找到這樣的女性董事,她們完全接受股東至上的理念,但對公司持續性漠不關心,而這也正是董事選舉的標準模式。如果真想要找到一個忠誠支持公司持續性的董事,倒不如建議他們去找一個“嚴格的素食主義者”。
其四,改變涉及公司董事的法律規則,尤其強調持續性標準和對利益相關者的責任。盡管我不反對對法律規則稍作修改,但我堅信這種方法所帶來的收益將是微不足道的,且其影響將主要是象征性的。首先,當下現有的法律規則并沒有告訴董事他們必須在短期內最大化價值,甚至根本沒有告訴他們要最大化股東價值。在美國,特拉華州僅在公司要出售時才要求股東財富最大化,這就是所謂的“露華濃規則(Revlon rule)”——美國其他州的法律在這一點上并不認同特拉華州。坦率地說,董事的行為方式更多的是由習慣和觀念決定的,即使美國法律并沒有作出這樣的要求,習慣和觀念都使董事相信他們有責任使股東價值最大化。
依賴于董事職責的法定變更來改變董事行為存在另外一個更明顯的問題:歐洲的法律規則并不像美國那樣能夠迫使董事去承擔責任。眾所周知,美國擁有相對活躍的訴訟體系,其定義要素是集體訴訟(class action)、或有費用(contingent fee)、陪審團審判(jury trial)、懲罰性賠償(punitive damage)以及針對原告的少量費用轉移(fee-shifting)。但即使在美國,我們也不會強制執行勤勉義務(duty of care),而且通常來說其也不可以被強制執行。
我并不反對通過法律來修改董事職責的想法,但可以預見的是,謹慎的公司律師將指導董事們去滿足所有形式條件和程序要求,但不會做出任何實質性轉變。像往常一樣,形式將戰勝實質。
什么改革措施真正有效?
如果擬議的改革措施將難以帶來實質性效果,那什么舉措才能真正行之有效呢?
首先,如果回購是問題所在,有一個簡單的補救方法:使用稅法來減少回購。稅法如果規定股票以回購方式出售將被賦予更高的稅率的話,股東將不太可能想要進行股票回購,也沒有這種需求。這正是“奧卡姆剃刀( Occams Razor)定律”的一個典型示例,“如無必要,勿增實體”,即動用最少的部分來獲得最簡單的答案。
同理,如果短視主義是問題所在,且這一觀念受到只持有公司股票一兩年的激進股東的宣揚,那就考慮“終身投票制度”(tenured voting)——在這種制度下,長期股東將獲得更多投票權。硅谷其實早就意識到,雙重股權結構也可以遏制短視行為。但是就我個人而言,我并不喜歡這兩種選擇,任何基于任期增加投票權的行為都應該被加以限制,但不可否認的是,這兩種措施都與問題切實相關并且可以迅速響應。
觀點差異的根源在于,科菲教授更傾向于將改革的視角與重心放在股東身上,而報告卻忽略了這個問題。機構投資者不僅持有絕大多數股票(按價值加權基準在美國約占75%),而且其持股比例近十年來異常集中地升高。美國目前由貝萊德集團、道富銀行(State Street Corp)和先鋒集團(Vanguard Group)組成的“三巨頭”持有了美國上市公司股份總額的20%,并擁有25%的投票權。更重要的是,他們會定期進行共同投票以支持可持續發展提案,尤其是與氣候變化相關的股東提案。這三巨頭都是永久性股東,他們在迫使上市公司作出政策轉變后并沒有像對沖基金那樣退出公司。
我們可以輕易列舉出很多大型多元化機構投資者支持可持續化公司治理的證據。具有代表性的是發生在2018年的一個重大事件,當時三巨頭聯合其他機構投資者迫使荷蘭皇家殼牌公司(Royal Dutch /Shell Group of Companies)和英國石油公司(BP p.l.c.)轉變長期堅持的立場,大大提前了他們實現“碳中和”(carbon neutrality)的進程。盡管能源公司們曾一度激烈抵抗,但在被三巨頭槍指腦袋的情況下也只能乖乖就范,并做出了他們想要的轉變。
更為有趣的是,對于評估投票提案的影響,這些大型指數化機構正在將目光從單個公司轉向整個投資組合。正因如此,它們推行的一些提案,比如一個針對氣候變化的建議,可能會降低目標公司的股票價值而提高其投資組合中其他五只股票的價值。很多人也曾指出,至少在投資組合的整體收益超過其損失的情況下,這一轉變為大型投資機構提供了一種經濟上合理的動機來控制外部性。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激進的對沖基金通常會做出相反的選擇。2017年,美國第二大電力生產商NRG能源公司(NRG Energy, Inc.)宣布將改革其能源生產政策,將電力生產能源從“骯臟”轉變為“清潔”,并開始收購太陽能和風能公司。但當時最大的激進投資基金之一,埃利奧特資本管理公司(Elliott Capital Management Corp),對此提出強烈反對。這一轉變使得NRG的股價大幅下跌并招致埃利奧特公司領導的一場委托書爭奪戰(proxy fight)。最終,激進投資者贏得了勝利,并將NRG恢復為最初的骯臟能源政策(dirty energy policy)。這起事件是反持續性政策的一個典型例子,而由激進主義者引發的類似事件不勝枚舉。
簡而言之,在追尋公司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上,對沖基金和資產管理者既是主要盟友,也是頭號大敵。這也說明建立一個可持續發展董事委員會來定期與這些基金進行磋商、招攬盟友并平息批評意見是非常必要的。此外,持有數萬億美元投資組合的大型機構實際上比單個董事會擁有更專業的知識來支持公司的持續發展,并可以提供切合實際的指導。
更重要的是,如果想要讓歐洲的公眾公司能夠抵御短期導向型基金的襲擊,最簡單的方法可能還是使用稅法以更高的稅率對其在持股三年內出讓股票的行為進行征稅,這將有效遏制其短期持股的欲求,但不會對永久股東產生不利影響。矛盾的是,股東們既支持又反對可持續化公司治理。永久股東和激進基金除了偶爾結為盟友的時候,已然被鎖定在一場尚未宣戰的虛擬戰爭中;公共政策應鼓勵前者而反對后者,但應始終支持合作。為了行之有效,公共政策必須站好隊,選定立場,并不斷支持它的盟友。
本文還得到哈佛大學教授Holger Spamann、Jesse M. Fried,哈佛大學副教授Charles C. Y. Wang等學者的熱情支持。
編輯者羅大千,華東政法大學國際金融法律學院碩士研究生;
李高宇,倫敦國王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