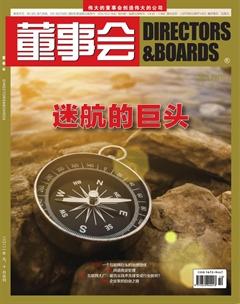一致行動協(xié)議:資本市場的“專利制度”
鄭志剛

我國資本市場從2015年開始,進入上市公司第一大股東平均持股比例低于三分之一的分散股權(quán)時代,如何加強公司控制,防范控制權(quán)紛爭和潛在的野蠻人入侵成為高科技公司創(chuàng)業(yè)團隊首先需要思考的問題之一;與此同時,隨著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專業(yè)化分工程度的加深,投資者和上市公司信息不對稱加劇,高科技公司創(chuàng)業(yè)團隊需要思考如何擺脫投資者信息不對稱下“逆向選擇”出現(xiàn)的融資困境。
我們看到,像“看似限制了技術(shù)的傳播,但反過來鼓勵了社會創(chuàng)新”的專利制度一樣,創(chuàng)業(yè)團隊簽署一致行動協(xié)議看起來為股東自由進入退出設(shè)置門檻,但卻為高科技企業(yè)成功化解上述困境提供了可行的解決方案。一致行動協(xié)議由此被我們稱為是“資本市場的‘專利制度”。
加強創(chuàng)業(yè)團隊公司控制
作為股東投票協(xié)議的一種,一致行動協(xié)議指全體或部分股東就特定的股東大會決議事項達成的,在行使召集權(quán)、提案權(quán)、表決權(quán)時,采取一致行動的一種協(xié)議。我們以通信信息領(lǐng)域的佳訊飛鴻為例。單純從持股比例來看,第一大股東,同時兼任董事長和總經(jīng)理的林菁原本無法實現(xiàn)對上市公司的相對控制。但在創(chuàng)業(yè)團隊林菁、鄭貴祥、王翊、劉文紅、韓江春等簽署了《一致行動協(xié)議書》后,林菁獲得了全體協(xié)議參與人支持,獲得在董事會和股東大會上投票表決舉足輕重的影響力,成為公司的實際控制人。
過去十年間,越來越多的非國有上市公司創(chuàng)業(yè)團隊傾向于在IPO前簽署一致協(xié)議(見表1)。而當?shù)谝淮蠊蓶|持股比例較低,加強公司控制權(quán)的動機使主要股東更傾向于在IPO時與其他創(chuàng)業(yè)團隊簽署一致行動協(xié)議。
表1 非國有上市公司IPO創(chuàng)業(yè)團隊簽訂一致行動協(xié)議的年度分布

鼓勵創(chuàng)業(yè)團隊人力資本投入
一致行動協(xié)議的另一特征是其分布具有十分典型的行業(yè)特征。那就是,在高科技企業(yè)中,創(chuàng)業(yè)團隊在IPO時更可能簽訂一致行動協(xié)議(見表2)。
表2 IPO時實際控制人簽訂一致行動協(xié)議公司的行業(yè)分布

我們注意到,隨著以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shù)為標志的第四次工業(yè)革命的興起,高科技企業(yè)需要采用更有利于研發(fā)創(chuàng)新的組織構(gòu)架。曾經(jīng)一度被認為不利于外部投資者保護的雙重股權(quán)結(jié)構(gòu),如今已經(jīng)成為各國鼓勵創(chuàng)新型企業(yè)快速發(fā)展的普遍政策工具。出于同樣的理由,實現(xiàn)控制權(quán)配置權(quán)重向創(chuàng)業(yè)團隊傾斜的一致行動協(xié)議,成為鼓勵高科技創(chuàng)業(yè)團隊人力資本投入的重要控制權(quán)安排實現(xiàn)形式。我們的研究表明,一致行動協(xié)議幫助高科技創(chuàng)業(yè)團隊形成對未來穩(wěn)定控制的預(yù)期,保護和鼓勵創(chuàng)業(yè)團隊人力資本的持續(xù)投入。而簽訂一致行動協(xié)議的高科技企業(yè)由于更重視研發(fā)投入與研發(fā)隊伍建設(shè),企業(yè)未來績效表現(xiàn)更為優(yōu)異。
另一方面,隨著高科技企業(yè)業(yè)務(wù)模式創(chuàng)新的不斷深入,所知有限,甚至“理性無知”的外部投資者越來越無法理解企業(yè)的業(yè)務(wù)模式創(chuàng)新的真諦,甚至對業(yè)務(wù)模式現(xiàn)金流從何而來也無從得知。外部投資者和創(chuàng)業(yè)團隊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可能導(dǎo)致有潛力的高科技企業(yè)無法獲得投資的逆向選擇問題。此時,創(chuàng)業(yè)團隊有必要通過向資本市場傳遞特殊的信號來緩解這一信息不對稱導(dǎo)致的逆向選擇問題。
我們基于一致行動協(xié)議的研究同樣表明,如果創(chuàng)業(yè)團隊簽訂一致行動協(xié)議,該公司由于向資本市場發(fā)出上述積極信號,會在IPO時折價率顯著降低。同時,從短期經(jīng)濟后果來看,市場將對簽訂一致行動協(xié)議的事件作出積極評價,對解除一致行動協(xié)議的事件作出負面評價。上述結(jié)果清楚地表明,一致行動協(xié)議成為信息不對稱下高科技企業(yè)向外部投資者傳遞信號的特殊方式。一致行動協(xié)議的簽訂表明,該公司獨特的業(yè)務(wù)模式不是部分頭腦發(fā)熱的少數(shù)人的“一意孤行”,而是同樣可以稱得上是該領(lǐng)域?qū)<业摹耙蝗喝恕钡墓餐J同和集體背書。
內(nèi)部人控制的道德風(fēng)險傾向有限
盡管我們看到一致行動協(xié)議在鼓勵人力資本投資等方面的潛在作用,理論界與實務(wù)界對這種控制權(quán)加強實現(xiàn)形式的質(zhì)疑卻長期存在。這是因為在創(chuàng)業(yè)團隊為加強控制權(quán)形成的一致行動中,我們或多或少看到實際控制人“現(xiàn)金流權(quán)與控制權(quán)分離”的影子。理論上,實際控制人作為協(xié)議團體的“領(lǐng)導(dǎo)者”,擁有較高的個人威望、持股比例優(yōu)勢和其他協(xié)議簽署人無法分享的私人信息,從而可能在協(xié)議成員協(xié)商時占據(jù)優(yōu)勢。然而,實際控制人的實際出資比例卻只占一致行動人整體持股比例的一小部分,從而出現(xiàn)其控制權(quán)與現(xiàn)金流權(quán)的分離。當現(xiàn)金流權(quán)與控制權(quán)分離時,由于責(zé)任小于權(quán)利,實際控制人有動機通過資金占用、資產(chǎn)轉(zhuǎn)移和關(guān)聯(lián)交易等行為對公司資源進行挖掘掏空,使外部分散股東的利益受到損害。因此,投資者們擔(dān)心創(chuàng)業(yè)團隊通過一致行動協(xié)議加強公司控制,形成內(nèi)部人控制。

我們的研究表明,簽訂一致行動協(xié)議的企業(yè)不會必然導(dǎo)致實際控制人隧道挖掘上市公司資源的行為。這一定程度源于一致行動協(xié)議的“事前”屬性。“金字塔”股權(quán)結(jié)構(gòu)等傳統(tǒng)控制權(quán)安排是在公司完成IPO、已經(jīng)實現(xiàn)外部融資后,迫于外部緊張形勢(例如,面臨接管威脅,甚至野蠻人入侵)下所采取的具有道德風(fēng)險傾向的手段,是事后的公司控制權(quán)安排。而一個公司在上市IPO時選擇一致行動協(xié)議需要在招股說明書中予以充分信息披露。投資者購買該公司發(fā)行股票的決定,是在充分評估控制權(quán)傾斜配置可能對自己投資收益和安全影響的基礎(chǔ)上,對實際控制人權(quán)利大于責(zé)任具有充分預(yù)期,甚至安排了相應(yīng)防范和救濟措施下作出的。因而,相對于事后的加強公司控制的實現(xiàn)方式,建立在透明規(guī)則和理性預(yù)期上的事前的控制權(quán)安排一致行動協(xié)議,道德風(fēng)險傾向相對較小。
因而,從資本市場進入分散股權(quán)時代的現(xiàn)實制度背景出發(fā),或許我們不應(yīng)太多目光投向一致行動協(xié)議“現(xiàn)金流權(quán)與控制權(quán)的分離”帶來的負外部性,而更多關(guān)注其信號傳遞以及鼓勵創(chuàng)業(yè)團隊的人力資本投資的積極作用。
資本市場的“專利制度”
我們有以下政策建議供參考。
其一,公司在IPO前簽訂一致行動協(xié)議將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在成為公眾公司后,一些機構(gòu)通過二級市場染指公司控制權(quán),甚至以極端的“野蠻人”方式入侵的可能性。
其二,在信息不對稱嚴重的高科技企業(yè)中,自發(fā)簽訂的一致行動協(xié)議可能成為具有豐富管理經(jīng)驗、專注業(yè)務(wù)模式創(chuàng)新的創(chuàng)業(yè)團隊投入更多人力資本的標志。
其三,對于看似同樣導(dǎo)致現(xiàn)金流權(quán)與控制權(quán)實現(xiàn)分離的控制權(quán)安排,與事后的控制權(quán)安排相比,事前控制權(quán)安排的道德風(fēng)險傾向更小。“事前”還是“事后”由此成為資本市場與監(jiān)管機構(gòu)對控制權(quán)安排可能引發(fā)的道德風(fēng)險程度識別的潛在標準之一。
其四,創(chuàng)業(yè)團隊簽署一致行動協(xié)議看起來為股東自由進入退出設(shè)置門檻,但卻為高科技企業(yè)成功化解種種困境提供了可行的解決方案,一致行動協(xié)議由此成為“資本市場的專利制度”。
李邈對本文的寫作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