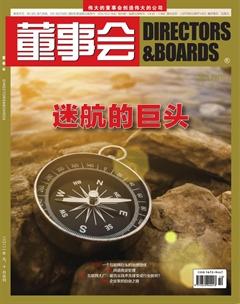董監(jiān)高《聲明及承諾》,還有簽的必要嗎?
林益
2020年8月,因全新好控股股東及實際控制人,未能在成為公司控股股東或?qū)嶋H控制人后的一個月內(nèi),完成《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聲明及承諾書》的簽署和備案工作,深交所認(rèn)為全新好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違反了《主板上市公司規(guī)范運作指引》第4.2.5條的規(guī)定,對其下發(fā)監(jiān)管函。
實踐中,上市公司對于提交《上市公司董事(監(jiān)事、高級管理人員)、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聲明及承諾書》(以下簡稱《聲明及承諾》)普遍不感冒,也極少有投資者關(guān)心《聲明及承諾》的內(nèi)容,但《聲明及承諾》填報違規(guī)的案例仍時有發(fā)生,那到底《聲明及承諾》的制度設(shè)計初衷是什么、有何功能、是否還有存在必要?
主要內(nèi)容規(guī)定
滬深交易所的上市規(guī)則均要求上市公司董事、監(jiān)事及高級管理人員、控股股東等主體在公司首發(fā)上市前或初次任職后向交易所提交《聲明及承諾》,且多在各自上市規(guī)則中列專節(jié)予以規(guī)定。雖然板塊不同、簽署主體不同,滬深交易所《聲明及承諾》均分為聲明部分和承諾部分,主要內(nèi)容及相關(guān)規(guī)定大同小異。
一是聲明部分以簽署人陳述個人主要信息為主要內(nèi)容。根據(jù)《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guī)則》(以下簡稱《主板上市規(guī)則》)第3.1.2條規(guī)定,董事、監(jiān)事、高級管理人員(以下統(tǒng)稱董監(jiān)高)應(yīng)當(dāng)在《聲明及承諾》中聲明持股情況、違規(guī)被查處情況、參加證券業(yè)務(wù)培訓(xùn)情況、工作經(jīng)歷等個人信息。在《聲明及承諾》格式文本中聲明實際包括以下具體內(nèi)容:1.聲明人的基本信息,主要包括姓名、聯(lián)系地址、國籍、身份證明號碼、工作經(jīng)歷等個人基本信息;2.聲明人及其近親屬的利益情況,包括兼職情況、本人及其近親屬持股情況等;3.與任職資格有關(guān)的信息,是否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條規(guī)定的禁止任職情形,是否涉及影響任職的訴訟程序、行政處罰、紀(jì)律處分或其他情形等;4.責(zé)任認(rèn)知的聲明,主要包括是否已知悉將被追究刑事責(zé)任的情形、虛假記載的后果。
二是承諾部分以簽署人承諾遵守各項規(guī)則并接受交易所監(jiān)管為主要內(nèi)容。根據(jù)《深交所股票上市規(guī)則》(以下簡稱《創(chuàng)業(yè)板上市規(guī)則》)第3.1.5條的規(guī)定,上市公司董監(jiān)高應(yīng)當(dāng)履行多項職責(zé)并在《聲明及承諾》中作出承諾,例如遵守并促使上市公司遵守本規(guī)則和本所其他相關(guān)規(guī)定,接受本所監(jiān)管、監(jiān)事應(yīng)當(dāng)承諾監(jiān)督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遵守其承諾等。在《聲明及承諾》格式文本中承諾實際包括以下具體內(nèi)容:1.遵守規(guī)則的承諾,主要內(nèi)容是承諾遵守并促使公司遵守法律、法規(guī)、證監(jiān)會交易所規(guī)則和公司章程;2.接受監(jiān)管的承諾,主要內(nèi)容是承諾按照交易所要求履行各項義務(wù),如如實回答問題、按要求出席會議、按要求參加培訓(xùn);3.承擔(dān)責(zé)任的承諾,即如違反承諾,愿意承擔(dān)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責(zé)任;4.訴訟管轄權(quán)承諾,承諾與交易所的相關(guān)訴訟糾紛,由交易所所在地法院管轄。

制度設(shè)計初衷
從境外實踐來看,紐約證券交易所、臺灣交易所、香港聯(lián)交所等主要交易所要求上市公司或董監(jiān)高等主體提交聲明或確認(rèn)資料。初步推斷,滬深交易所《聲明及承諾》更多是借鑒聯(lián)交所的相關(guān)做法實踐。一是聯(lián)交所的實踐更早,2001年,滬深交易所修訂股票上市規(guī)則,新增董事、監(jiān)事應(yīng)當(dāng)簽署聲明及承諾的相關(guān)規(guī)定。而根據(jù)可查的資料顯示,早在1999年前,聯(lián)交所即已根據(jù)董事提交的《聲明及承諾》對相關(guān)董事予以紀(jì)律處分。二是體例一致,均分為聲明及承諾兩個相互獨立的部分。三是內(nèi)容相似,聲明均是與聲明人任職適格性相關(guān)的信息,承諾也主要為遵守規(guī)則、接受監(jiān)管的承諾。四是形式相近,均需本人簽署,并由律師對聲明及承諾的內(nèi)容進(jìn)行解釋、見證。從聯(lián)交所的規(guī)定來看,聲明及承諾發(fā)揮著資格審查、監(jiān)管依據(jù)的功能。
一是發(fā)揮資格審查的功能。《聯(lián)交所上市規(guī)則》第3.09條規(guī)定,上市發(fā)行人的董事,必須令本交易所確信其具備適宜擔(dān)任上市發(fā)行人董事的個性、經(jīng)驗及品格,并證明其具備足夠的才干勝任該職務(wù)。交易所可能會要求上市發(fā)行人進(jìn)一步提供有關(guān)董事或擬擔(dān)任董事者的背景、經(jīng)驗、其他業(yè)務(wù)利益或個性的資料。可見,聯(lián)交所對董事的任職具有實質(zhì)審查的權(quán)力。此外,在聯(lián)交所在《聲明及承諾》要求聲明人聲明“本人明白,聯(lián)交所或會倚賴上述資料評估比本人是否適合出任發(fā)行人董事”,亦是證明。為落實聯(lián)交所對董事資格的審查職責(zé),《聯(lián)交所上市規(guī)則》規(guī)定上市公司的新任董事(監(jiān)事)在獲得委任后,在切實可行范圍內(nèi)盡快簽署并提交《聲明及承諾》。
二是實施自律監(jiān)管的依據(jù)。聯(lián)交所上市規(guī)則雖未明確指出,聯(lián)交所根據(jù)《聲明及承諾》對董監(jiān)事等承諾主體進(jìn)行監(jiān)管。但是根據(jù)聯(lián)交所做出的紀(jì)律處分決定,聯(lián)交所將承諾視為重要的監(jiān)管依據(jù)。在具體實踐中存在兩類情形。一是,同時違反上市規(guī)則等相關(guān)規(guī)則及承諾。2019年5月,魏橋紡織因關(guān)聯(lián)交易未履行決策程序、未按期披露財務(wù)報告等違規(guī),被聯(lián)交所公開譴責(zé),同時,公司董事長張紅霞、董事兼財務(wù)總監(jiān)趙素及董事兼董事會秘書張敬雷等違反《上市規(guī)則》關(guān)于董事“避免實際及潛在的利益和職務(wù)沖突”“ 以應(yīng)有的技能、謹(jǐn)慎和勤勉行事”的規(guī)定,也違反了向聯(lián)交所作出的《董事的聲明及承諾》所載責(zé)任,未有盡力遵守《上市規(guī)則》,亦未有竭力促使該公司遵守《上市規(guī)則》。二是,僅違反承諾。2018年12月,因辰興發(fā)展未披露購買理財?shù)戎匾畔ⅲ宦?lián)交所公開譴責(zé)。同時,聯(lián)交所認(rèn)為,公司董事長等四名董事違反各自向聯(lián)交所作出的《董事的聲明及承諾》所載的責(zé)任,未能盡力促使該公司遵守《上市規(guī)則》的條文。又如,因同仁資源前執(zhí)行董事Gaankhuyag不配合聯(lián)交所的調(diào)查,違反其向聯(lián)交所作出的《董事的聲明及承諾》所載的責(zé)任,聯(lián)交所對其予以公開譴責(zé)。
作用并不突出
從滬深交易所目前的監(jiān)管實踐來看,《聲明及承諾》的作用并不突出。
首先,滬深交易所對董監(jiān)高任職的監(jiān)管更多為信息披露監(jiān)管,聲明的資格審查功能不突出。雖然,滬深交易所在相關(guān)規(guī)則中規(guī)定了董監(jiān)高候選人不得存在的禁止性情形。例如深交所《上市公司規(guī)范運作指引》第3.2.3條規(guī)定,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條規(guī)定的情形之一、被證監(jiān)會采取市場禁入措施等情況的,不得被提名為董監(jiān)高候選人。但實踐中,滬深交易所對董監(jiān)高等主體任職資格的監(jiān)管,僅為一般性的信息披露事項進(jìn)行監(jiān)管,均未明確將通過《聲明及承諾》對簽署人的任職資格進(jìn)行審核。一是,根據(jù)滬深交易所公開的審核、登記事項辦理指南來看,除了獨立董事資格備案外,滬深交易所均未將董監(jiān)高的《聲明及承諾》的報備事項視為交易所的審核及登記事項;二是,從時限要求來看,《聲明及承諾》不具有一般審核所具有的及時性要求,滬深交易所僅要求簽署人在任命后的一個月內(nèi)報備《聲明及承諾》,報備周期較長,可見滬深交易所并無審查《聲明及承諾》對相關(guān)簽署人任職資格的意圖。
其次,滬深交易所作為證券法規(guī)定的自律監(jiān)管組織,聲明的監(jiān)管依據(jù)功能同樣不突出。有學(xué)者認(rèn)為,證券交易所對上市公司董監(jiān)高的懲戒基礎(chǔ)是相關(guān)聲明與承諾……其性質(zhì)相當(dāng)于合同,約束交易所與上市公司董事雙方權(quán)利義務(wù),一旦出現(xiàn)違法違規(guī),交易所可依此作出懲戒。在滬深交易所各板塊的上市規(guī)則中,也明確將聲明與承諾作為監(jiān)管依據(jù)之一。例如,《主板上市規(guī)則》第1.5條的規(guī)定,本所依據(jù)法律……本規(guī)則及本所其他規(guī)定、上市協(xié)議、聲明與承諾,對發(fā)行人、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監(jiān)事、高級管理人員、股東……證券服務(wù)機構(gòu)及其相關(guān)人員進(jìn)行監(jiān)管。但是在實踐中,相對于上交所在其作出的紀(jì)律處分決定書中普遍援引《聲明及承諾》不同,深交所在其多數(shù)處分決定中則未作引用,也極少發(fā)現(xiàn)有僅因違反《聲明及承諾》而被監(jiān)管的案例。滬深交易所是否援引承諾作為紀(jì)律處分依據(jù)方面存在的差異,一定程度說明承諾僅作為監(jiān)管依據(jù)之一。在監(jiān)管規(guī)則完備的情況下,《聲明及承諾》的內(nèi)容在相關(guān)監(jiān)管規(guī)則中均可找到依據(jù),是否援引《聲明及承諾》并不實質(zhì)影響監(jiān)管權(quán)力的行使。
具有必要性
如上文所分析,《聲明及承諾》在資格審查、監(jiān)管依據(jù)方面的作用并不突出。那么除了路徑依賴外,《聲明及承諾》是否仍有其必要性?
筆者認(rèn)為,《聲明及承諾》的必要性,一是體現(xiàn)在其具有一定的“宣誓”功能。《聲明及承諾》的核心內(nèi)容在于簽署人明確其擔(dān)任董監(jiān)高等主體的適格性,并承諾知悉并遵守規(guī)則、接受監(jiān)管。通過本人親自簽署、律師解釋文件內(nèi)容并見證,一方面能提醒簽署人審慎填報相關(guān)個人信息,幫助簽署人更好地理解自己的責(zé)任;另一方面這種宣誓性的書面承諾,增加了其任職的儀式感,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簽署人更為盡責(zé)。這一做法有著充分的心理學(xué)基礎(chǔ)。心理學(xué)理論認(rèn)為我們的信念以及行為在不同時間、場景下趨向于保持一致的特點,其中聲明和承諾是一類基本的運用。在法律已經(jīng)有所規(guī)定的同時增加聲明及承諾,一定程度可增加對行為的約束,而書寫下來的承諾更能得到一致性,更容易被遵守。
二是,可作為交易所收取懲罰性違約金的監(jiān)管依據(jù)。2017年10月,中國證監(jiān)會修訂《證券交易所管理辦法》,規(guī)定“發(fā)行人、證券上市交易公司及相關(guān)信息披露義務(wù)人等出現(xiàn)違法違規(guī)行為的,證券交易所可以按照章程、協(xié)議以及業(yè)務(wù)規(guī)則的規(guī)定,采取……收取懲罰性違約金……等自律監(jiān)管措施或者紀(jì)律處分”。對此,滬深交易所分別修改了交易所章程、上市協(xié)議及上市規(guī)則,明確交易所可對上市公司、上市公司董監(jiān)高等主體收取懲罰性違約金。其中,上交所于2018年更新《上市協(xié)議書》,約定上市公司及其相關(guān)方違反上市協(xié)議或者向交易所作出的聲明與承諾,上交所有權(quán)根據(jù)其業(yè)務(wù)規(guī)則規(guī)定的情形、標(biāo)準(zhǔn)和程序等,對上市公司及其相關(guān)方收取懲罰性違約金。按規(guī)定交易所可根據(jù)業(yè)務(wù)規(guī)則收取懲罰性違約金,但考慮到懲罰性違約金更多具有約定性質(zhì),具有雙向性,難以覆蓋第三人。因此,一方面,僅在交易所的規(guī)則層面予以規(guī)定,可能有違“違約金”違約的本意;另一方面,嚴(yán)格意義上說,通過上市協(xié)議是否能夠覆蓋董監(jiān)高等非協(xié)議相對方亦有疑問。如采取承諾書的方式,更接近協(xié)議性質(zhì),更符合懲罰性違約金的“約”本質(zhì)。
因此,從前述兩點出發(fā),《聲明及承諾》有兩項完善之處。一是縮短提交時間,可要求相關(guān)主體在任命后的五日內(nèi)提交。《聲明及承諾》的相關(guān)內(nèi)容,在董監(jiān)高任職前,上市公司即應(yīng)當(dāng)予以核實、本人即應(yīng)當(dāng)予以確認(rèn),一個月的提交時間必要性不足。二是將接受交易所包括收取懲罰性違約金在內(nèi)的紀(jì)律處分措施作為明確的承諾事項。通過這種明確約定、本人確認(rèn)的方式,形成懲罰性違約金的相對性,提高威懾力,督促相關(guān)主體能夠更審慎地履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