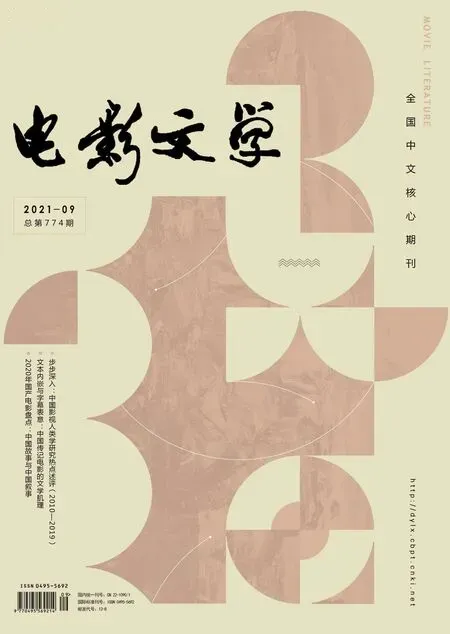用桌面屏幕觀照計算機時代:桌面電影的形式溯源與美學風格
2021-11-15 00:06:35王婷婷北京電影學院北京00088河北大學河北保定07000
電影文學
2021年9期
關鍵詞:計算機
王 薈 王婷婷(.北京電影學院,北京 00088;.河北大學,河北 保定 07000)
桌面電影這一概念最早由俄羅斯導演提莫·貝克曼貝托夫(Timur Bekmahambetov)提出,他稱其為“屏幕電影(Screenlife Movie)”,是將敘事“完全在電腦或手機的屏幕展開”的電影,即用此種方式“展示當代網絡用戶在現實生活中通過網絡所發生的故事”。其深層體驗是借由操作視窗展現在電子設備桌面內容,與大眾日常經驗產生“擬真感”同構,從而進行非線性組合的敘事形式(或風格)。桌面電影在發展過程中,逐漸特指某計算機操作系統的視窗(計算機實體邊框和屏幕內矩形邊框)所呈現出的各種類型敘事形式,其增多了畫面中電影創作者模擬用戶操作從而產生人為干預,制造出更多的特效交互場景。與手機電影所特有的豎屏交互形式產生了明顯分流,固化為“電腦屏幕電影(screen film)”“電腦桌面電影(desktop film)”以及“電腦視窗電影(computer sreen film)”等,并在項目開發和創作實踐中不斷深化和尋找桌面電影的獨特視聽語言美學,孫紹誼將之歸類于超現代電影(hypermoderncinema)。其他藝術形式也向桌面電影借鑒經驗,2020年,在多國都展示出積極的探索,同時嘗試已經拓展到電影、劇集和短片等不同體量,如中國導演尹宇豪自編自導自演的30分鐘短片《君羊·陰網懼世》,以及來自日本的2集短劇《遠程遇害》(リモートで殺される),56分鐘的美國恐怖驚悚電影《奪魂連線》(The
Host
)。BAZELEVS影視公司(提莫·貝克曼貝托夫創立)為首的影視公司仍對桌面電影有數部開發計劃。隨著“桌面電影”的作品越來越多,開始獲得越來越多觀眾的關注,也為越來越多的觀眾所熟悉與接受。……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小學科學(學生版)(2021年7期)2021-07-28 06:44:42
趣味(數學)(2020年9期)2020-06-09 05:35:08
鐵道通信信號(2020年12期)2020-03-29 06:21:58
科技傳播(2019年22期)2020-01-14 03:06:34
科技傳播(2019年22期)2020-01-14 03:06:30
消費導刊(2017年20期)2018-01-03 06:26:40
電子制作(2017年14期)2017-12-18 07:08:10
辦公自動化(2016年18期)2016-08-20 12:50:22
鐵道通信信號(2016年11期)2016-06-01 12:11:32
鐵道通信信號(2016年3期)2016-06-01 12: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