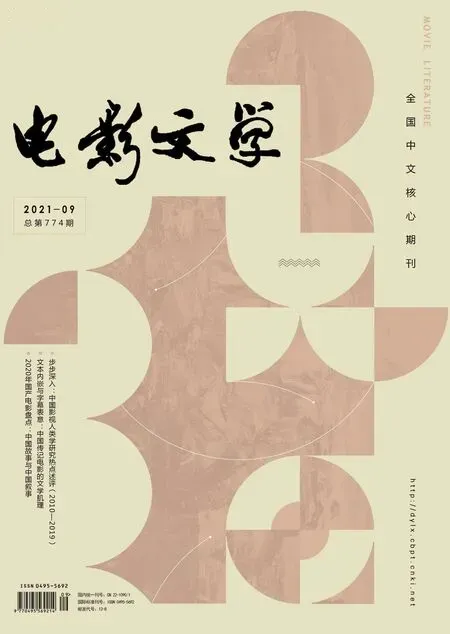中國形象:跨文化改編視角下的新移民電影
2021-11-15 00:06:35馬阿婷哈爾濱師范大學黑龍江哈爾濱150000
電影文學
2021年9期
關鍵詞:文化
馬阿婷(哈爾濱師范大學,黑龍江 哈爾濱 150000)
隨著中國“一帶一路”政策的發展,跨文化傳播對于中國形象的建構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在跨文化傳播路徑當中,電影的作用日益凸顯,因為隨著人們日常生活水平的提高,自媒體時代的到來,使得人們對視覺的效果有了更高的追求,電影的震撼效果與高大上的觀影體驗無疑是提升生活品質的絕佳選擇。出于對觀眾心理的分析與觀眾口味的迎合,電影題材從家庭倫理片、好萊塢大片、紀錄片、都市言情片到系列動畫片、系列賀歲片等類型電影占據了各大影院的各個檔期。而近年來,新移民文學作品改編為電影越來越受到各大導演的青睞,筆者以北美華裔女性作家嚴歌苓創作的《金陵十三釵》《陸犯焉識》《芳華》《媽閣是座城》等文學作品為例,深入分析其成功改編為電影腳本,并取得了令人矚目票房收益的原因不難發現,這些文學作品擁有了大量的讀者粉絲,文字的力量使得讀者懷著獵奇的心理想一探其視覺上的奧秘,進而讀者演化為觀影者,而作家也隨之成為編劇。雖然身份的轉變憑借一張電影票就可以完成,但文字轉化為鏡像確需一定的功力。
一、文化折扣:光與影的留白
以嚴歌苓為代表的新移民文學已經形成具有一定基礎的文學產業鏈,形成了一定的品牌規模,由于其文字充滿畫面感,飽滿的色彩似乎在銀幕上呼之欲出,文學作品受到許多知名導演的青睞,獲得不錯票房業績的改編電影同時也反哺文學作品的流傳。……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中國德育(2022年12期)2022-08-22 06:16:18
湖北教育·綜合資訊(2022年4期)2022-05-06 22:54:06
金橋(2022年2期)2022-03-02 05:42:50
金橋(2022年1期)2022-02-12 01:37:04
英語文摘(2019年1期)2019-03-21 07:44:16
小天使·一年級語數英綜合(2018年9期)2018-10-16 06:30:16
西部大開發(2017年8期)2017-06-26 03:16:12
西部大開發(2017年8期)2017-06-26 03:15:50
人民中國(日文版)(2015年10期)2015-04-16 03:53:52
人民中國(日文版)(2015年9期)2015-03-20 15:0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