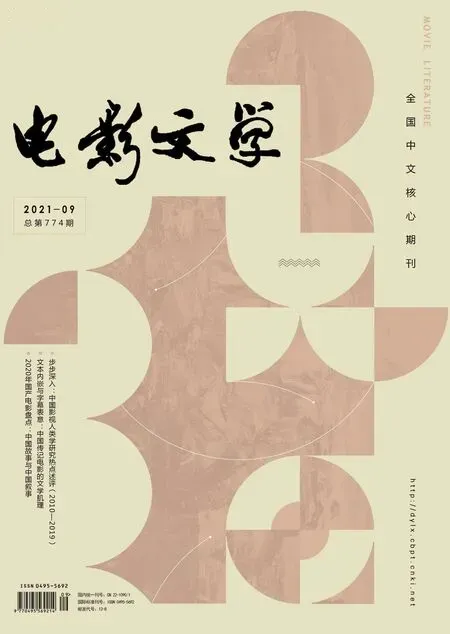論網絡電影的“五小”審美
2021-11-15 00:06:35江蘇師范大學傳媒與影視學院江蘇徐州221000
電影文學
2021年9期
董 鑫 陳 巖(江蘇師范大學傳媒與影視學院,江蘇 徐州 221000)
網絡電影通常指網絡自制,并在網絡上發行、放映的電影,是電影視聽藝術與網絡新媒介的自然碰撞與融合。基于網生屬性,網絡電影引發了非常大的爭議,關于其是否是電影的討論如今仍然此起彼伏。近年來,網絡電影發展迅速,并在多種場合與院線電影產生沖突,涉及電影未來的話語權爭奪。普遍的看法認為,網絡電影的美學形態與院線電影迥異。“網絡電影”召喚了一種新的觀影經驗,這種經驗與院線電影的欣賞機制大不相同。同時,作為一種媒介,網絡電影生產的內容往往以文學、電影、電視等傳統媒介內容作為前文本。結合網絡電影自誕生以來的具體作品,低級、模仿/抄襲、土味等成為其存在的一個折射,蹭IP、同質化現象不斷出現,助力大眾形成了對網絡電影的某種偏見。
而在對網絡電影發展與美學特性的考察中,筆者認為其形成了有別于院線電影的審美特征。從最初的基于網生屬性的對院線電影的“寄生”,到一種雜糅進創作意識的主觀改造。它的“小”“丑”“土”景觀,從一種視覺“吸睛”蛻變為自我標識。這種“小”化的審美改造,從整個網絡電影發展史來看,趨向性越來越強,越來越具備自發性和創造性,并影響到其他媒介的內容呈現。它依托于網絡媒介,將傳統審美中的宏大、上鏡頭、崇高改造為草根的狂歡。盡管根植于大眾文化的土壤,其中仍凸顯出寶貴的藝術思索。它不再單單是對傳統影像的變相模仿,而是摻雜了自我意識的藝術創作。……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