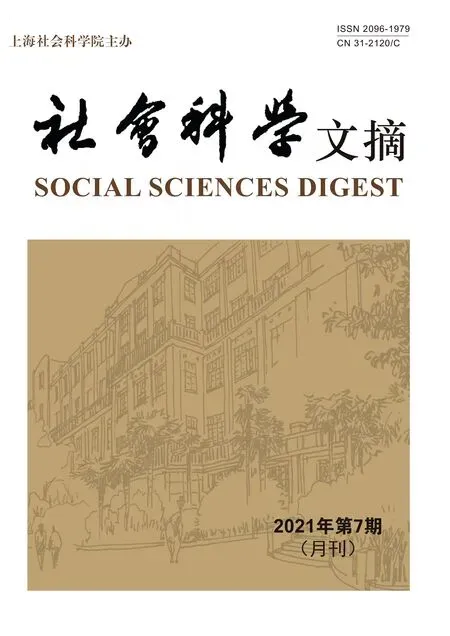能否將中國哲學看作一種“地方性知識”?
——與陳少明先生商榷
文/何剛剛
近年來,格爾茲提出的“地方性知識”概念被應用于本土的社會學與人類學研究中,均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也有一些學者試圖從“地方性知識”的視域去審視中國哲學,陳少明先生的《中國哲學:通向世界的“地方性知識”》一文就屬于這類嘗試的代表之作。然而由于其對格爾茲“地方性知識”理論的誤解,造成此文的觀點存在一定的問題。本文擬在此文的基礎上,對于“能否將中國哲學作為一種‘地方性知識’”這一問題進行討論。
兩種“地方性知識”概念的混淆
一般來說,學界認為存在兩種“地方性知識”(local knowledge),一種是由人類學家格爾茲提出的“地方性知識”,一種是由哲學家勞斯提出的“地方性知識”。格爾茲的“地方性知識”是一種人類學視角,主要是通過對一些邊緣文化的研究得出了這個概念。這種“地方性知識”屬于闡釋人類學中“后殖民與后現代”話語,不屬于認識論部分。而哲學家勞斯提出的“地方性知識”則是一個哲學概念,其地方性是指在知識生成和辯護中所形成的特定的實踐情境。
兩種“地方性知識”都強調地方性與情境性,但是實際存在很大的不同。格爾茲的“情境性”總是與地域性、時空性聯系在一起,它是一種地域情境。而勞斯的“情境”是“實踐情境”。可以說,兩種“地方性知識”中“情境”最大的不同在于,格爾茲認為是地方性導致了情境性,而勞斯認為恰恰是因為情境性才有了地方性。因此,雖然它們兩者都叫做“地方性知識”,但其實有很大的不同。而《中國哲學:通向世界的“地方性知識”》(以下簡稱《知識》)一文常常陷入兩種“地方性知識”的概念混淆之中。
《知識》一文在開始時就說其使用的是格爾茲的“地方性知識”概念,對于“地方性知識”的理解也都基本偏向于格爾茲的“地方性知識”。如文中說,“因為所有的知識都是在特定時空(即‘地方’)中創(chuàng)造的”,這里的“地方性知識”偏向于格爾茲的“地方性知識”,因為格爾茲的“地方性知識”就是在強調特定的時空關系。然而,后文對于“地方性知識”的理解則偏向于勞斯的“地方性知識”。如文中說:“對之作以‘禮’為中心的解讀。‘仁’之所以含義模糊,是因為它泛化為對人事行為的態(tài)度表達。而這些行為總與特定的情景相關,必須在具體語境中理解。”這種對于具體實踐場域的強調其實正是勞斯的“地方性知識”的特色之所在。勞斯之所以提出“地方性知識”,是因為在他看來傳統(tǒng)的知識都帶有理論優(yōu)位的特點,而“理論性理解是非視角性的,因而在時空的所有位置上理論都是等同的。它從特定的生活情境中抽離了出來”。因此,可以看出《知識》一文借用的概念是格爾茲的“地方性知識”,而在對“地方性知識”的理解與展開層面則已經成了勞斯的“地方性知識”。
對“地方性知識”與普遍性知識關系的誤解
(一)普遍性知識的預設
《知識》一文對于普遍性與地方性的理解仍然是傳統(tǒng)的二元對立式的。因此它在強調中國哲學是“地方性知識”的時候,就需要預設一種與之相對應的普遍性知識作為參照。然而“地方性知識”并不需要去預設某種普遍性的東西,因為不論是哪一種知識,在人類學家那里都只有發(fā)生學的意味。“格爾茲要借助對文化他者的認識反過來觀照西方自己的文化和社會,從而意識到過去被奉為圭臬的西方知識系統(tǒng)原來也是人為‘建構’出來的。”格爾茲的“地方性知識”不會預設普遍性,“地方性知識”也不會與普遍性知識相對應。
而《知識》一文認為早期的西方哲學和早期的中國哲學都是一種“地方性知識”,后來逐漸走向普遍性知識。然而這種對于普遍性知識的預設恰恰違背了“地方性知識”建立的初衷,因為“地方性知識”所要做的事正是消解近代以來興起的普遍性的觀念。格爾茲說:“承認他人也具有和我們一樣的本性,是一種最起碼的態(tài)度。能夠將我們自己與地方性的例子都作為個案來理解,作為世界中的一個世界來看待,這將會是難能可貴的成就。”可見“地方性知識”本身不需要預設普遍性知識,它最終的目的是互相理解、互相溝通。
總之,《知識》一文對于普遍性知識的預設并不符合格爾茲“地方性知識”的邏輯。而之所以會預設普遍性知識,主要是因為作者企圖將“地方性知識”與普遍性知識對應起來,對“地方性知識”做普遍化的處理,這也是他對“地方性知識”與普遍性知識理解的誤區(qū)。
(二)“地方性知識”與普遍性知識不構成對應關系
《知識》一文中對普遍性知識的預設,其目的是將“地方性知識”與普遍性知識對應起來。如文中所說:“以地方性知識的眼光看待古典的哲學觀念的時候,不能忘記,哲學最終不會以‘地方性知識’為滿足。”這就說明了作者理解的“地方性知識”并不是盡頭,因此他說:“中國哲學后期已經超越局部經驗而具有趨向普遍性的含義。”可以看出在《知識》一文中處處充斥著地方性與普遍性的互參。然而,格爾茲的“地方性”知識所對應的其實不是普遍知識,而是西方知識。西方知識并不等于普遍性知識。格爾茲曾明確說過:“我的作品中絕大部分其實都致力于證明‘伊斯蘭’‘印度教’和廣義的‘馬來西亞’可以說根本不是隨時間、空間與人群而變異的一大塊同質性的實體,將他們具體化這種模樣,實際上一向是‘西方’用來規(guī)避以及清楚了解他們和看待他們的一個主要設計。”格爾茲所提出的“地方性知識”主要的參照物就是西方知識,但是西方知識不等于普遍性知識。事實上,格爾茲的“地方性知識”概念源于“ethno-”有關的知識考查或者和“ethno sciences”有關的知識概念,其在西方的詞匯“sciences”前加上了一個前綴,以表示西方沒有的知識。因此“地方性知識”是對于西方知識的補充。
另外,“地方性知識”不僅不與普遍性知識相對應,也不追求普遍性知識,甚至“地方性知識”也無法追求普遍性知識。格爾茲的“地方性知識”沒有普遍性的訴求。格爾茲說:“雖然‘一般性理論’仍在我們中有其信眾,但其實質已逐漸空泛,這種企望已漸被視為虛妄。”然而《知識》一文處處在追求知識的普遍性。而在后文更是直接鮮明地強調中國哲學的地方性,實際上是為了將其通向普遍性。然而,格爾茲的“地方性知識”從來沒有要去上升到普遍性的理論追求。格爾茲“地方性知識”的提出是為了“去中心主義”,而不是為了讓自己成為中心話語。而且格爾茲所提出的“地方性知識”在許多學者看來最大的問題是:“它始終不是一個入住普遍性知識殿堂的類,而是一個只能居住于小茅屋的類。”格爾茲所提出的“地方性知識”無法普遍化,“地方性知識”是作為普遍性知識的補充而存在的。格爾茲不斷地強調:“人類學需要借助本土認知結構框架來認識本土社會現象,厘清事實,追根究源,而不是用事先預設的因果關系,一廂情愿地推導結論,以為萬變不離其宗,舉一可以反三。”格爾茲的“地方性知識”一開始就是為了展開多元性,通過“濃描”來展現地方性的知識形態(tài)。因此格爾茲并不追求普遍性,也拒絕在普遍與特殊之間選擇立場。格爾茲的“地方性知識”的主要任務在于通過對“地方性知識”的“濃描”,處理抽象知識與具體知識之間的關系。“地方性知識”之所以重要,就是因為任何制度文化、任何語言系統(tǒng),都不能窮盡真理,都不能直面上帝,只有從各個地方知識內部去展開這種知識結構,才能找到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并在此基礎上發(fā)現“重疊共識”,從而避免把普遍性與特殊性對立起來。
《知識》一文之所以會出現將“地方性知識”通達到普遍性知識的做法,主要是因為對普遍性有某種執(zhí)念。然而,將近代西方哲學預設為普遍性知識,而將中國哲學說成是“地方性知識”,不僅在哲學史層面太過牽強,也與格爾茲的“地方性知識”并不相符。而造成這種問題最核心的原因在于,《知識》一文對于特殊性與普遍性之間的關系的理解依舊沒有突破傳統(tǒng)的范式。
(三)特殊性與普遍性處于溝通融合之中
“地方性知識”與普遍性知識之間的關系歸根到底是特殊性與普遍性之間的關系。依照傳統(tǒng)的觀點來看,普遍性與特殊性是對立統(tǒng)一的。然而,特殊性與普遍性其實是處在溝通融合之中的。“地方性知識”不是要在特殊性中去尋求普遍性,而是希望所有特殊性都能與其他特殊性之間實現溝通與交流。所有的“地方性知識”都向其他的“地方性知識”敞開著,能夠通過對話實現交流與溝通,達到對于不同文化的理解。正如格爾茲所說,讓擁有不同知識背景的人類學家深切理解彼此之間的認識差異,接受“地方性知識”的多樣化,從交流的目的來看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達成某種一致,而是使不同的認識結果通過充分交鋒與彼此校正得以更加豐富。因此,最重要的是不同文化之間的溝通與理解,而不是要去通過地方性追求普遍性。
中國哲學作為“地方性知識”存在的問題
(一)“地方性知識”應用的限度
“地方性知識”最早是作為一個人類學概念而提出的,因此這個概念的運用必然會有它的限度。人類學與哲學的一個最大不同在于人類學可以對任何的“地方性知識”進行所謂的“濃描”與展開,分析知識內部的細節(jié)。而哲學知識本身就是抽象的。如果按照人類學中的“地方性知識”理論的視域分析中國哲學,將其方法論貫徹到底,對中國哲學中的概念、語詞都進行徹底的分析闡述,最終將導致中國哲學的自我解構。
“中國哲學”本身就是一個帶有抽象性的概念,它內在包含著儒家、道家等理論。如果強調中國哲學的地方性,而忽略中國哲學內部其他理論的地方性,則會陷入邏輯矛盾。作者似乎也意識到這一點,因此他說:“中國哲學是‘地方性知識’,依然是有風險的,因為所有的知識都是在特定時空(即‘地方’)中創(chuàng)造的。”然而實際上這種限定并不能規(guī)避問題,因為“中國哲學”這個概念本身就是一個帶有抽象性的概念。儒家哲學中又可分為各個不同的理論形態(tài),那么如此細分下去,最終出現的是一個個類似于維特根斯坦所說的“原子命題”。事實上格爾茲正是受到維特根斯坦語言觀的重大影響,他所追求的正是維特根斯坦的“繩索共同體”,利用多股重疊交叉、頂針續(xù)麻,最終擰成一股繩。但是這種做法將導致中國哲學的自我解構,中國哲學將成為人類學或者社會學,不再具有任何抽象的形而上學品格。
人類學家強調知識的地方性,這在很大程度上與人類學學科的經驗性有關。哲學是從“普遍”的角度來思考“特殊”的。“哲學的知識是出自概念的知識,它只在普遍中考慮特殊。哲學之所以與數學、自然科學的思維方向相反,這是由它的非經驗的性質決定的。”因此,將人類學的某些概念推向哲學有很大的風險。其實,學界早已有學者意識到將中國哲學推向地方性研究存在的問題。陳來曾說:“有的學者借用人類學的觀念,把儒學描述為從曲阜的‘地方性知識’到儒學的三期發(fā)展。雖然,這種提法仍然承認孔子思想是有普遍意義的‘地方性知識’,但把孔子或孔孟的思想稱為‘地方性知識’,這種說法在嚴格的意義上看并不恰當。”因此,將中國哲學描述為一種“地方性知識”實際已經超出了“地方性知識”概念使用的限度。
(二)文化相對主義的風險
中國哲學作為一種“地方性知識”將極有可能走向文化相對主義。“地方性知識”獲得的前提就是傳統(tǒng)心態(tài)的轉變,接受“文化相對主義”。格爾茲提出“地方性知識”的初衷是為了破除一種曾左右西方人類學界的“我族中心觀念”,其功績在于此種意識“向發(fā)源于西方而依然占據特權地位的全球均質化觀點、普同化價值觀、忽視或削弱文化多樣性的社會思潮及其對現實的界說提出挑戰(zhàn)”。然而“地方性知識”概念在不同領域的濫用,已經使得“地方性”成為一種為愚昧與落后辯護的手段。“它造成的風險在于‘地方性知識’將完全有可能成為主觀化的產品,而不是如格爾茲所設想的那種認識主體與認識客體高度滲透交融。”這種趨勢將導致文化相對主義的泛濫。
格爾茲很早就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他說:“‘地方性知識’是為了了解事物,更精確地了解事物的性質,而不是要利用相對主義去大談非洲人搞冥婚、澳洲人吃蠕蟲之類的事情,它是為了將自我覺知、自我理解與他人知識、他人感知和他人理解焊接起來,從而更準確地辨識我們是什么樣的人,我們周圍是什么樣的人。”中國哲學的發(fā)展不需要利用“地方性”追求所謂的特色,而是要與其他文化實現交流與溝通。
(三)阻礙中國哲學融入世界
將中國哲學看作一種“地方性知識”,在一定意義上阻礙了中國哲學融入世界。格爾茲的理論中一個極其重要的觀念是“文化持有者的內部視角”,強調從文化持有者的內部眼光來看問題。這是一種典型的局內人視角,即只有本地人才能更好地理解“地方性知識”。這意味著知識的掌握者在一定程度上有對知識解釋的優(yōu)先權。雖然格爾茲曾經一度為自己辯護過,他說:“提倡‘地方性知識’并不意味著研究對方,一味妥協(xié),把自己完全變成對方,而是要通過他們自己的‘眼鏡’來觀察他們的意義和心智。”然而格爾茲本人在研究巴厘人斗雞時,就親臨斗雞現場,以至于警察到來時,他和參賭的人群一起出逃。這個時候格爾茲成了真正的局內人。雖然可以說對于“地方性知識”的理解固然不需要完全成為他者,但是總是需要有一種局內人的視角。
然而,這種局內人視角是極其荒謬的。社會學家默頓曾經對“局內人信條”有過經典的批判。他說:“局內人信條是典型的對于知識的一種壟斷的策略,這些要求會無限地擴展到各種先賦地位。因此局內人信條雖然有部分的合理性,但是同時也有唯我論與自我中心主義的傾向。如果從社會結構或者文化屬性來看的話,局內人的很大問題在于他忽略了個人所擁有的并不是單一的地位,而是一個地位集,它們相互作用影響著個人的行為和它們的視角。因此它的取向是一種靜態(tài)的。”局內人視角忽略了動態(tài)的交流與溝通,僅僅以先賦身份對知識解釋權進行壟斷,在一定意義上阻礙了知識的交流。
如果說中國哲學是一種“地方性知識”,那就意味著中國人對于中國哲學具有優(yōu)先的解釋權。但是實際上在當今高度流動的現代社會,沒有哪個人是單純的局外人或者局內人。“在前現代社會,空間和地點總是一致的,因為對于大多數人來說,社會空間維度都是受到‘在場’支配的,但是在現代性條件下,時空逐漸分離,在場與不在場的各種關系都變得模糊起來。”在現代社會,很多人可能既是局內人,也是局外人。因此,這種將中國哲學歸結為“地方性知識”的說法無異于畫地為牢。中國哲學要走向世界,就必須擺脫這種思維方式,努力地與其他文明實現對話與交流,只有這樣,中國哲學才能更好地融入世界文明之中,煥發(fā)出生機與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