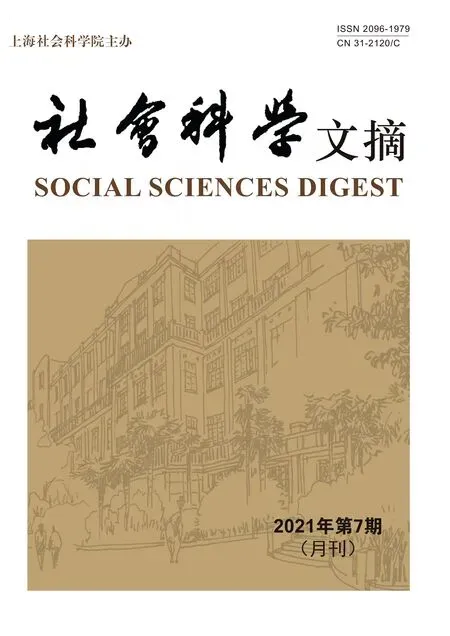自然美理論重建的三條路徑
文/胡友峰
興起于18世紀的自然美學在康德美學中達到巔峰,自黑格爾美學開始逐漸沉寂,到了20世紀初葉,美學已基本等同于藝術哲學。但是自然美理論缺席的美學是不完整的,現代美學對自然美的忽視的后果是以其自身局限性為代價的,因而,重建自然美理論成為當代美學建構的迫切需要。自20世紀中期以來,對自然美理論的重建從三條路徑展開。
環境美學:融合概念主義與非概念主義自然欣賞的美學路徑
在英美哲學的版圖中,自然美在當代美學領域的失落與當代西方分析美學的盛行緊密相關。在分析美學家看來,審美鑒賞涉及設計者的意圖、藝術史的觀念和藝術的批評實踐等,而這些在自然審美中是不可能找到的。
自然美的重建發端于羅納德·赫伯恩(Ronald Hepburn)在1966年發表的《當代美學及其對自然美的忽視》一文。針對分析美學對自然美的忽視,赫伯恩強調了自然美的開放性特征。在他看來,正是因為對自然的鑒賞不受設計者的意圖、藝術史傳統和藝術批評實踐的限制,才促使了一種開放的、介入的和創造性的自然美鑒賞模式的存在。而且,這種審美鑒賞模式應當由我們對自然世界的真實本質的認識所指引。赫伯恩的這篇文章開拓了自然美理論發展的兩種路徑,這兩種路徑被區分為“概念的”與“非概念的”(conceptual and non-conceptual)。簡而言之,前者是對傳統審美方式只關注感官與形式屬性的回應,因而強調科學知識等認知因素在自然審美中的主導作用,以艾倫·卡爾松(Allen Carlson)、霍姆斯·羅爾斯頓(Holmes Rolston III)、馬西婭·繆爾德·伊頓(Marcia Muelder Eaton)等美學家為代表;后者主要是對遠距離地靜觀這種審美方式的回應,因而強調參與、想象、情感等在自然審美中的主導作用,以阿諾德·伯林特(Arnold Berleant)、諾埃爾·卡羅爾(No?l Carroll)、斯坦·伽德洛維奇(Stan Godlovitch)等美學家為代表。
實際上,環境美學對自然美的復興始終伴隨著自然與藝術的區分以及對“究竟何為自然”的追問。即便非概念主義者看似強調審美主體的參與和創造,但這也要建立在“自然是環境的”這一基礎之上。各種不同的審美理論在“自然”究竟是什么這一問題上,就已開始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卡爾松認為“自然”是自然的且自然是環境的,因而反對將自然物看作藝術品似的孤立對象,主張將其放入與其密切相聯的整個環境中去欣賞。而伯林特的“自然”則是一個包括人與萬物在內的普遍聯系的統一體,自然之外無他物,因而主張不去區分人與自然的一元論的審美觀。摩爾(Ronald Moore)的“自然”則超越了環境自然,最大限度地涵蓋了整個非人造世界,因而不僅瀑布、日落是美的,桌子上的細木紋、手指上的指紋也是“自然”,也可以是美的。
對真與美的聯結是概念主義自然美學的主要方向。概念主義者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將自然當作自然而不是藝術來欣賞,并同時避免自然審美的膚淺與瑣碎。隨著當代自然美學的發展,“知識”早已溢出了自然科學知識的范圍而擴展至更廣泛的文化藝術領域,由此就引發了審美相關性的問題。在此基礎上,另外一個重要問題是自然審美與藝術審美的關系問題,隨著當代自然美學的發展,最初對自然審美與藝術審美的嚴格區分逐漸讓位于對二者間密切聯系的探討。摩爾認為,在實際的審美活動中,二者通常是相互作用的,我們可以正確利用在藝術審美中習得的聯想物、類比物等,我們只是在充分利用業已形成的感受力,而不是將藝術審美的方式或經驗強加于自然審美。唐納德·克勞福(Donald W.Crawford)德則更具體地為備受批評的“如畫”理論辯駁,他認為無論如何我們欣賞的都是自然的一個維度而不是別的什么。羅伯特·斯特克(Robert Stecker)則認為卡爾松所批判的“對象模式”與“景觀模式”是對審美對象完美恰當的欣賞,沒有任何不合理或不正確的地方。
對于非概念主義者而言,自然審美更具開放性,但非概念主義審美的開放性并非來自審美方式的開放性,而是源自非概念因素(情感、想象等)本身所具有的開放性與無限性。例如,赫伯恩、艾米麗·布雷迪(Emily Brady)與伽德洛維奇都強調想象的重要地位。尤其赫伯恩,不僅在《當代美學及其對自然美的忽視》一文中認為自然的無框性與開放性能夠帶來想象力的突然擴張。他還在《景觀與形而上學的想象》一文中,強調通過想象所洞悉的一些關于生命意義、人類狀況等形而上的真理。但是關鍵在于,想象的邊界在哪里。概念主義者就認為想象的虛構性可能會造成虛假的自然審美,因而非概念主義者同樣面臨著“審美相關性”的重要問題。伯林特就意識到這一點,當他將“感知”擴展為感官感知與個人經驗、信仰、價值觀等的統一體時,他也強調關鍵問題是如何忠實于當下的、直接的感知,而不去人為地編輯它們。
因此,無論是概念主義還是非概念主義,都具有某種片面性,要么偏重審美主體要么偏重審美客體。對此,有些學者試圖尋找一種融合的途徑。例如摩爾的“融合美學”(syncretic aesthetics)就綜合了自然審美與藝術審美以及科學與想象。羅爾斯頓在強調科學知識的重要性的同時,也指出知識并不能保證形成全面的審美經驗,欣賞者還需進入自然環境并“身體化”地去感知。謝麗爾·福斯特(Cheryl Foster)也認為兩種方式都是必要的,任何一種方式都無法單獨地獲得完整全面的自然審美體驗。因而,隨著當代自然美學的發展,從赫伯恩那里分流出來的概念主義與非概念主義又有合流之勢。
生態美學:走向自然整體審美的建構路徑
生態美學的興起和發展有賴于生態世界觀的形成。1866年,德國生物學家恩斯特·海克爾(Ernst Haeckel)首先提出了“生態學”這一概念。1935年,英國生態學家坦斯利(A.G.Tansley)明確提出了“生態系統”的概念。生態學的誕生意味著西方世界從對“人是萬物之靈長”的強調開始轉向了一種生態進化的視角。20世紀中后期,全球環境問題惡化進一步引起人們對生態的關注和思考,西方生態美學在這一背景下開始萌芽。在生態倫理、生態文學以及景觀生態設計等領域的滋養下,西方生態美學逐漸與傳統的自然美學以及新興的環境美學區分開來。
被譽為“生態美學之父”的美國生態倫理學家利奧波德(Aldo Leopold)在他的《沙鄉年鑒》中首次以“大地美學”的理論形態將生態、倫理和美關聯起來,探索了生態環境的倫理價值和美學意蘊。利奧波德將生態的“和諧”“穩定”與“美”的概念結合起來并一同作為其土地倫理正確與否的標準,實則就是打破了美學與生態學的界限,建立了二者之間的雙向關系——自然“美”被賦予了全新的生態意義,同時指明了美在衡量生態健康中的重要作用。雖然利奧波德并未明確提出“生態美學”的概念,但其土地倫理中所蘊含的這種大地美學,已經具備了濃厚的生態美學意蘊。
利奧波德之后的一段時間,西方生態美學的發展主要體現在生態文學和景觀生態設計理論領域。1962年,萊切爾·卡遜(Rachel Carson)《寂靜的春天》一書出版。作為生態文學里程碑式的作品,該書以文學細膩的筆觸從生態整體的角度重新探討了人與自然的關系。1972年美國學者約瑟夫·米克(Joseph W.Meaker)在《生存的喜劇——文學生態學研究》一書中,首次使用了“生態美學”這一術語,并將其作為第六章的標題。米克在繼承了利奧波德生態倫理思想的基礎上,從西方思想文化的根源及其在文學領域中的呈現探索了生態美學建構的可能性和合法性問題;在審美理論上,他提出只有結合當代生態生物學知識,自然審美才能恰當地界定美與丑的范疇。對自然美生態模式的探索更為鮮明、系統的是西方景觀生態設計的實踐范式,這主要體現在賈蘇克·科歐(Jusuck Koh)的“生態建筑設計美學”和戈比斯特(P.H.Gobster)的“森林景觀管理生態美學”中。
西方生態美學在美國學者希拉·林托特(Sheila Lintott)這里得到了理論整合。林托特在利奧波德大地美學和戈比斯特生態美學研究的基礎上,將生態科學、自然審美和環境保護三者聯系起來進行考察,提出了她的“生態友好型美學”。林托特提出,生態科學雖不存在于對象本身,卻與該對象的審美密切關聯。林托特的“生態友好型美學”使生態學、美學和環境保護在互相聯系中各司其職、互相促進,在確立生態友好審美品味的基礎上促成生態美學對自然保護的指導意義。
相比于生態倫理、生態文學以及景觀設計實踐對西方生態美學理論發展的推動,自然審美在中國則直接進入了一個“生態”本體論的語境,以“生態美學”的理論形態發展起來。短短20來年,中國生態美學涌現出了一大批理論代表,如曾永成的“人本生態美學”,袁鼎生強調“整生”的生態審美,曾繁仁的“生態存在論美學”以及程相占的“生生美學”等。其中,曾繁仁的“生態存在論美學”最能代表中國生態美學發展的成就。
總體來講,中西生態美學雖然側重點不同,但都圍繞著自然“生態”的維度對自然美理論進行了重構,總體表現為四方面特征。其一,在審美視野上,生態美學突破了二元對立的機械論世界觀,轉向一種生態進化論和生態整體主義的世界觀。生態美學雖然同部分環境美學一樣,強調了“生態”概念,但與環境美學不同的是,“生態”不再作為一種知識因素來介入,而是以生態整體性介入審美之中,從而超越了環境美學對自然局部認知的局限性。其二,在審美立場上,生態美學對自然審美的重構不僅打破了傳統自然審美在人類中心主義立場上的靜觀審美,也超越了環境美學導向的環境中心主義,走向了一種新的生態人文主義,包含了人、社會、文化、環境四個維度的融合。其三,在審美標準上,生態美學從生態整體的健康、和諧、美麗出發,恢復了環境美學“自然全美”“一切皆可”導致的標準缺失,聯系起了審美對環境保護的應有之義。其四,從審美體驗來看,生態美學是在整體的感知體驗中獲得的一種間接的和諧感,而非直接的視覺愉悅,也正是在這種生態和諧、物我合一的完整性體驗中,生態審美完成了從感官體驗到精神完滿的升華,走向了一種參與的、人性的、情境的綜合美學。
生態美學的路徑強調把自然美放在作為整體的生態系統中來考察。如果說環境美學是對自然美在形式問題上的突破,生態美學則是進一步完成了對自然美從物質實體到生命本體、從局部對象之“美”到生態整體的“和諧”之美的超越。
形而上學:自然美作為人類生存的一種確證
自然美理論重建的第三種路徑是形而上學的路徑,這種路徑在思維方式上轉變了傳統自然美研究的對象化的本質主義方法論,遵循自然美建構的歷史演進邏輯,將自然美視為人類生存的一種確證,通過自然美呈現出存在的真理性問題,從形而上學角度重建了自然美理論。這種路徑的代表人物為西奧多·阿多諾(Theodor W.Adorno)、彭鋒和劉成紀。
阿多諾通過“自然美與藝術互相救贖”的路徑,以自然美的真理性為核心重建了自然美的形而上學性。阿多諾對于自然美的討論是在藝術與美學的框架之中進行的。自然美以其獨特和非同一的內蘊支撐起現代藝術的真理性和超越性,也因此重新獲得了在美學理論領域存在的合法性和必要性。然而,由于自然美具有不可界說和不可概念化的本質,拒絕一切以概念和理性的方式進行認知的途徑,于是阿多諾便否認了在現代社會進行自然審美的可能性,因而他最終選擇的不是重建自然美學而是救贖藝術的道路。他在自然美中重新找到了抵抗和救贖嚴重扭曲和異化的人與社會的唯一力量,然后將自然美的真理性內核移植到現代藝術之中,讓藝術蘊含著自然美并肩負起社會批判和救贖的使命。這是一條通過對自然美真理的重塑而將其納入藝術理論體系的思路,而不是重建自然美理論的路徑,但是阿多諾的這種對自然美真理性的重塑為我們重建自然美的形而上學性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
真正對自然美形而上學性進行重建的是彭鋒的“恢復人與自然原初和諧狀態”的路徑。他認為:“審美經驗是人生在世的本然經驗,審美對象是事物的本然樣態,審美中的人與對象的關系是一種前真實的肉身關系。”因此,審美并不是對對象進行美或丑的判斷,也不僅僅是一種純粹的靜觀,而是一種全方位的、本然的生存樣態。自然美最具有“解構舊范疇并引導新范疇的表現力”和審美上的優越性:“自然在根本上是我們人類及其世界的真身和根源。換句話說,從自然是我們人類及其世界的原初形式來說,自然本身就是美的。”正是自然與人及其世界相異又相似的雙重性,使得自然美獲得了既解構又建構人類文化形式的張力,進而獲得了美學上的優勢。彭鋒在環境美學和生態美學研究思路之外,從自然美的形而上學性層面反思自然美作為原初審美經驗的可能性,為重建自然美理論提供了一條新的思路。
劉成紀則通過“人與自然共在和互賞”的路徑來建構自然美的形而上學性。他認為,重建自然美理論既要解決自然的問題,又要解決人的問題。因而,重新認識自然美的主體和客體基礎成為自然美學重建的切入點。劉成紀認為,使自然美得以統一的主體性和物性交匯于人的身體之上,人具有精神性和肉身物性的雙重本質,一旦整個身體成為自然審美的主體,那么物性必然最大限度地克服精神性,人與自然之間人為設置的鴻溝也就得以填平了。由全部身體充當自然審美體驗的中介,人的主體性讓位給了身體的客觀性,因此審美判斷實現了主體與自然對象最終的契合。
結語
鑒于上述三條路徑,我們對于自然美理論的重建,不能局限于某一方面,而應該綜合物性(生態本性)和詩性(主體)兩個方面,以之為基礎來建構一種后形而上學語境下的自然美理論體系。首先,我們要尊重自然的物性,擯棄人類加載在自然身上的精神重負,確立尊重和熱愛自然的情感原則,確證物性在自然美生成中的作用。我們要充分吸收環境美學和生態美學對自然物性充分尊重的理論觀點。其次,要建構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生命共同體,在尊重物性的基礎上尊重人性,借鑒生態倫理學的方法,將自然作為人類生存的他者,擔當起尊重和守護自然的道德責任,將人的詩性主體在自然美生成中的豐富性充分挖掘出來。最后,自然是具有生命的,自然形式美就是其生命的表現形態,人作為自然的一分子,人的生存就融入這種生命形式之中,自然的形式美是自然生命的活潑潑的呈現。對此,中國古典美學的天人合一、生生之為美、對自然的詩意關照等原則都可以成為后形而上學語境下自然美理論重建的方法論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