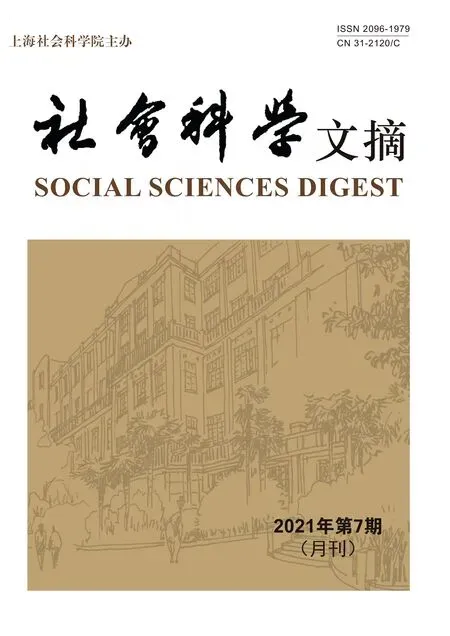陳獨(dú)秀的政治何以不得不談?
——“不談?wù)巍迸c轉(zhuǎn)型時(shí)代知識分子時(shí)代轉(zhuǎn)型
文/魏旭
從甲午戰(zhàn)爭后到20世紀(jì)20年代中期,張灝先生稱這一時(shí)期為轉(zhuǎn)型時(shí)代,這是中國思想文化承先啟后的關(guān)鍵時(shí)期,思想知識的傳播媒介和內(nèi)容有了突破性巨變,逐步產(chǎn)生了棲身其中的新的社群媒體——現(xiàn)代知識分子。關(guān)于“知識分子”,總體上是指靠某種專業(yè)知識謀生、具有強(qiáng)烈社會責(zé)任感的群體,在薩義德看來,重要的是“全身投注于批評意識”。這意味著現(xiàn)代知識分子批評政治,卻未必以政治為業(yè)。不過,中國古代的讀書人倒是很大程度上以政治為業(yè),如果說他們是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前身,那么轉(zhuǎn)型時(shí)代呈現(xiàn)的正是知識分子身上學(xué)術(shù)與政治分離的轉(zhuǎn)型過程。以學(xué)術(shù)為業(yè)的現(xiàn)代知識分子繼續(xù)呼吁“不談?wù)巍保喈?dāng)一部分投身社會運(yùn)動的政治行動主義者成為職業(yè)革命家。陳獨(dú)秀是在轉(zhuǎn)型時(shí)代嶄露頭角的,從早年大搞革命活動到突然“不談?wù)巍保俚轿逅倪\(yùn)動后發(fā)表《談?wù)巍罚c政治的糾葛一直備受矚目。陳獨(dú)秀對政治的態(tài)度變化與知識分子的時(shí)代轉(zhuǎn)型有著時(shí)間上的耦合,某種程度上反映著這個轉(zhuǎn)型的復(fù)雜過程。
懸而未決的張力:轉(zhuǎn)型時(shí)代知識分子的政治與學(xué)術(shù)
中國古代有讀書人群體,大約從春秋戰(zhàn)國時(shí)期基本形成的“士”階層開始,爾后數(shù)千年一直在歷史演進(jìn)中發(fā)揮著主持與領(lǐng)導(dǎo)作用。他們不像現(xiàn)代知識分子那樣受到知識專業(yè)化影響,道德和知識訓(xùn)練通常是一些“不那么功利、目的性不那么具體的超技能的持續(xù)學(xué)習(xí),一種追求和探尋無用之用的努力”。傳統(tǒng)讀書人兼得政治和學(xué)術(shù),轉(zhuǎn)型時(shí)代則要求知識分子“仕學(xué)分途”。隨著清末廢科舉,讀書人以政治為業(yè)的制度通道被正式割斷,轉(zhuǎn)而棲身于各類依靠專業(yè)知識的社會職業(yè),成為游離于政府之外的自由人。然而,讀書人肩負(fù)的道義責(zé)任還在,轉(zhuǎn)型時(shí)代的政治也需要他們來過問。這樣,清理學(xué)術(shù)與政治的關(guān)系便不是簡單的態(tài)度問題,更是知識分子面臨的時(shí)代命題。
轉(zhuǎn)型時(shí)代要求知識分子褪去政治的一面,但內(nèi)憂外患的政治局面,反而成為許多讀書人化身為政治行動主義者的動力。這個時(shí)代的知識分子視拯救國家為己任,這是自古以來讀書人肩負(fù)的道義和責(zé)任所激發(fā)的,但又不可避免受到自身轉(zhuǎn)型的大勢束縛。學(xué)術(shù)與政治間的張力終究是要解決的,由此引出一個問題:何時(shí)二者能真正切割開來?何時(shí)這種徘徊的狀況變得不可能了?知識分子在五四運(yùn)動前后的差異是值得注意的,一個引人注目的現(xiàn)象就是,歷史舞臺上出現(xiàn)了相當(dāng)一批多的職業(yè)革命家,隨后的革命運(yùn)動中知識分子似乎被邊緣化了。
之所以認(rèn)為五四運(yùn)動前后是知識分子轉(zhuǎn)型的重要時(shí)點(diǎn),還在于五四運(yùn)動本就有著從學(xué)術(shù)轉(zhuǎn)向政治的一面。胡適曾稱五四運(yùn)動“實(shí)是這整個文化運(yùn)動中的一項(xiàng)歷史性的政治干擾。它把一個文化運(yùn)動轉(zhuǎn)變成一個政治運(yùn)動” 。傅斯年亦認(rèn)為,“五四運(yùn)動過后,中國的社會趨向改變了,有覺悟的添了許多”,“以后是社會改造運(yùn)動的時(shí)代”,“醞釀些時(shí),中國或又有一種平民的運(yùn)動”。陳獨(dú)秀更是清楚表示,“文化運(yùn)動與社會運(yùn)動本來是兩件事,有許多人當(dāng)做是一件事”。如果把文化運(yùn)動和政治運(yùn)動看成是知識分子在新文化運(yùn)動中從事的兩類活動的話,那么在五四運(yùn)動之后,從事學(xué)術(shù)和政治在知識分子身上變得難以兼得。這一變化在陳獨(dú)秀身上頗為直觀,作為曾影響一代人的著名知識分子,追求學(xué)術(shù)和政治在他身上演繹著雙重變奏。他在新文化運(yùn)動中常宣稱“不談?wù)巍保逅倪\(yùn)動后又迅速成為職業(yè)革命家。他有關(guān)政治的談與不談,與知識分子的時(shí)代轉(zhuǎn)型密切相關(guān)。
革命者的政治疏離:陳獨(dú)秀的“不談?wù)巍?/h2>
陳獨(dú)秀踏上政治之路很早,早在20世紀(jì)初就成為務(wù)實(shí)的革命派。他因曾在杭州求是學(xué)院發(fā)表反清演說遭到當(dāng)局通緝,可以說這是他“從事政治活動的開始”。1902年,在日留學(xué)時(shí),他加入青年團(tuán)體“勵志會”,當(dāng)年又在安慶與柏文蔚等人組織“青年勵志學(xué)社”,開辟“藏書樓”展出革命書刊,還曾被清廷列為首要叛亂分子追捕。1904年,陳獨(dú)秀參加了楊篤生等人組織的上海暗殺團(tuán),后來他回憶,當(dāng)時(shí)“住上海月余,天天從楊篤生、鐘憲鬯試驗(yàn)炸藥”,后來對吳樾預(yù)謀暗殺清廷出國考察憲政的五大臣的革命事件也有參與。1905年,陳獨(dú)秀在蕪湖創(chuàng)辦“岳王會”并擔(dān)任會長,該會宗旨就是推翻清王朝。民國建立后他又積極為革命奔走,先是應(yīng)孫毓筠之邀出任安徽都督府秘書長,后又協(xié)助柏文蔚治皖,并在二次革命中追隨柏文蔚積極反袁,直至反袁失敗后被迫流亡。
陳獨(dú)秀的革命活動是隱藏在學(xué)人身份下的。他職業(yè)相當(dāng)多樣。他當(dāng)過報(bào)人:1904年應(yīng)邀擔(dān)任《國民日日報(bào)》編輯,并在1904年到1905年間創(chuàng)辦《安徽俗話報(bào)》,后又成為《甲寅》雜志的撰稿人。他當(dāng)過教員:1905年擔(dān)任安徽公學(xué)的國文教員,1909年又到杭州任職浙江陸軍小學(xué)國文史地教員,1912年在安徽大學(xué)堂舊址重辦安徽高等學(xué)校,自任教務(wù)主任,常就教育發(fā)表演講。他寫書譯書:1903年出版了一本《小學(xué)萬國地理新編》,作為小學(xué)堂的教材,1913年又撰寫了《字義類型》和編纂了《新華英文教科書》,留下不少詩詞作品。這些職業(yè)身份當(dāng)然是為政治活動服務(wù)的,這些靠知識謀生的活動是其公開的本職。
辛亥革命的失敗致使陳獨(dú)秀思想發(fā)生轉(zhuǎn)變,出于對政局的極度失望,他產(chǎn)生了不談?wù)蔚南敕ā?914年11月,陳獨(dú)秀在《甲寅》雜志發(fā)表了著名的《愛國心與自覺心》,聲稱已經(jīng)對現(xiàn)實(shí)政治失去了熱情,并指出問題在于民眾的覺悟。文章將人心分為“情”和“智”,愛國心是“情之屬”,自覺心是“智之屬”,前者是立國之要素,后者則辨別“用適其度”。“今之中國,人心散亂,感情智識,兩無可言”,結(jié)論就是“今吾國之患,非獨(dú)在政府。國民之智力,由面面觀之,能否建設(shè)國家于二十世紀(jì),夫非浮夸自大,誠不能無所懷疑”。文章透露出了陳獨(dú)秀的傷感,或可視為他疏離政治的告別書。但不能據(jù)此認(rèn)為他已無心政治了,陳獨(dú)秀所傳達(dá)的既是悲嘆更是不甘。他疏離國家和政府,卻逐步醞釀出一條“不談?wù)巍钡男侣贰?jù)好友汪孟鄒回憶,“他想出一本雜志,說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會發(fā)生很大的影響”。1915年9月,他在上海創(chuàng)刊了《青年雜志》(后改名《新青年》)。1917年1月,陳獨(dú)秀出任北京大學(xué)文科學(xué)長,這份雜志也隨遷北大,由此聚集了一批致力文化革命的知識分子,如胡適、吳虞、錢玄同、劉半農(nóng)、魯迅等人,轟轟烈烈的新浪潮向全國鋪開。
走向職業(yè)革命家:五四運(yùn)動時(shí)期陳獨(dú)秀的政治抉擇
在陳獨(dú)秀看來,中國問題的根本解決有待于“政治的覺悟”和“倫理的覺悟”,后者“為吾人最后覺悟之最后覺悟”。在《新青年》上,他反對孔教,對于孔教“不可不有徹底之覺悟,猛勇之決心,否則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他高揚(yáng)自由,稱自由意味著“一切操行,一切權(quán)利,一切信仰,唯有聽命各自固有之職能”。他倡導(dǎo)科學(xué)和民主:“我們現(xiàn)在認(rèn)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xué)術(shù)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他創(chuàng)刊之日即號召:“予所欲涕泣陳詞者,惟屬望于新鮮活潑之青年,有以自覺而奮斗耳!”新文化運(yùn)動被視為思想啟蒙運(yùn)動,一系列活動展示出陳獨(dú)秀宣揚(yáng)學(xué)術(shù)的一面,因?yàn)樗还膺h(yuǎn)離政治活動,而且“不談?wù)巍薄?/p>
要說“不談?wù)巍保惇?dú)秀確實(shí)曾經(jīng)下過決心,只是既談不上嚴(yán)守,也沒有持續(xù)多久。《青年雜志》創(chuàng)刊初期便定下基調(diào):“批評時(shí)政,非其旨也。”同人和讀者也認(rèn)同《新青年》不探討時(shí)政。然而,這只是就總體而言,實(shí)際上他所主編的《新青年》前三卷,都設(shè)有評點(diǎn)政治事務(wù)的“國外大事記”和“國內(nèi)大事記”,后來他也解釋:“新文化運(yùn)動影響到政治上,是要創(chuàng)造新的政治理想,不要受現(xiàn)實(shí)政治底羈絆。”不過,對“不談?wù)巍笨傮w上的嚴(yán)守也沒有持續(xù)多久。1918年12月,陳獨(dú)秀與李大釗、高一涵等人共同創(chuàng)辦《每周評論》,宣稱“主張公理、反對強(qiáng)權(quán)”。相比于《新青年》,它的出版周期短、板塊劃分靈活,正適合大談?wù)危惇?dú)秀每期都發(fā)表點(diǎn)評國內(nèi)外政治的“隨感錄”若干條。《每周評論》還形成了強(qiáng)烈的示范效應(yīng),帶動了一批學(xué)生團(tuán)體和學(xué)生刊物的創(chuàng)立,新文化運(yùn)動的政治一面越來越明顯了。
1919年五四運(yùn)動爆發(fā),陳獨(dú)秀又邁出一步,不光大談?wù)危抑匦麻_展政治活動。他在《每周評論》和《新青年》發(fā)表多篇文章。值得注意的是,他在6月8日的《每周評論》發(fā)表《我們究竟應(yīng)當(dāng)不應(yīng)當(dāng)愛國》的同時(shí),又連載14則“隨感錄”,其中包括著名的《研究室與監(jiān)獄》,鼓勵人們“出了研究室就入監(jiān)獄,出監(jiān)獄就入研究室”。他還起草《北京市民宣言》,其后在北京街頭散發(fā)傳單被捕。出獄后的陳獨(dú)秀對政治更具熱情,開始專心從事社會運(yùn)動。1920年初南下后,陳獨(dú)秀真正走進(jìn)工人運(yùn)動,在武漢、上海密集參與勞工集會,宣揚(yáng)階級斗爭。比如,在上海演講時(shí),他號召工人有覺悟,當(dāng)年底,他又強(qiáng)調(diào)工人運(yùn)動“務(wù)必要專心在工會組織和工人生活改良上做功夫”,而不可像過去的政客活動那樣帶了“政治的臭味”。
陳獨(dú)秀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和參與社會運(yùn)動是相輔相成的。在1919年底的《新青年》宣言中,他明確表示“我們主張的是民眾運(yùn)動、社會改造”。1920年9月,《新青年》第8卷第1號頭篇文章正是著名的《談?wù)巍罚皇樗渡砩鐣\(yùn)動的宣言書。陳獨(dú)秀開宗明義地指出:“你談?wù)我擦T,不談?wù)我擦T,除非逃在深山人跡絕對不到的地方,政治總會尋著你的。”并明確表示要開展階級斗爭和“勞動階級專政”,今后努力的方向就是“用革命的手段建設(shè)勞動階級的國家”。當(dāng)年11月,《共產(chǎn)黨》月刊在上海創(chuàng)立。1921年1月,他在廣州再次論證,唯有社會主義能“救濟(jì)現(xiàn)代經(jīng)濟(jì)的危機(jī)及社會不安的狀況”,應(yīng)該采用俄國共產(chǎn)主義式的社會主義:階級斗爭、直接行動、無產(chǎn)階級專政、國際運(yùn)動。半年后,陳獨(dú)秀在中國共產(chǎn)黨一大上當(dāng)選中央局書記,成為一名專心于社會運(yùn)動的職業(yè)革命家。
政治的談與不談之間:作為社會運(yùn)動的政治
回顧陳獨(dú)秀這些活動軌跡,他在轉(zhuǎn)型時(shí)代與政治的糾葛尤為引人注目:他在新文化運(yùn)動前后都是活躍的政治行動主義者,唯獨(dú)在發(fā)表《愛國心與自覺心》到五四運(yùn)動前竟聲稱“不談?wù)巍薄A袑幘俚刂赋觯骸肮_聲明不再過問政治,這也就是政治。”或許應(yīng)該這樣理解,“不談?wù)巍贝_是對有關(guān)政府的政治活動既不參與也不公開談?wù)摚⒎菬o心政治本身,可以說陳獨(dú)秀沒有改變對政治的關(guān)心,只是對政治的理解變了。既然陳獨(dú)秀身上的政治線索并未因“不談?wù)巍倍兴袛啵敲此谖逅倪\(yùn)動后逐步走向職業(yè)革命家也不能以偶然事件來解釋:當(dāng)陳獨(dú)秀在一戰(zhàn)后選擇了公開重談?wù)危愫芸赡苓M(jìn)一步重新投身政治活動;當(dāng)他產(chǎn)生了無產(chǎn)階級覺悟,從事工人運(yùn)動也勢所必然;而當(dāng)他在五四運(yùn)動后繼續(xù)“消耗在政治生涯中”,是否離開北大已不影響他是否成為革命家了。時(shí)人郭湛波曾提到:“中國研究馬克思學(xué)說最有心得,介紹最早的就算陳獨(dú)秀、李大釗、李達(dá)。尤以陳氏的影響為大。”那么當(dāng)時(shí)陳獨(dú)秀是怎么介紹的呢?他將馬克思的學(xué)說歸結(jié)為“實(shí)際研究的精神”和“實(shí)際活動的精神”,對他而言,“寧可少研究點(diǎn)馬克思的學(xué)說,不可不多干馬克思革命的運(yùn)動”。
值得注意的是,對比陳獨(dú)秀“不談?wù)巍鼻昂螅m然都從事革命活動,其性質(zhì)卻大不相同。著名革命史學(xué)家斯考切波曾區(qū)分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政治革命“改造的是政權(quán)結(jié)構(gòu)而非社會結(jié)構(gòu),而且并不必然要經(jīng)由社會沖突來實(shí)現(xiàn)”;社會革命則“社會變遷與階級突變同時(shí)進(jìn)行;政治轉(zhuǎn)型與社會轉(zhuǎn)型同時(shí)展開”,與之相伴的是自下而上的階級反抗。陳獨(dú)秀在清末民初和五四運(yùn)動后的不同表現(xiàn)則反映了這樣的轉(zhuǎn)換。比如,他早年多是參與暗殺團(tuán)、會黨活動,這些活動對象很有限,目標(biāo)也很明確,革命領(lǐng)袖的視域很難超出國家層面。五四運(yùn)動后的社會革命則不同,比如出現(xiàn)了諸多具有代表性的大眾政黨,有明確的意識形態(tài)旗幟,著眼廣泛的社會動員以爭得民眾支持,目標(biāo)直指社會的根本變革,手段多樣且富有公開性。總之,兩相對比,隨著中國革命形勢的變化,以陳獨(dú)秀為代表的一批知識分子本身也發(fā)生了變化,不再局限于關(guān)注國家政權(quán),而是更加下沉到廣泛的社會運(yùn)動中了。
“不談?wù)巍钡谋澈笳菍ι鐣拇蟀l(fā)現(xiàn)。清末民初陳獨(dú)秀面對的是社會之上的國家和政府層面的政治,革命活動多是會黨結(jié)社和秘密行動之類,而他的社會職業(yè)是報(bào)人或教員,學(xué)術(shù)和政治之間雖有張力但畢竟仍是兼具的。陳獨(dú)秀的《愛國心與自覺心》宣告放棄對國家政權(quán)的幻想,在新文化運(yùn)動中,陳獨(dú)秀是享譽(yù)全國的北大教授,他的確不再談過去那種政治了,經(jīng)由“發(fā)現(xiàn)社會”,政治早已拓展到社會中,可以說學(xué)術(shù)是明線、政治是一條暗線,一明一暗之間,政治和學(xué)術(shù)尚能兼容。五四運(yùn)動后,政治既不是秘密行動,也不是隱性活動了,而是一項(xiàng)需要大眾參與的關(guān)涉全社會的“直接行動”了,這時(shí)政治和學(xué)術(shù)便只能二擇其一了。進(jìn)一步而言,當(dāng)政治須在社會運(yùn)動中進(jìn)行時(shí),選擇政治便成了一條通往職業(yè)革命家的道路。列寧曾談道:“自發(fā)地卷入斗爭、構(gòu)成運(yùn)動的基礎(chǔ)和參加到運(yùn)動中來的群眾愈廣泛,這種組織(共產(chǎn)黨)也就愈迫切需要,也就應(yīng)當(dāng)愈鞏固”,“這種組織的構(gòu)成主要應(yīng)當(dāng)是以革命活動為職業(yè)的人”。此外,學(xué)術(shù)也成了避免政治干涉的專業(yè)活動,徐復(fù)觀注意到過去學(xué)術(shù)與政治現(xiàn)象的混雜,直言五四運(yùn)動時(shí)期只是學(xué)術(shù)研究的“宣傳時(shí)代”,到北伐后才成為“研究時(shí)代”,這時(shí)“‘打倒孔家店’這一派的人,已失掉了對學(xué)術(shù)界的影響力”。
結(jié)語
對于轉(zhuǎn)型時(shí)代的知識分子,政治和學(xué)術(shù)之間是存在張力的。傳統(tǒng)讀書人具有學(xué)術(shù)身份的同時(shí)又以政治為業(yè),而現(xiàn)代社會則要求知識分子褪去政治的一面。以陳獨(dú)秀為例,他在轉(zhuǎn)型時(shí)代經(jīng)歷了從積極反清到“不談?wù)巍痹俚匠蔀槁殬I(yè)革命家的轉(zhuǎn)變,展示的正是知識分子身上政治和學(xué)術(shù)的分離,政治本身影響了這個過程。當(dāng)五四運(yùn)動后,政治本身成了一項(xiàng)面向大眾的社會運(yùn)動,政治和學(xué)術(shù)之間的張力也達(dá)到了頂點(diǎn)。這在著名的“問題與主義”論戰(zhàn)之中有所體現(xiàn)。胡適奉勸人們“多多研究這個問題如何解決,那個問題如何解決”,李大釗則強(qiáng)調(diào)根本解決之道,認(rèn)為要提取共同的社會問題,須“先有一個共同趨向的理想、主義”。就論戰(zhàn)的實(shí)質(zhì)而言,其實(shí)并非要不要“學(xué)理”抑或“紙上的學(xué)說”,而是關(guān)于要不要繼續(xù)做研究室里盯著具體問題的專家,抑或用某種一攬子方案來促成社會運(yùn)動的職業(yè)革命家。
學(xué)術(shù)和政治既然成了二選一的抉擇,知識分子本身也就完成了轉(zhuǎn)型。要么以政治為業(yè),比如中國共產(chǎn)黨早期領(lǐng)導(dǎo)人大都受過良好的中西學(xué)教育,成為革命者之前很多人從事教員或編輯等職業(yè)。要么專注學(xué)術(shù)身份,成為報(bào)人、教授、科學(xué)家等各種憑借專業(yè)知識的謀生者。可以說,一條路通往的是居于舞臺中央的職業(yè)革命家,視政治使命的實(shí)現(xiàn)為天職;另一條路則通往專注學(xué)術(shù)的現(xiàn)代知識分子。現(xiàn)代知識分子和職業(yè)革命家的分流正是轉(zhuǎn)型時(shí)代帶來的結(jié)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