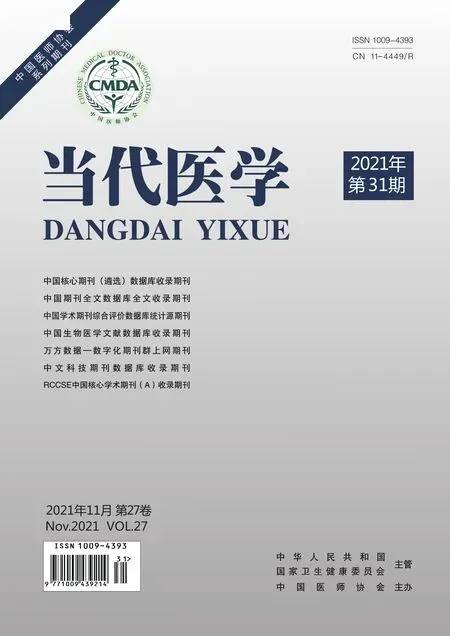探析硬膜外分娩鎮痛與產婦發熱及并發癥的關系
謝育娣,林雅真,葉倩
(1.廈門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婦產科,福建 廈門 361003;2.武平縣醫院婦產科,福建 龍巖 364300)
二胎政策開放以后,我國迎來新一輪生育高峰,選擇無痛分娩的產婦也越來越多[1]。硬膜外分娩鎮痛是產婦常用的一種鎮痛方式,可緩解產婦分娩時引起的劇烈疼痛,緩解其由此引起的焦慮及恐懼心理,防止出現血壓的不穩定,還可促進陰道及盆腔肌肉的松弛,有利于胎頭下降及宮頸擴張,使產婦盡早順利分娩[2]。硬膜外分娩的鎮痛效果顯著,在臨床應用廣泛,但少數患者會出現不良反應,如低血壓、頭痛、惡心嘔吐等,部分患者甚至出現產時發熱的現象,此現象發生后易造成不良的分娩結果,發生產后出血、羊水污染的情況,胎兒體溫也會升高,使其出現缺氧、宮內窘迫及窒息的風險,引發缺氧性腦損傷及敗血癥,甚至有胎死宮內的風險。關于產時發熱的發病機制尚不明確,多數學者認為與感染有關,而硬膜外分娩鎮痛是產時發熱的獨立危險因素,但其引起的發熱為非感染性[4]。基于此,本研究選取于本院分娩的150例產婦,旨在探討硬膜外分娩鎮痛與產婦發熱及并發癥的關系,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選取2019年1月至2020年7月于本院分娩的150例產婦作為研究對象,按照隨機抽簽的方式分為兩組,抽取到單號的產婦作為對照組(n=50),抽取雙號的產婦作為觀察組(n=100)。對照組年齡20~40歲,平均年齡(28.98±3.56)歲;孕周38~41周,平均孕周(39.12±0.67)周;宮頸Bishop評分(3.21±1.09)分。觀察組年齡21~42歲,平均年齡(28.92±3.51)歲;孕周38~40周,平均孕周(39.09±0.61)周;宮頸Bishop評分(3.19±1.08)分。兩組患者臨床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具有可比性。納入標準[3]:①均為足月單胎產婦,頭位;②未見自發性宮縮;③無胎膜早破;④無嚴重合并癥或麻醉禁忌。排除標準:①產前發熱,體溫≥37.3℃;②由呼吸道感染、泌尿系統感染及闌尾炎引起的發熱;③精神病史;④胎位不正、雙胎及以上;⑤對本研究使用的麻醉藥物過敏者。
1.2 方法 對照組未實施分娩鎮痛。觀察組實施硬膜外分娩鎮痛,產婦宮口開至2~3 cm時,實施硬膜外麻醉,將L2~L3椎間隙作為穿刺點,注入2%利多卡因(山西晉新雙鶴藥業有限責任公司,國藥準字H11022295,規格:5 mL∶0.1 g)2 mL∶0.05 mg/kg芬太尼(國藥集團工業有限公司廊坊分公司,國藥準字H20123298,規格:10 mL∶0.5 mg),觀察患者有無不良反應,隨后固定導管,連接鎮痛泵,其中藥物配方為0.9%氯化鈉注射液(上海百特醫療用品有限公司,國藥準字H19983149,規格:1 000 mL∶9 g)、0.75%羅哌卡因(廣東華潤順峰藥業有限公司,國藥準字H20050325,規格:75 mg)及0.2 mg芬太尼,首劑為12 mL,持續泵入10 mL/h,自控鎮痛6 mL/h,最大用量30 mL/h。待產婦宮口全開后,將鎮痛泵關閉,產程結束后撤出硬膜外導管及鎮痛泵。
1.3 觀察指標 ①不同產程體溫情況。②產時發熱發生率。③并發癥發生情況,包括羊水污染、新生兒感染及產后出血等。④晨起在空腹的狀態下,抽取患者5 mL靜脈血,離心處理后,放置-80℃冰箱保存,采用放射免疫法檢測血清白細胞介素-6(IL-6),試劑盒由上海酶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根據試劑盒說明書內容進行操作。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0.0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采用“x±s”表示,予以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n(%)]表示,予以χ2檢驗,硬膜外分娩鎮痛與產婦發熱及并發癥的關系采用Logistic回歸分析,以P<0.05表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產婦不同產程體溫比較 觀察組產婦第二產程及第三產程的體溫均高于對照組(P<0.05),見表1。

表1 兩組產婦不同產程體溫比較(x±s)Table 1 Comparison of body temperature between two groups of parturients in different stages of labor(x±s)
2.2 兩組產婦產時發熱發生率比較 觀察組發熱時體溫37.3℃≤產時體溫<38℃發生率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發熱體溫>38℃發生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見表2。

表2 兩組產時發熱發生率比較[n(%)]Table 2 Comparison of the incidence of fever during childbirth in the two groups[n(%)]
2.3 兩組并發癥發生率比較 觀察組并發癥發生率高于對照組,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見表3。

表3 兩組并發癥發生率比較[n(%)]Table 3 Comparison of complication rat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n(%)]
2.4 兩組產婦不同時間段血清IL-6水平比較 觀察組鎮痛后2 h、分娩前及分娩后2 h的血清IL-6水平均高于對照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4。

表4 兩組產婦不同時間段血清IL-6水平比較(x±s)Table 4 Comparison of serum IL-6 level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parturients at different time periods(x±s)
2.5 硬膜外分娩鎮痛與產婦發熱及并發癥發生的Logistic線性回歸分析 以產婦發熱及并發癥為應變量,硬膜外分娩鎮痛及不同產程為自變量,進行Logistic線性分析,結果顯示,硬膜外分娩鎮痛及不同產程均為產婦發熱及并發癥發生的獨立危險因素(P<0.05),見表5。

表5 硬膜外分娩鎮痛與產婦發熱及并發癥發生的Logistic線性回歸分析Table 5 Logistic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of epidural labor analgesia and maternal fever and complications
3 討論
分娩疼痛的產生是由于子宮收縮時胎兒經產道娩出,使子宮肌層缺血嚴重,導致大量致痛物質被大量釋放,尤其是產程活躍期,宮縮加強會加劇疼痛,使產婦產生各種煩躁及焦慮情緒,導致血壓波動大,造成不良的分娩結局[5]。產婦忍受劇烈疼痛時,呼吸明顯加快,機體耗氧量加大,發生呼吸性堿中毒的風險高,如分娩疼痛未得到及時緩解,易導致胎盤供血不足,使胎兒出現宮內缺氧的情況[6]。硬膜外分娩鎮痛是產婦常用的鎮痛方式,其鎮痛效果確切,鎮痛時間靈活,在臨床應用廣泛[7]。但實施硬膜外分娩鎮痛后,產婦易出現產時發熱現象,引發不良的分娩結局,據調查[8],約30%的產婦分娩時會出現發熱現象,而實施硬膜外分娩鎮痛的產婦出現發熱的概率高于未實施麻醉鎮痛的產婦。
母體發熱后,耗氧量會不斷增加,使胎兒血液中含氧量降低,而子宮溫度升高導致胎兒無法正常散熱,易出現宮內窘迫及窒息的情況,引發羊水污染及宮內感染的情況[9]。導致產婦產時出現發熱現象的因素較多,分為感染性及非感染性,由病原體入侵引發的感染,患者如出現發熱則為感染性發熱,研究指出,產婦體溫升高缺乏感染相關支持依據,可見發熱與非感染因素有關[10]。硬膜外分娩鎮痛可使被阻滯的神經支配的皮膚血管擴張,導致體表溫度升高,而硬膜外分娩鎮痛與產時發熱的關系復雜,部分學者認為母體體溫調節紊亂是導致發熱發生的主要原因,由于麻醉平面以上的血管出現收縮,使體溫調節中樞接收信號的能力減弱,機體產生的熱量大于散發的熱量,進而導致發熱情況發生[11]。同時,麻醉藥本身也會引發低熱,尤其是阿片類藥物,以導致體溫升高的情況發生。本研究中選用的芬太尼為阿片類激動劑,會導致體溫升高,羅哌卡因也會影響體溫,使其得以升高[12]。
本研究結果顯示,觀察組產婦第二產程及第三產程的體溫均高于對照組(P<0.05),觀察組37.3℃≤產時體溫<38℃發生率高于對照組(P<0.05),說明實施施硬膜外分娩鎮痛會增加第二產程及第三產程體溫升高及發熱的概率,發熱多數情況下不需使用抗生素。麻醉鎮痛后,產婦發熱時,子宮溫度升高,胎兒在較高的環境內會出現心動過速的情況,血液循環異常,進而發生胎兒窘迫及胎死宮內的不良分娩結局[13]。本研究結果也證實,觀察組并發癥發生率高于對照組,進一步說明發熱與并發癥的發生相關。有學者認為[14],硬膜外分娩鎮痛導致體溫升高可能與炎性因子激活有關,學者發現產婦血清中IL-6水平隨著鎮痛時間的延長而增高,且麻醉組顯著高于未麻醉組。本研究結果顯示,觀察組鎮痛后2 h、分娩前及分娩后2 h的血清IL-6水平均高于對照組(P<0.05),有不少學者認為IL-6升高為分娩時的正常生理反應,與硬膜外分娩鎮痛發熱無關[15],實施硬膜外麻醉的產婦出現發熱現象是否與炎癥因子有關還需進一步研究證實。本研究中Logistic多因素分析可知,硬膜外分娩鎮痛是產婦發熱的獨立危險因素,麻醉阻滯后引起的一系列反應使熱量堆積,產程得以延長,導致產婦體溫得以升高,因此,一旦出現發熱現象,需密切關注產婦及胎兒情況,并及時加以干預。
綜上所述,硬膜外分娩鎮痛是導致產婦出現發熱現象的重要因素,同時,還會引發羊水污染、新生兒感染及產后出血等并發癥,因此,實施麻醉后,需密切關注產婦及胎兒情況,嚴格把握麻醉劑量。